『在朝鲜族的精致与东北的豪放之间,延边有属于自己的独到滋味。』
延边是吉林省下辖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这片夹在长白山与图们江之间的土地,是中朝俄三国的交界地带,饮食里自然也流淌着“混血基因”。
清晨5点,州府延吉的水上市场已经人声鼎沸,蒸腾的热气从朝鲜族阿迈(阿姨)的汤锅升起,与东北汉子的打糕声交织,盛满酱汤的大碗泛着诱人的艳红色,上百种泡菜整齐列队,酸菜馅的饺子扑通跳进沸水。延边美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既不是单纯的朝鲜风味,也不是典型的东北菜,而是风土的碰撞,辣白菜的刺激被东北黑土地的醇厚驯服,大酱的深沉又被朝鲜族的轻盈甜辣所点亮。
▲早晨5点钟,延吉的水上市场已是人声鼎沸(黄宇 摄)
延边的饮食,是土地与历史的产物。长白山的松茸、图们江的明太鱼、珲春海域的帝王蟹,乃至东北平原的大豆与玉米,都在这里找到了最生动的表达。走进延边的任何一家餐馆,你都能从食物的细节里读到迁徙与定居的故事。在这里,风味的边界是模糊的,就像国境线上的晨雾,也像延边人的生活哲学,在朝鲜族的精致与东北的豪放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滋味。

龙浦洞(村)三面被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包围,在村子的最深处,有一家专营朝鲜族水豆腐的作坊。一连三天的大雨,驱散了赶来这里吃饭的食客,张学择师傅索性盘算着和太太金华一起做顿早餐家宴,邀请大姨和小姨来叙旧。早上5点,张学择把泡了一夜的鲜黄豆从盆里取出,他熟练地剥去豆衣,露出鲜黄色的豆子。此时,院子里的石磨静静地立在晨雾中,磨盘上还沾着昨夜的露水,他舀起一瓢清水,将石磨冲洗干净。第一缕阳光刚爬上东边的土墙,张学择摇起了磨杆,浸泡饱满的黄豆混着清水从磨眼漏下,乳白的浆汁便从磨缝间汩汩溢出,顺着石槽流进木桶。
这个小小的豆腐坊,也是张学择一家的住所,房子是姥姥传下来的,一并传下来的还有几亩地。每到春天,夫妇两人就种起茄子、紫苏、大白菜。随着泥土的解冻而来的还有每年第一批到这里吃鲜豆腐的朝鲜族客人。“大豆是延边这边的主要特产,朝鲜族在历史上还有过食素的传统,所以就养成了吃豆腐的习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肉很贵,价格低廉的豆腐就成了美味,嫩豆腐汤、辣炖豆腐都是我小时候经常吃到的菜。”张学择说。
张家的房子有三间,大门直通客厅,房屋内仍保留着如今已经并不多见的“温突儿邦”(温石炕),雕刻着“十长生”纹的木柜里装着各式山货、干料,一侧的厨房里铺着米黄色的木质地板,张学择掀起一块地板说道:“我们朝鲜族人的饮食秘密就藏在这里。”
与汉族地区常见的砖砌灶台不同,朝鲜族的锅是直接嵌在略低于地面的方形灶坑中的,锅沿与地板齐平,周围用黏土或水泥固定,形成下沉式的烹饪空间,被朝鲜族人称为“嘎玛索”(锅下灶)。约40厘米宽的两个铸铁锅,样子犹如礼器一样,嵌入地板,无法撼动,“一口煮饭、一口炖汤”。张学择跳进灶中,开始烧起火来,不一会儿,客厅的地面也跟着温暖起来,“我们很少炒菜,直到今天,炖和煮仍是朝鲜族最常见的烹饪方式”。
地灶这种深坑结构能减少热量散失,特别是在冬季,它不仅是烹饪工具,更承载着朝鲜族人对“家”的记忆。“从前房子少,家里人口又多,三代人挤在一栋房子里,这锅天天都是热的,如今人口少了,楼里暖气充足,这种锅几乎要消失了。”张学择说。
张学择大火烧豆浆,太太金华也化好了妆,开始煮粥。大姨小姨从市区赶来,为了参加这场早餐聚会,她们起得更早,脸上厚厚的粉底,遮住了她们的皱纹,完全看不出年近70岁的样子。即便是这样一场家庭聚会,朝鲜族人也穿得格外隆重,张学择穿了件带有蓝色传统纹样短襟周衣,女性们则穿着色彩明快、纱制的筒裙和“则羔利”(短衫),颇有庆祝节日的意思。
二姨韩英玉在锅里下了玉米糁和芸豆,她讲“这种灶台的火很旺,煮饭快”,不出20分钟锅里的玉米粥就变浓稠了。另一边,张学择把已经煮好的豆浆倒入桶里降温,不一会,厨房里满是水汽。“在我小时候,水豆腐是大户人家的早餐,虽然清甜,但不到中午就饿了。”大姨韩英子说。豆浆温度降到60摄氏度,金华开始点卤水,她每隔几分钟就会打开盖子,观看豆腐是否成型,“水豆腐讲究的是嫩度,口感比豆腐脑要嫩,比豆花要糯一些。在过去,吃水豆腐只点一些香油和酱油,后来朝鲜族开始迁徙到内陆城市,才演变出了葱丝酱油汁的吃法”。
如果仅有水豆腐和玉米粥,这顿早餐还称不上地道的朝鲜族早席。张学择用土鸡蛋做了大葱煎饼,炖了酱猪肉,最后还端上了自家种的蘸酱蔬菜。他强调,“真正的主角是你们说的咸菜”,说着,一家人从大小不一的陶罐、陶缸中夹出五六样泡菜,被辣椒酱包裹的白菜、萝卜、缨菜、黄瓜、桔梗等,散发出不同的酸甜味道,“每一种蔬菜都被辣酱、豆酱的咸味包裹,吃的趣味来自不同的口感,你只有仔细品尝,才能在咀嚼时尝到那食材原本的清香”。从这些老旧的容器不难看出,在延边的饮食版图中,泡菜不仅是一道小菜,更是一种味觉信仰。张学择说:“辣椒、蒜、姜、鱼露,和漫长的发酵时间,赋予了蔬菜鲜脆、辣爽的口感。”
早上7点,10盘菜摆满了餐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他们偶尔用朝鲜话交流起当年在家腌小菜的场景,偶尔用普通话对我说,如今已经不算常见的“沙参、蕨菜、野芹菜、海白菜、海菠菜”,是过去家中常备的佐餐佳肴。现如今,辣白菜成为泡菜的主流,“像用辣椒和蒜泥腌的茄子泡菜,还有味道清淡的水泡菜都很少见了,一些特殊的口感和味道也随之消失了,像被剥夺了某种乐趣,特别是在吃包饭的时候”。
▲腐坊老板张学择(左二)与家人围坐在餐桌前等待着开餐(黄宇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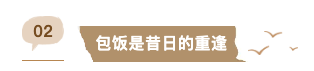
朝鲜族老饕说,当你对着菜单犹豫不决时,包饭是一种近乎万能的解决方案。一张新鲜的菜叶,卷起各种菜肴,一口塞进嘴里,层次分明的口感瞬间在口腔里炸开。这种吃法不仅省事,还透着一种质朴的满足感,仿佛所有的美味都能被这一口裹入其中。
中午的延吉牛市街一带,老字号的门店里挤满了食客。金太元的店也在其中,他常常一边招呼客人,一边“传授”着最地道的包饭吃法:“菜叶放在手心里,米饭不能多,放一个辣椒圈,来几根泡菜,挑脆的,酱也来一勺,肉放一块就行,别贪多,卷起来,一口吃下去。”这样的话,金太元每天都会重复很多遍。
出生于1962年,金太元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为“阿走西”,这是一种近似于“老哥”的朝鲜语称呼。他端着茶缸,讲起过往:“从前穷,孩子又多,一大家子围坐着吃饭很费餐具,为了省下几个碗钱,聪明的妈妈就发明了用菜叶包饭往小孩子嘴里塞着吃的方法,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种传统。”
▲“平山包饭馆”老板金太元,他喜欢在午休时喝上一杯米酒,享受一天中难得清闲的时光(黄宇 摄)
金太元的确有些怀旧。他曾经当过兵,餐厅里挂了不少和战友合影的黑白照片。他甚至还在厨房门口,用老式发报机自制了一台军旅风格的点餐系统,当信号灯亮起时,那些过去的岁月仿佛从未走远。
金太元所服役的部队是原先的“四野”,这是一支作风硬朗、战术全面的部队。即便在餐厅工作,他的身上仍保留着军人的作风。每天清晨5点,他准时起床,赶在早高峰前来到店里,开始炖煮猪肉。肥瘦相间的肉块经过酱油、大酱、葱叶两小时的陪伴,慢慢析出油脂,凝成晶莹的胶质。这种对时间的把控和对细节的讲究,也让他的烹饪多了一分旁人难以复制的精准。
在延吉,新餐饮人会推崇烤肉,比起延吉黄牛肉,金太元个人觉得土猪肉才更正宗,“卷在紫苏里的五花肉,永远有一种乡土气”。金太元说五花肉很早就登上了朝鲜族人的餐桌,也更贴近他们的日常,“整个延边上的人好像都对这种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肥瘦相间的肉有一种执着”。
他做包饭,爱用延吉本地种植的大米,用得多的是口感软滑的“吉粳81”,有时候也会用带有天然清香的“稻花香2号”,“米黏度适中,颗粒饱满,更能衬托出猪肉的丰腴”。老金说,包饭的奥义在于“一口融合”,否则失去咀嚼的乐趣。延吉地处长白山区,昼夜温差大,稻米生长期长,淀粉结构恰好落在老金想要的区间,像一位懂得退让的配角,“让苏子叶的清香、五花肉的脂香、大酱的咸鲜在口中层层展开”。
在物资匮乏时期,包饭不过是几片白菜叶裹着米饭和零星泡菜的果腹之物,“菜叶的品种单一,甚至带着些许清苦,却也因此衬得那一点荤腥格外珍贵”。老金说:“如今的包饭已经从家常便饭升格为宴席上的主食——苏子叶的辛香、嫩绿的生菜、柔韧的海带、清甜的豆皮和焯过水的白菜团子,都能成为包裹美味的载体。”金太元继续说着菜中的内容:“除了烤牛肉、烧五花这些人们熟悉的菜色,海兔子、明太鱼这些海鲜也被‘卷’了起来。但食材越是丰富,越让人想起最初那一口质朴的搭配,微苦与肉香的混合,才是生活的本味。”
▲包饭曾是果腹之物,但如今已升级得格外丰盛(黄宇 摄)
金太元的包饭餐厅名叫“平山”,是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黄海北道,临近礼成江畔的一个郡,100多年前,金太元的爷爷带着家人从这里迁徙到中国东北,如今,家族的血脉已散落各地:妻子带着父母在韩国工作,女儿大学毕业后定居南通,只剩老金一人守着这家小店,像一名固执的士兵,坚守着最后的阵地。
他偶尔会和当年的老战友聚聚,酒桌上总少不了朝鲜族人的“三米”——米饭、打糕和米酒,老金喜欢米酒,他说:“滋味就是回忆。”开店20多年来,客人来来往往,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当年被妈妈带来吃饭的孩子,在多年后,又带着自己的母亲回来寻找昔日的味道,临别时的一句“味道依旧”,让老金百感交集。那个不变的味道,是装在小小石锅里的大酱。这个半个世纪前的调味,是母亲制作的配方。老金记得,母亲以前总说,“酱的味道最重要”,这句话他一直记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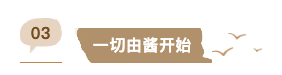
从延吉市区向西北驱车20分钟,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土路,空气中渐渐浮起一股复杂的发酵气息——咸鲜里裹着豆腥,隐约还有晒透的秸秆香。尹哲虎的大酱厂就藏在这条土路中间,几间平房围出的小院,被塑料大棚笼罩着,水泥台上晾着上百块棕褐色的酱坯,远看像刚出土的陶器。
发酵车间像个时间停滞的洞穴,成坨的酱坯被草席包裹,在半晒处静置百日,表面渐渐皴裂出深色纹路。“朝鲜族老话讲,酱缸台是家里的脸面”,尹哲虎打开陈年酱块,内里呈现出葡萄酒一般的红褐色,他把酱块凑到我鼻尖,一股发酵的酸韵、隐约的酒香扑面而来。
▲大酱厂老板尹哲虎认为圆形的酱块发酵更为充分(黄宇 摄)
1972年出生的尹哲虎蹲在灶台前,用铁钩拨弄柴火。这个从韩国打工回来的朝鲜族汉子不善言辞,问到火候时他讲:“大火两小时,小火六小时。”他的搭档金成日掀开蒸笼,一团白雾瞬间吞没了半个车间,“工厂大酱用机器压碎豆子,我们非得蒸到几乎出泥”。随即,他抓起一把黄豆轻轻一攥,金黄的豆沙就从指缝里溢出来。
这是最为原始的大酱制作工艺,黄豆经过蒸煮之后,就要进入“摔酱块”的环节,捣碎的豆泥一般被“摔”成立方体的酱块,但尹哲虎觉得圆筒形更适合接触空气,于是他自制了圆筒形模具,重塑了酱块的形状。昼夜的温差,让发酵大棚吐故纳新,酱块也在这里开始“呼吸”,随后“长出白色的霉菌,这说明发酵已经开始”,金成日说。
经过100天的发酵,酱块步入“下酱”环节,此时的酱块被纷纷掰碎,放入陶缸,加入盐水,这个过程极其漫长,有时会持续到一年半的时间。“中间还要‘打耙’,充分搅拌,撇去浮沫,让酱料发酵均匀,”尹哲虎补充道,“现在的工厂用发酵机和温箱,制作时间被大幅度缩短,但没有受到真正的日晒、温差影响,没有足够长时间的糖转化(发酵),味道还是不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延边是一个被酱香浸润的世界。大酱勾勒出东北风味的轮廓,发酵的鲜咸在菜肴上碰撞。车间内的午饭是酱汤配米饭,此刻的汤锅在咕嘟,浓稠的酱色里翻滚着豆腐和白菜,某种比盐更厚重的滋味顺着蒸汽爬满屋顶。尹哲虎从石锅中舀出深褐色的液体,他讲当年自己在韩国打工时的境遇,“不喜欢那里的酱汤,淡得像喝盐水”,他想念的咸,是属于黑土地的咸,让离开的人想家。

每隔一两周,尹哲虎就会开着他的小皮卡,将一批手工大酱送到位于延南路上一家名为金氏园的餐厅,这里的主厨会妥善地将其制成酱汤,也正是在这里,朴实的民餐正在进化成一种宴席。
在过去,当人们提到朝鲜族宴席的时候,会想到融合了满、汉、蒙的粗犷菜式,偶尔也会想到铺满了一桌子生菜和泡菜的冰冷宴席。金氏园的许京熙认为,真正的朝鲜族宴席并不是这样的,“是从民餐层层筛选出来的”。31年前,许京熙刚开金氏园的时候,她只有一道拿手菜——江米鸡。在延边地区,新女婿第一次去岳父家过年时,女方家通常会准备江米鸡来款待。许家妈妈当年就是用这道菜打动了女婿金先生,也让许京熙有了复兴朝鲜族民餐的念头。
现如今,江米鸡的做法早已革故鼎新,土鸡腹中填入的已经不只是当年的红枣,枸杞、松仁、野生人参等滋补调料也与江米一同下锅,经过两个小时的蒸煮,滋味相互融合,鸡肉也浸透了米饭之中。在厨房制作江米鸡的主厨名叫刘东宾,是来自汪清县的汉族小伙子。他多年前娶朝鲜族太太为妻时也经过了江米鸡的“洗礼”,对朝鲜族风味有了更深的理解,“开锅要能闻到人参、红枣的药材香;米粒要有少许的粘连,才能有好的口感;鸡‘骨肉分离’时,中间的汁水才能足够丰富;最要紧的是入味,贴近鸡骨的肉丝,需嚼起来有一丝陈年火腿的复杂咸鲜”。
▲“金氏园”的主厨刘东宾认为江米鸡的做法早已革故鼎新(黄宇 摄)
“把民餐做成宴席,其实就是尽可能地把经典菜重新升级”,刘东宾说他曾经在大连学习如何改良韩国风味菜,在他看来,朝鲜族餐和韩餐一直是相互影响的,“两边菜系是同根的,但韩国的食材用法单一,那边的人喜欢淡口味,甜、辣、咸三个维度要分别突出,这与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不一样,我们偏爱更多元的食材,和更重的口味,但讲究味道的平衡”。刘东宾用明太鱼举例,韩式的辣明太鱼汤,配料里大多只有洋葱、豆腐、辣椒;而朝鲜族除了这些料,还会放入银鱼、西葫芦、水芹作为调味,压制住汤中明显的辣味,用蔬菜提升了汤的香甜。
▲“金氏园”餐厅把朝鲜族的民餐做成宴席,吸引了不少回头客(黄宇 摄)
在刘东宾看来,无鱼不成宴,最能抚慰延边人肠胃的鱼就是明太鱼。他做辣炖明太鱼颇为拿手,半干明太鱼在料酒和姜片的浸泡下,退去了海潮的腥味,入锅时的油烹,锁住了鱼身中最后的那点水分,随即加入的韩式辣酱和辣椒粉,则是给鱼裹上了一层赤红色的外衣,使其看起来更有食欲。10余分钟焖煮后,刘东宾还要让这鱼在锅里待上一会,“酱料的香气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再次被鱼肉吸收”。
酒红色的明太鱼,配了几片鲜绿的苏子叶,两种颜色的对撞让人眼前一亮。菜的色泽,如今也是朝鲜族菜的一大特色,泡菜坛里是“一清二白”的素净美学,煮炖大菜铺陈着“浓墨重彩”,金色的煎饼、翡翠色的野菜拌饭、打糕上的红豆沙艳若朝霞,甚至在摆盘时都要遵循“五方色”的古老传统。
“朝鲜族的饺子皮不用面粉,用的是米粉和糯米粉。”刘东宾说。东北人喜欢有点黏牙的口感,所以饺子就做成了这样,他继续说道:“黑色的饺子用的既不是荞麦粉,也不是黑米粉,而是土豆,早年间,土豆经过长时间的贮存,在地窖里氧化后变成黑色,因为样子太丑,就把它烘干,制成土豆粉,于是就有了黑色饺子。黑白两色的饺子皮,一个对应着白云,一个代表黑土地。”
“朝鲜族宴席上必不可少的菜,是小吃”,从煎沙姜到米肠,从橡子冻到炸多春鱼,刘东宾说这些都是搭配米酒的小菜。做厨师之前,刘东宾下馆子必点的两道菜是“熘肉段”和“锅包肉”,但如今,他偏爱烤牛肉锅和辣白菜鲅鱼。刘东宾说:“如今的朝鲜族菜也讲究时令,比如吃鲅鱼最好的时节是秋季,此时鲅鱼为越冬储备脂肪,肉质肥厚、油脂丰富,口感也鲜嫩;春天的鲅鱼开始洄游,肉质紧实,最好的烹饪方法就是红烧、辣炖。”“虽然朝鲜冷面上总是漂着两片牛肉,但在过去的日子里,耕牛是不能随便宰杀的,那两片肉也只能解解馋”,刘东宾说朝鲜族人心底里爱吃牛肉,但真正实现牛肉自由也不过这20多年,“烤能激发出牛肉的那种特有味道,又透着一种粗犷的烟火气”。
▲烤延边黄牛肉、参鸡汤都曾是朝鲜族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主菜(黄宇 摄)
刘东宾的刀在砧板上轻快地跳动,辣酱香裹挟着蒜香从铁锅里窜出,酸辣交织的“鲜”与“辛”在空气中勾勒出延边市井的烟火轮廓。在这里,食物超越风物的范畴,几十年间的时代更迭,几代人的生活变化,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味觉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