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4月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侵占中国4000多平方公里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据点。
1962年9月20日,战争阴云早已笼罩在高原边境。当晚,印军再次武装挑衅,朝我军择绕桥西阵地开枪射击,还投掷手榴弹。西藏军区二团二连班长吴元明眼疾手快,一把拾起手榴弹,扔了回去,完成了守卫任务。而在这之前,吴元明和他的两名战士已经在被三面包围的情况下,同来势汹汹的印军对峙3天3夜,仍坚决执行着我国政府不开第一枪的边防政策。
不开第一枪不是不敢,而是时候未到。10月15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苏联和美国都紧张关注着这件事,没空注意印度和中国。
这给了等了三年的中国反击时机。
10月19日晚,在夜色的掩护下,一支一万多人的部队涉过克节朗河。这一万多人静静地潜伏在河边,周围只听得到水流声。19时30分,两枚信号弹升空。振耳欲聋的炮弹声瞬间响彻喜马拉雅山麓。中印边境反击战的第一枪,也是反击战东线战场的克节朗河谷战役立马打响。
密集的炮弹落在印军阵地上,15分钟的火炮轰炸结束后,步兵冲锋的号角响起。1万多潜伏在印军眼皮子底下的解放军朝着这些碉堡冲了上来。
短兵相接后,印军兵败如山倒。
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解放军就拿下了克节朗河谷。三天内,全歼印军王牌第七旅,并活捉旅长达尔维准将。
10月24日,首战告捷的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建议,并命令东线反击作战部队停止追击。中印边境战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东线战场迎来短暂的休战期。而在西线战场,新疆边防部队一直战至28日,清除了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据点37个。
就在西线战场大获全胜的前一天,10月27日,新疆籍边防战士司马义·买买提所在的三班在副连长的带领下,乘汽车在边防线执行巡逻任务,一股印军突然出现。倚仗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印军向巡逻车辆发起猛烈扫射。汽车前轮被打穿,车厢板被击破,失去了掩体的战士们被印军密集的火力压得头都抬不起来。
“副连长,我去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司马义·买买提大喊一声,随后他跃过车厢后尾,端起冲锋枪向敌方阵地冲了过去,用肉身吸引火力。趁印军火力转移之际,三班战士迅速调转安置在汽车驾驶棚上的重机枪的枪口,向印军猛烈还击,最终等到了援军的到来,全歼了这股敌军。而司马义·买买提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司马义·买买提烈士,新疆军区骑兵3团机枪连班长
西线战事未停,中央明白印度对和平解决建议并不感冒,开始紧密筹划接下来的战事。而首战失利的印度也对自己抱有奇奇怪怪的期望,决定一打到底。印度总理尼赫鲁开始向美国求援。美国很乐意有人牵制中国。很快,大批美式军火被送到了中印边境,有的直接空投到了第一线。
11月14日,有了美式装备后,休整了不到一个月的印军又发起了反攻,中印边境自卫战第二阶段打响。
当时的最前线是瓦弄。
当印军后援行军抵达瓦弄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一支中国军队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这支以逸待劳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130师,被称为“四野最能打的十个部队之一”,指挥官为张国华中将。

张国华原名张福桂。少年时期,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期许,他把名字改为“国华”,奔赴井冈山。解放后,征战多年的张国华担起了解放与重建西藏工作,并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在中印边境战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后,张国华前往北京参加了中央军委会议,随后立即返回拉萨,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的对印作战任务。
那几天,他一共想了3个作战方案。最后觉得前两个不能歼灭敌人主力,特意选了最后一个:正面实施强攻,还要派奇兵迂回到敌人后方,吃掉逃跑的印军,阻断增援的印军。
11月16日晨,我军发起第二阶段反击。围绕着瓦弄战场,中印爆发了惨烈战事。在瓦弄地区80高地战斗中,排长周天喜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两次负重伤,带领全排打下了印军两个地堡群,夺回高地,为部队反击创造了条件。而他本人却在冲击第二个地堡群时,不幸牺牲。
周天喜烈士,陆军第54军130师389团7连排长
11月18日晨,来自陕西省贫穷农家的22岁青年庞国兴所在的九连,在袭击西山口印军的任务中担任先锋。西山口前面有个不大的无名高地,高地后面有印度的炮兵阵地。印军还在无名高地上配置了一个加强连,前沿分布着机枪点。
突然,西山口上印军的榴弹炮一声不响了。九连乘机迅速扫清了无名高地上的残敌。但在享受胜利的喜悦同时,大家感到非常奇怪,就连团长解全威也很纳闷:“我还没有调部队去打,西山口上敌人的火炮怎么就哑了呢?”
是谁干掉了这个炮兵阵地?
原来,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和战士王世军首先冲上无名高地。他俩发现一股敌人正向西山口逃窜,就紧紧追赶上去,就此冲出了无名高地,和连队失去了联系。新战士冉福林看到庞国兴、王世军穷追残敌,也跟了上去。
于是,三人自动组成临时战斗小组,不仅解决掉了两个炮兵阵地,还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台汽车。
庞国兴三人战斗小组,庞国兴(中)、冉福林(左)、王世军(右)
11月18日上午,愈战愈勇的我军拔除了印军多个据点,开始转向纵深的印军炮兵阵地发起进攻。然而,在向印军27号据点发起冲锋时,部队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据点建在中国境内的5100高地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由于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由此向东可通视中国境内纵深10多公里,向西可清楚地瞭望楚舒勒附近的丁如泽地区,是印军丁如泽机场的最后屏障。
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印军岂会不做部署?
无数地雷埋在通往27号据点的路上。发起冲锋的步兵连战士被地雷炸得非死即伤。这时,高地上的轻重机枪又猛地响了起来,封锁了雷场边缘;10多辆美制M-26“潘兴”式坦克,连同印军炮兵火力一同向高地前沿实施拦阻射击,部队暴露在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山坡上,伤亡惨重。
“工兵!工兵!”
步兵连长曹富荣急了,扯开嗓子大叫起来,“快把地雷排掉”。
工兵3班几名战士在副排长的带领下,率先冲入雷区,没过多久,先后牺牲。于是,工兵2班又顶了上去。班长张铭儆先冲进了雷场,开始用探雷针起雷。跟在班长身后的是刚入伍不到两年的四川籍战士罗光燮。

罗光燮烈士,陆军第4师10团工兵连战士
在第一阶段反击作战中,为了作战更方便,罗光燮在零下40度的高原严寒中脱掉了皮手套,赤手拿着爆破筒。事后,他的双手被活生生地揭掉了一大块肉。在临时包扎所里,军医跟他说,再不及时治疗,他的两只手就会有截肢的危险。可在往后方转院接受治疗的途中,他却找机会溜了,搭便车返回了连队。
回到11月18日那个上午。为了提升排雷效率,正在起雷的班长张铭儆让罗光燮用爆破筒在前方引爆地雷,开辟通路。罗光燮弯腰猛跑了10多米,刚通过了一片开阔地,“轰”地一声雷响。他的左腿血肉模糊,左脚掌连着大头鞋飞到几米以外,身后背着的56式半自动步枪被炸得七零八碎。
见罗光燮负伤,班长张铭儆正要赶过来救援。罗光燮转过头来,举起一只手臂,然后又扑在地面上,向着雷区爬去——他要用自己的身躯排雷。

“罗光燮!罗光燮!”班长流着泪吼了起来。随着一连串地雷爆炸声响起,年仅21岁的罗光燮壮烈牺牲。他的身后,是一条6米宽的安全通道。
同为18日,西线战场,河南籍战士王忠殿所在的九连遇到了印军暗堡的阻拦,身边战友两次冲上去爆破都未得手。这个暗堡有20多米长,印军密集子弹朝外疯狂射击。王忠殿心想:不排除这个障碍,部队直接在印军火力威胁下,会遭受更大的伤亡。
于是,心急如焚的王忠殿对班长说道:“班长,我上!”班长同意后,他和一位战友一起冲了上去。他端着爆破筒,在火力掩护下,时而跃起,时而卧倒,一直冲到暗堡跟前。刹那间,王忠殿翻身冲进了密弹交织的火网,把爆破筒插进暗堡的缝隙里。可是,还没等拉火,爆破筒就被印军推出来了。王忠殿又使劲推了进去,刚要拉火,爆破筒再次被推出来。
王忠殿气得咬牙切齿,他第三次把爆破筒推进暗堡,用尽全身力气顶住,再拉断导火索。爆破筒吱吱作响,眼看就要爆炸了,战友大喊“王忠殿下去!下去!”但他动也不动,伴随着爆破筒爆炸的“轰隆”声,印军的机枪声熄灭,同时熄灭的,是王忠殿年仅十八岁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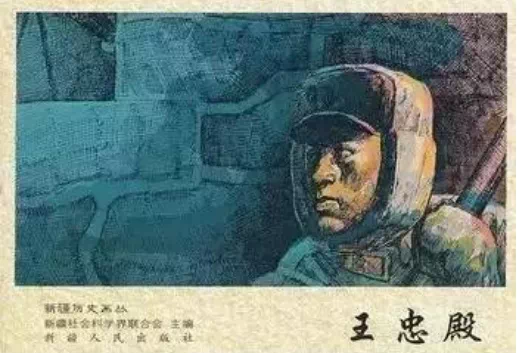
正面激战正酣,张国华将军部署的那支奇兵也有了进展。
11月20日,在当地藏民的指点下,这支奇兵找到了狭窄的贝利小道。这条路最早是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时勘查到的,路很难走,有些地方不能行军,解放军就用绳子往下吊。经过不眠不休六天五夜的强行军后,这支奇兵,终于在中国发起总反攻之前,顺利绕到了印军后方,切断了印军援军的唯一可能性。
此时,已进行到了战争尾声。解放军东线一直打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眼前就是无险可守的印度阿萨姆平原,印度边防重镇提斯普尔垂手可得;西线打到了印度河上游,离首都新德里就剩300公里了。
要不了几日,我军就能直挺挺地开进新德里,并全歼前线战场上的印军。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胜利唾手可得之际,中国对外宣布:自12月1日起,中国将撤回1959年的实际边境线,并在此基础上,再往后撤20公里。
消息一出,无论印度还是一直在背后支持印度的美国,都深感震惊。同样感到震惊的,还有张国华将军。他表示自己想不通。他也深知,手底下那些亲眼目睹战友牺牲的边防战士们,也很难想通。即便如此,张国华将军还是给自己的军官们下了死命令:想不通也要通。
其实,中国从没想过要占领印度的领土,而且补给运输也实在困难,无法长期保障。退一万步讲,就算打到你家去了,也捞不着什么实际好处,白白牺牲了宝贵的子弟兵。
我们唯一想要的,只是捍卫领土主权,仅此而已。
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印战事升级,正遂了一直在背后积极鼓动印度的美国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