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隋林
编辑丨吴酉仁
问:能否谈一谈史迪威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的作为。看过一种说法,说他刻意拖中国的后腿,是真的吗?
日军口中的“一号作战”,即1944年4月-12月的豫湘桂会战。这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大的一役。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损失了60余万军队和2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史迪威当时有一重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缅甸战场,对豫湘桂会战的支持极为有限。这是“史迪威在豫湘桂会战中刻意拖中国军队后腿”之说产生的背景。1944年4月12日,史迪威下令禁止陈纳德与蒋介石直接来往。陈纳德所有与蒋的交涉,必须通过史迪威处转达。陈纳德当时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隶属美国军方;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空军参谋长。陈纳德虽然不满这项指令,但只能服从。鉴于日军攻势猛烈,陈纳德在1944年4月初曾提醒史迪威,“日本地面部队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①据此,陈纳德建议将十四航空队的主要任务,由守卫轰战机改为应对日军即将发起的攻势——1943年12月,美国曾在中国部署过一批轰炸机,目的是攻击日本本土的某些重要目标。为保护这批战机,美国军方将陈纳德所属第十四航空队的半数移防成都。原本给予十四航空队的军用物资,也因此少了2500吨。②故此,陈纳德希望史迪威能够批准他使用已运抵中国的库存油料,以增加飞机的升空作战时间。但陈纳德的这项要求,未能得到史迪威的积极反馈。他等了一个多月未获史迪威的回复,不得不再次去信催促。信中说,军队的库存油料已降至最低限度,急需补充。史迪威的回复是:除非英帕尔的的情形有所改善,否则他看不到向陈纳德增加运送供应品的可能性。史迪威告诉陈纳德:“你只得减少你的活动到一个程度。”③为此事,蒋介石稍后也出面向史迪威提出请求。东南亚战区司令官蒙巴顿,同样表态支持陈纳德的要求,向史迪威施压。史迪威则在写给妻子的家信中说,他根本不想理睬中国与印度的催促,只想留在缅甸丛林里,与他的士兵们在一起。经此拖延,当史迪威迫于压力终于应允陈纳德的请求时,日军已结束了河南战事——据日军战史的记载,在河南会战中,“敌机出动共约400架次,我出动飞机共为2700架次,约为敌之7倍。”④在制空权方面,河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处于绝对劣势。第十四航空队获得物资补给后,随即投入湖南作战。史迪威则于同期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提出建议,希望免去陈纳德的职务。1944年6月,国民政府曾两次急召史迪威,希望他自缅甸返回重庆,共同商议军情。史迪威均不为所动。后来迫不得已飞回重庆,也仅停留两天,只走了一个形式,并未提供实际帮助。虽然史迪威的身份之一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他从未将注意力放在国内战场。史迪威在1944年最在意的,是如何收复缅甸,洗刷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耻辱。所以,自1942年开始,“两年多以来所有运入云南之租借物资,史迪威均装备了远征军,对于国内部队很少补给,精壮兵员又多补充远征军,国内部队空额多未填补……”⑤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训练的中国驻印军(代号“X部队”)和滇西远征军(代号“Y部队”)20万人,成为了中国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1944年9月,日军兵锋威胁到了桂林美军基地,蒋介石召见史迪威,要求他“将滇西卫立煌部队之主力调回昆明,以备必要时转用于桂林方面。”卫立煌部队即Y部队。史迪威则愤怒回答:“远征军调回昆明,缅甸作战势必陷于崩溃,则前功尽弃,加强桂林防守,应调胡宗南部队出来,让第十八集团军也参加作战。”⑥在历史学者齐锡生看来的,史迪威虽然在缅北战场取得了胜利,但那是“以牺牲中国本土为代价”换来的,“北缅之胜利,远不足以抵国内东战场之损失”。反之,“假如中国能够把Y部队留在中国本土,则日军‘一号作战’造成的破坏肯定会大幅降低。”⑦史迪威坚持缅北作战的最重要理由,是打通中印陆上交通。但远征军付出巨大伤亡(X部队伤亡1.8万余人、Y部队伤亡67403人),历尽艰辛修筑起来“史迪威公路”,作用却远不如预期。按史迪威的预估,该公路打通后每月可提供3万吨的物资运输,实际情形则是,至抗战结束前,运输量最小的月份,是1945年2月,只输送了物资1111吨;运输量最大的月份,是1945年5月,只输送了物资8435吨。与原定计划相去甚远。⑧可供对比的,是中印之间的空运吨数。1945年1月,空运输送物资为44099吨;6月增加到55387吨。1945年7月,共有91183吨租借法案物资运到中国,其中空运部分为73682吨,输油管为11061吨。“史迪威公路”在该月,则仅提供了5900吨的运量。⑨以上,即“史迪威在豫湘桂会战中刻意拖中国军队后腿”之说的由来。但这些,终不过是豫湘桂会战失败的外部原因。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向参政会解释豫湘桂会战的失败原因时,重点谈了两条内部原因。第一条是情报能力不足,导致河南战场上的军事部署出现了大问题。蒋说:“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是足够应战的。所以我们当时只照敌人过去步炮空连合作战的战术,来部署准备。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加作战。我们当时的布置,以许昌、洛阳为河南会战的两大据点,许昌的工事,建筑得相当的坚固,照敌人平时攻击的方法与力量,是必可久守无虞的。但是敌人攻击了几天无效之后,他就用战车来攻城,我们部队事先并未有此训练、各种工事,亦未注意及此。所以不到两天,许昌就被他攻破,吕公良师长也就在许昌城殉职了。”
第二条是战区长官与重庆之间发生矛盾,导致湖南战场上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溃败。蒋说:“长沙战役,长沙失守之速,是出于统帅部意料之外的,近年来,长沙的工事一再加强,而且长江以南精锐的武器差不多都集中使用,在长沙近郊及岳麓山各重要据点。守卫长沙的第四军是我们革命军里面最有历史的部队,统帅部当时相信其必有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谁知作战不到一周,统帅部就和他们失去了通讯上的联络,当时还以为是无线电发生了障碍,决不料长沙已经失陷,到第二天第四军的军长、参谋长和他各师长都退到岳麓山以南宁乡附近,我们才知道长沙失守。这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最痛心、最耻辱的一件事。……所以长沙失守之后,统帅部认为完全是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的责任,当即令第九战区长官部将其押解来渝,军法从事业已枪毙。”⑩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会众人看来,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的被枪毙,实际上是做了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替死鬼:“评判会议皆谓薛岳司令官退出长沙时,只命张德能保卫长沙,而对于保卫长沙之方法,毫未予以指示,且薛岳退出过早,致动摇军心,不能谓其已尽长官之职责。”⑪
然而,蒋介石震怒于长沙沦陷过于迅速,造成了极坏的国内外政治影响,批示必须将张德能枪决。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虽然明白“张德能任军长年余,该军之人事经理权皆不在手中,其死可谓半由于长官所造成”⑫,却也只能遵从蒋介石的意志,让张德能去为薛岳替死,然后在日记中感慨道:“近数年来,法律不能制裁权位较高者,实抗战军事上之一大缺陷。”④
当时,不但军委会军法执行处,对薛岳这类高级将领的失职毫无办法,专门弹劾政要的监察院,也不愿意接下针对薛岳的弹劾提案。监察院的理由是:若接了提案,审查明白后,却不能制裁薛岳,徒损监察院的尊严。何成濬在日记中写道:“监察院有委员数人,对于长沙、衡阳之失陷,查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实处置失宜,贻误戎机,即政治上之一切措施,薛兼主席亦有违法舞弊之嫌,特提出弹劾,经审查会通过,于院长右任虑办理一兼主席之长官不易,反损害监察院尊严,尚搁置未送呈国府。”⑭
就豫湘桂战役的惨败而言,这些内部因素,显然比史迪威这个“拖后腿”的外部因素,要重要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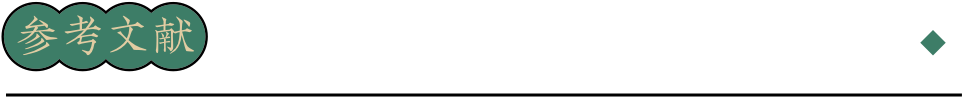
①③《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1-312页,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2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第93页。
②金光耀:《陈纳德航空队与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河南会战》(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162页。
⑤⑥⑦杜建时:《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第198、199、210页,杜建时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
⑧⑨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82-484页。
⑩蒋介石:《一年来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之报告》,1944年9月16日。
⑪何成濬著、沈云龙校:《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7月30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⑫何成濬著、沈云龙校:《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8月20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⑬何成濬著、沈云龙校:《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9月3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⑭何成濬著、沈云龙校:《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12月20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