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这样写道。这句振聋发聩的判语一直告诫着我。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逐渐淡漠了对上帝的景仰,却日益滋长起“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这种“救世”的野心,如阿隆所言,后来成为了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至今仍以“救人于水火”的名义生生不息。
自从读完《知识分子的鸦片》,我就喜欢上了了雷蒙·阿隆,而不是他的 “小同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尽管萨特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在中国的名声早就如日中天,尽管我读萨特的作品要远远早于雷蒙·阿隆——那个时候正是《存在与虚无》在青年学生中大行其道的时候,1988年,我大学三年级时的学年论文主题,就与存在主义有关,如今我已完全想不起来当年自己是如何在论文里胡诌的。
因为喜欢,所以这些年,我尽力搜罗国内出版的雷蒙·阿隆的作品,诸如《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历史讲演录》《论自由》等。这些作品中的部分,除了专业读者外,恐怕很少会有人再去阅读。当然,我也读别人写的雷蒙·阿隆,比如托尼·朱特笔下的雷蒙·阿隆。
“我相信,我已说出了基本事实。”作为20世纪法国最为杰出以及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艾伦·布鲁姆称雷蒙·阿隆为“最后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兼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论家、记者于一身的他,在临终前几分钟留下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告别。
1977年,在准备离开《费加罗报》的前一天,阿隆突发心梗,瞬间丧失说话和写字能力。虽然一天过后便部分恢复,但阿隆说,“从那时起,死亡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每天都出现在眼前的东西”。
这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让阿隆“渴望不受拘束地回忆自己的往事,这并非出于自觉的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意愿”。
中国人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中国人喜欢用善恶的概念,其实,可能应该是更真,是真话。所以,《雷蒙·阿隆回忆录》中,阿隆对他一生所经历的20世纪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追溯和辨析——而不全是辩护,它们帮助我们一起完整勾勒起了阿隆这个既能写象牙塔里的学术著作,又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不仅与阿隆与戴高乐、基辛格、德斯坦、特鲁多等政治家过往甚密,对重大历史事件也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哪怕与朋友为敌)的“介入的旁观者”,一个“无限复杂的忧患灵魂”(忧患来自于对现实的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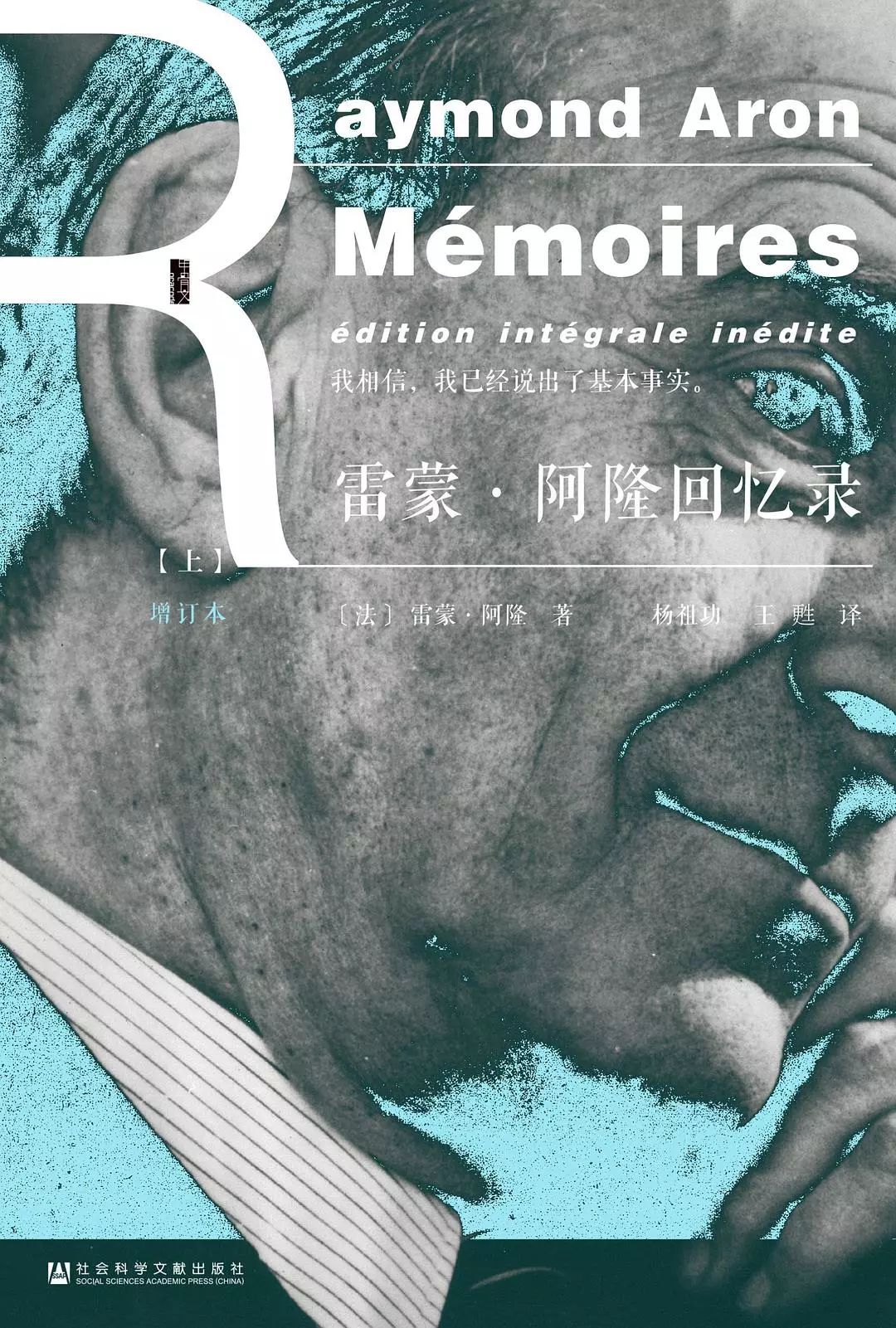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2017年版

二
作为法国最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政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称阿隆为20世纪法国人民的“思想保健师”——在面对20世纪那些重大事件时,阿隆那些与同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敏锐的触觉、深刻的思想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阿隆从小有着极端的自尊心,总是雄心勃勃地盯着班上第一的位置,喜欢学习新的知识,少年时代喜欢阅读《三个火枪手》《战争与和平》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小说,以及从父亲的藏书中寻找关于德雷福斯案件的报道以及左拉的《我控诉》等。在中学毕业时接触到了哲学,在读哲学班时,阿隆懂得了一条道理:“掌握了思索这个武器,就可以摆脱在生活中的被动性,就能充实、丰富生活,并与大思想家琢磨、切磋。”
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阿隆与萨特、尼赞、吉耶等成了同学,并成为朋友;他的老师有当时的著名哲学家莱昂·布伦什维格、阿兰等。莱昂·布伦什维格是新康德主义者,在高师,阿隆用了一年时间潜心研读康德的著述,这使他受益匪浅。而阿兰的和平主义、道德主义、反权力崇拜的观点也影响了阿隆,但阿隆后来认识到:“只有在政治权威作恶多为善少的情形下,阿兰的法则才是适用的。一旦我们真正需要反对集体膜拜的祸患了,谁都用不上。”当然,他也研习笛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卢梭、马克思、孔德、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年轻的阿隆一度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康德的研读,让阿隆认识到,“尽可能老老实实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自我要从现时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当个旁观者”。
阿隆1930年代初到德国科隆大学当助教,他既读资本论胡塞尔海德格尔曼海姆涂尔干的作品——现象学使阿隆跳出了新康德主义,而萨特也是通过阿隆才知道胡塞尔的——也读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
但是,“阅读马克斯·韦伯的书,我逐渐意识到韦伯学说的伟大,同时发现自己已同韦伯存在一种心意相通……1932年和1933年,我首次觉察出良心的交锋和怀抱的希望,这都是一个社会学家兼哲学家启发我的”“社会现实的内在意义和呼之欲出的政治关怀,是我亲附马克斯·韦伯的两条理由,另外还有一条理由是,他关心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用的认识论”。
1931年和1932年,阿隆常常扪心自问:漫无边际的阅读,是否分散了精力?后来回到法国,阿隆才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1979年,阿隆获得歌德奖时,颁奖者在致贺词是说阿隆:“德国是我的命运”,阿隆认为没错。
当然,像修昔底德、帕累托、克劳塞维茨等人的作品,同样深深影响了阿隆。


雷蒙·阿隆(1905-1983)

三
在《回忆录》的尾声,阿隆回忆,虽然自己受到德国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受盎格鲁-美国人重视分析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使我背离法国”。阿隆被视为继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后法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终其一生,阿隆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仅为法国的利益而努力,也一直捍卫着法国人文精神的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遗产:理性与自由。
阿隆一生经历了20世纪诸多大事,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不同阵营的对峙冷战,等等。一战时他尚年幼。在德国游学时,当别人对德国社会的变化不以为然的时候,他却敏锐地感到了可怕的变化来临:“最使我震动的是,纳粹掌权后几个星期,人们几乎不觉得历史上发生了大事情。成百万柏林人一点儿也瞧不出新东西。可兆头迹象却不是没有:仅仅三天功夫,都城里大街小巷全都是穿制服的人……”
在《历史意识的维度》一书中阿隆写道:“我曾在德国经历了1933年那几个悲壮的月份,一周接着一周,柏林的街道不断被棕色制服所占领,那些半个世纪以来为文明的社会主义投票的工人似乎神奇地消失了,一个奥地利下士嘶哑的嚎叫,在所有高音喇叭中发出回响,淹没了继承着一个伟大传统的文化人的声音。” 1933年,身处德国风暴中心的阿隆彻底打破对和平的幻觉,“1月31日之后,尤其是纳粹火烧国会大厦后,我就有一种气数将尽之感,觉得历史在动,而且短期内势不可挡。”(《介入的旁观者》)
媒体是阿隆离开学校后最初介入社会的公共平台。二战爆发后,阿隆参加了法军,当了一名气象兵,战败后他渡海到了英国,虽然没能当上希望的坦克兵,却在伦敦办起了刊物,为自由法国而战,这也奠定了他作为政论家最初的基础。
战争结束后,回到巴黎的阿隆先是加入了《战斗报》(加缪也在这家报社),1947年《战斗报》被喊停后又加入了《费加罗报》,最后加入《快报》。
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战前对于苏联制度的争论以及战后冷战对知识阶层的影响,阿隆也深度卷入了法国思想界的争执。而《知识分子的鸦片》的出版,就是在这种争论的成果,也是一份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答卷。
阿隆重回高校后,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立场。在学术探讨之外,他更迫切的关怀在于现实政治,即如他所说的受韦伯的影响:1957年阿隆拥护阿尔及利亚独立,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阿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1968年阿隆反对学生运动带来的社会分裂……
在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阿隆没有幻想,更不抒情,而是面对严酷的事实,站在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深度,通过在媒体撰文,对每一件重大事情都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从来没有向巴黎流行的思潮妥协过也没被裹挟过,没有首鼠两端,也没有什么政治正确,也毫不在意同代人乃至朋友的意见和立场——最著名的分道扬镳,就是与他的“小同学”萨特的决裂。
直到1979年,萨特在别人的搀扶下两个曾经的老朋友才重新有机会坐到一起——忠于自己对社会负责任会付出代价,阿隆并非不知道。“他们孤立无援,他们的影响(至少在平生大多数时间里)减弱了,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很少能与在国外友人和拥趸中的声望相比。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托尼·朱特)
即使站在了时代流行思潮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对立面,阿隆仍有勇气忠于自己,“我自以为对自己是忠实的”,“忠于我自己,忠于我的理念,忠于我的价值观和我的哲学。”这是因为阿隆有“对人类崇高的信念和深沉的爱”。(托多洛夫)
正如托尼·朱特指出的,阿隆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抵制、拒绝温和适度的主张以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恰恰在为不适度的东西扫清道路。极权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简言之,就是要看到秩序及依法实施权威的重要性——这并非是对自由的可耻让步,也不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由所需的条件;而仅仅是保护那些已得之物的最佳方法。(《责任的重负》)
阿隆与基辛格成为朋友,是其作为现实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分析家的另一种表现。基辛格曾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更孤独,也更空虚。”这是现实主义政治分析家之间的惺惺相惜。
阿隆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持着哲学家的信仰,对事物持怀疑态度,而不是否定态度,他没有忘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只是老老实实地理解自己的时代,所以,没有沉陷在过去的错误里。“我相信,我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我对希特勒没有幻想,我对斯大林也没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国可以通过法属阿尔及利亚实现自我革新。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的厚待。”


萨特(左)与阿隆,1979

四
托尼·朱特曾委婉地惋惜阿隆一生花费大量精力与人论战:“在知识分子圈当中,阿隆那样真正的自由派思想家将他们巨大的天赋过多地耗费于一遍又一遍地指出他者的错误和过失----雷蒙·阿隆最有趣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中一部分(如《知识分子的鸦片》)便出自对其对手(包括昔日好友萨特)观点的回应。这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但是显然,这几乎是一种次要的、屈尊的事。雷蒙·阿隆的自由主义在延误了差不多30年后,最终在其自耕地上繁荣兴盛。”(《未竟的往昔》)
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及其学生追随者的批评,一方面来自他眼里的政治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们的哲学或道德谬误——“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的责任的倾向”,阿隆由此认为,“他们的罪过不仅在于狂妄放纵,还有思想智识上的渎职。观察家、评论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
正是在现实的论战中,阿隆的睿见表明这个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站在了时间一边。他一生不遗余力捍卫了理性与自由的价值,这是启蒙的遗产。
“我们希望知道出于什么理由我们做出了决定,然而我们发现我们做出了决定却没有理由,甚至违背了所有理由。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恰恰是最好的理由。因为已经完成的行动,符合我们的全部心情,符合我们的思想和追求……总之,符合对幸福和荣誉的个人看法。”1977年,雷蒙·阿隆从《费加罗报》退出后,引用贝格松的话回答了友人絮费尔为什么离开的质疑。
“与盲目狂热和玩世不恭相反,最好的解剂是保持理性。”尼古拉·巴弗雷,阿隆的传记作者在《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中写道。
阿隆是一位秉持启蒙思想的人。“与其说他要激励人心,不如说他要启蒙思想。而且,他所带来的光明,不是一闪而过的闪电,而是不断点燃蜡烛时发出的闪烁光芒。”托多洛夫在为《回忆录》写的前言中这样夸奖阿隆。阿隆完全配得上这样的盛誉。
2017年12月,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与腾讯文化联合举办的《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好书评选时,我强烈推荐了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版本的《雷蒙·阿隆回忆录》。这是我在2017年最期待的一本书,尽管它在国内并非第一次出版,此前三联书店和新星出版社都有出过。但是,除了旧版已很难买到外,在我心中,这个时候出版增补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当下性。阿隆及其反对者和过去的20世纪,已经从不同角度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出了镜鉴。
在历史再度面临大转折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伦理不在于对集体冲动阿谀奉承,也不在于激化仇恨和不满或鼓励人们诉诸武力,他们应该为了平息紧张和冲突而去帮助阐明现代性的困境”。
“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和公民情操”, 在历史加速的关键时刻,像雷蒙·阿隆,“我们必须投入自由的事业”,“捍卫自由与理性。”巴弗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