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蝈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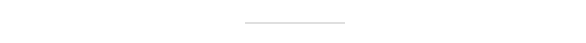
从小到大,我一直挺幸运的。
一路走来,一直有很好的朋友相伴左右。有些好朋友,因为地理的不同,时间的流逝,或许渐渐淡去了。可往往再次相见,又如昨日般滋润心田。
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你来,贵的请不起,但我有什么,你有什么。
认识马修是在我研究生最后一年。
开学不久,班里选班代表。马修毛遂自荐。虽然最后没有被选上,但大家都对他多了几份熟悉。
后来一次上课,刚巧坐在他身边,就开始聊起来。研究生班里的学生很多样化,一部分是已经有从业背景,再过来进修的。马修就是其中一位,他也是班里唯一的尼日利亚学生。我对尼日利亚的了解大概就停留在这个国名上,所以很热情地问他家乡的情况。
马修简单答了几句,然后道:“你对尼日利亚知道得不多吧。在法国,我们国家的名声很不好的。”他的口气出乎意料得直接。
“为什么?因为移民吗?”我理所当然觉得是移民问题。因为历史原因,许多北非西非的人偷渡来法国,钻福利政策的墙角。
我愤愤道:“哪个国家没有蛀虫,不能一概而论啊。说起来中国人在法国不也被歧视。巴黎人还歧视外省人呢。 ”
马修淡淡地笑,再没有详细说明。
这一年大家都过得很辛苦。所有的专业课压缩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同时就业的压力也随影而行。因为和马修渐渐相熟,很多专业课的小组讨论和他分在了一组。我渐渐发现马修是一个很出色的学习伙伴。或许是得益于之前的工作经验,他对于很多的专业课都得心应手。更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每次小组作业,他不仅严格按照计划进行,而且会查阅很多相关资料,保证作业的质量。
我很高兴在学业最后也最关键的一年,有这么一个好伙伴。期中考评一出,我们组大部分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有些我并不擅长的科目,因为有了马修,也被平均成了高分。
除了功课外,他在许多方面都像前辈,甚至长辈般照顾我。投简历时的问卷题,马修会仔仔细细帮我修改。他不仅对金融行业了解,而且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所以在语言表达上,他也帮我润色不少。
后来见面多了,也开始聊彼此的生活。原来他结婚多年,前年喜得一对双胞胎儿子。他告诉我,来法国进修的主要目的,是想以后能移民来欧洲,这样两个儿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他说得很坦白,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也感叹我一个人背井离乡,父母都不在身边,不容易。
还记得圣诞前和好朋友去希腊玩。临行前一天放学,马修拉住我,“你要去希腊了吗?”
“是啊!”我很激动。
“好好玩。希腊很美的。”他拉起我的左手,掏出20欧元放在我手心里,“买点好吃的。”
我愣在原地,本能地拒绝,“这……你怎么能给我钱呢?”
他把我的左手,连同我手心里的纸币一起攥在他手里,“你收下,在我们尼日利亚,小孩子出去玩之前,大人给点零花钱是习俗。我今年35岁,可以做你的Uncle了吧。”
在法国,每个人都是很独立的个体。不要说同学朋友之间,甚至父母与子女都维持着所谓尊重的距离。马修的举止,一下子让我有了祖国文化的亲切感。朋友们,直到现在我想起他这句话,仍然很感动。我愿意相信他做这件事,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出自真心的。
在希腊回来之后,自然而然地,我就叫他Uncle了。
下半个学期,我和马修成了固定拍档。有时候功课紧张,下了学,我还会去他宿舍研究作业。他的宿舍很干净,除了生活必需品,只有学习资料。他常常和老婆奥比在Skype上聊天,我也会和奥比打招呼,隔着屏幕逗逗双胞胎。我每次总是猜错,马修就安慰我,没关系,他们两个唯一的区别是其中一个屁股上有颗痣。不过,他们的性格天壤之别,一静一动。如果有天我见到他们,马上就能分辨出来。
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学生叫罗伯特,是个做律师的老男人。我对他一时倾心。有一天在马修宿舍写作业,写了不一会儿,罗伯特发来一条信息,“What’s up? ”(做什么呢?)
我顿时心花怒放,再也无心向学,跳起来就要出门。
马修拦住我,“是罗伯特吧。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Uncle......我要去见人家......”我在马修面前从来恬不知耻,直话直说。
“哎。你们这些小姑娘呀。太不懂男人心了。”
他居然开始和我谈起感情生活来,“想当年我和奥比……”
我好奇了。坐下来听马修说。
“奥比当年可是班花。多少人喜欢呀。我喜欢她三年,可我觉得自己不优秀,她肯定不喜欢我。所以也一直没有表现出来。结果后来她反而来找我了。”
“其实她喜欢你?”
“才不是,她来找我,盛气凌人问我一句话,‘所有男人都喜欢我,或者追我,为什么你连话都不和我说?’”马修笑,“她不知道我也喜欢她。她只是被自己的骄傲打败了。”
“所以这之后你就和她好了?”
“也没有,我只是开始和她出去玩。也没有主动做过什么。”
“那你什么都不做,你们之间......”
马修不动声色地笑,“人的感情是藏不住的。可以说在口里,也可以看在眼里。我什么也不需要做,只要静静看着她。她就懂了。她就靠近来吻我。”
我恍然大悟。腹黑啊这是。
他拍了拍我的头,“所以小姑娘,你这么着急做什么。该来的会来的。自己不要乱了阵脚。”
每次深夜做完功课,马修都会送我回家。我家和他宿舍离得并不远,走路十五分钟就到了。不过因为远离市区,治安并不是很好。他个子很高,超过一米九。瘦,也结实。往我身边一站,比保镖还有安全感。
我脑子里想着罗伯特,又看他一表人才,口不择言道:“Uncle,你老婆孩子都不在这里,会不会寂寞?”我潜在的意思是,难道你不会想找个女伴吗?
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不寂寞是假的。天天看着班上金发碧眼的女孩子飘来飘去,能不动心吗?”他狡黠地眨眨眼,“你知道吗?伊莎贝尔那天还约我出去呢。”伊莎贝尔是班里典型的美女,有俄罗斯血统。
“真假的!那你去了没?”
“当然没有。”他耸耸肩,“诱惑是诱惑,行动是行动。说起来,寒假快要到了。奥比会带着孩子来这里玩。到时候我们会一起去英国和卢森堡。”
“卢森堡?”我诧异,这个小国家在欧洲众多繁花似锦的国度里,几乎是被遗忘的。
“这是奥比一直以来梦想的国家。你要知道为什么,到时候问她咯。”
在那个冬天,我见到了马修一家人。
他学术味道浓厚的宿舍因为两个孩子的到来,一下子变成了孙悟空的花果园。马修给儿子们买了全新的宝宝车,还有很多玩具。他说非洲小孩子的东西少又贵,质量还不好,若能带得下,都在欧洲买了。
奥比看起来比在网络上沉默些。友好地打完招呼,便一直忙着照看两个小宝宝。果然同马修说的,其中一个孩子总是猴子般跳来跳去,另一个总是赖在妈妈怀里。
因为家人到访,之后我就没再去打扰马修。
再后来我们都开始忙着面试,直到考前才碰了次头。
马修告诉我,他过了瑞信银行的三轮面试,就差最后一轮了。我高兴道,“太好了,这样你们全家以后可以去英国了。”
他笑,“英国那么贵,除非单位安排住房,要不然一家三口在伦敦,租房就得压死我。”
“那瑞信会帮忙解决吗?”
“要看我做多大的职位咯。”他皱了皱眉,“不过,上次我们全家人来,消费得很厉害。如果又要去英国,怕是负担不了。”
“哎?你身边没有钱了?”印象中马修不是缺钱的人。
“没有没有。”他连连摆手,“我的钱都在尼日利亚的公司里。刚好前阵子买了块地,所以没有带很多出来。只是现在要转账过来,短时间怕是到不了。”
“那要不我先借你路费?”我不假思索道,“伦敦很近啊,一百欧都不到。”
“你方便吗?”他看起来有些尴尬。
“没问题啊。”我取了一百欧元给他。
过了不到一个礼拜。马修回来了。他一见面就递给我两张五十欧,“谢谢你啊。我面完了。转账也到了。”
“面得如何?!”
“不太好。好像他们找到了新的人。”马修口吻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情绪。“我在考虑申请博士学位。这样可以让学制长一些。”
“你考虑去英国还是美国?”
“我申请了墨尔本大学。那里有个导师是做经济学研究的,很出名。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去了。”
“Uncle,你肯定可以的。”我给他打气,也给自己打气。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谁不煎熬呢?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马修也开始和墨尔本大学的那位导师联络。一切好像如计划中进行。突然有一天,马修来找我。他看起来很憔悴,胡子拉碴。
我认识马修起,他从来没有蓄过胡子。我问他:“出什么事了?”
他苦笑道:“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奥比和别的男人好了。”
“什么?!不可能!”我跳起来。在我眼里,奥比生活里除了马修就是两个孩子,典型的非洲传统女人。
“我也不相信,可是我看到了。她和我视频的时候,后面有陌生的男人走过。”
“那,你问奥比了吗?是不是误会了?”
“她否定,还在电话里和我吵。我后来查了,她那天根本就不在家里。她其实是在那个男人家和我视频。”马修语气确凿,“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要求要看孩子。结果她借口说孩子不在家。”
我愣了。“Uncle,不管你怎么确定,都可能有误会,你一定听奥比解释,才能知道事实。”
“我也知道,可那次挂了电话后,我再也联系不上她了。”
“你怎么联系不上她?你为什么不回去?现在考试也结束了,你墨尔本那边有网络就可以,为什么不回去?”我替他着急了起来,“你一定要回去。很多事情,你就算联系上她,隔着距离也是说不清楚的。Uncle,家庭比什么都重要,你还有两个儿子呢,你有什么放不下?”
“我也想回去。不过我现在连机票都买不起。”他终于说。
“为什么?你上次不是告诉我你买的地还赚了很多钱吗?”
“因为......”他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这件事,毕竟关系到奥比的名声。在查清楚前,我不想下结论。你既然在这里,我告诉你也无妨。奥比拿了公司的钱。所以我现在身无分文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
“她是有财政签字权的,当然可以动我的钱。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带着我的钱和我的孩子们,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
“跑了?跑了是什么意思?”
“我们全家和他们全家都联系不上她,也找不到儿子们。她肯定是和那个男人走了。”
“那你还不回去找她?”我气急败坏地说:“你飞回去要多少钱?我先借给你,你回来再给我。”
马修很认真地看着我:“你真是太好了,我并不是一无所有。除了公司的钱还有我们的共同财产,我自己也有结余。我回来一定会把钱还给你。”
“哎,你一定要找到奥比,好好和她说,不要吵。你告诉她要见儿子,她肯定会同意的。”
我给了马修一千欧元。银行每日取款有限,我连着两天去取款机取款。马修坚持要陪我。学校附近治安不好,有些阿拉伯人常在取款的时候强取豪夺。
马修走的那天,我还特地去机场送他。我百般强调:“Uncle,一定不要和奥比吵。不管她是不是背叛你,为了孩子,一定要坐下来好好说。”
又过了几个月,我的毕业实习结束了,开始正式上岗。期间我和马修在Skype上很短地聊过几句。他说他和奥比见面聊过了,没有挽留的余地。他已经上诉离婚,希望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不过有个好消息,墨尔本大学录取他了。开学还有几个月,他趁着这个空档,和几个朋友去加纳做项目挣钱。
“所以奥比那边的钱,你还是没有能够要回来吗?”
“没有。她那么有计划地要离开我,我怎么可能要的回来呢?”
“那你在墨尔本的学费怎么办?”
“博士生是半工半读的,加上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都差不多够了。”
“那就好。Uncle,你不要担心,你条件这么好,教育背景又好,法院肯定会把孩子判给你的。”
“希望了。我想澳大利亚的教育也不错,孩子们过去也好。只是,希望加纳这里尽快能拨钱下来,要不然,恐怕就算录取我也去不了了。”
“为什么?不是学费生活费都够吗?”
“他们注册需要交定金2000欧左右。如果九月开学前我不缴清,自然就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算了算,离九月还有不到两个月,“这么赶!那你项目的钱什么时候能够拨下来?”
“你也知道非洲,从来都是不规范的。一般都是过一段时间一起结算,没有固定时间一说。”
“那也就是说九月前不一定能发了?”
“不一定。”
“Uncle,墨尔本大学都录取你了,你肯定要去啊。我现在也没有钱,不过7月底我会发工资,到时候我帮你先垫了。”我说得斩钉截铁,生怕他拒绝。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我最受不了他这么说。“快把账号给我,我转好了告诉你。”
我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没有给父母,没有给自己买衣服买包,全数汇给了马修。他给我的账号是在加纳的。银行负责人处理的时候有些犹豫,暗示我这些地方的银行都不是很规范,让我三思。
我恨不得早些能汇到马修手里,让他了却墨尔本的注册费,莫说三思,一思都没有。
马修在三日后邮件确认我,钱收到了。
又过了一个月,他说墨尔本那边都弄好了,会直接飞过去。我问他:“你见到奥比了吗?开庭了吗?”
“没有,奥比一直拖。上一次开庭的时候都没有到。我委托了律师,要年底再审。”他的网路信号不好,带着很多杂音。“这种离婚的民事案件,一般都会拖很久。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争取到最后。”
我汇钱的这件事,同屋室友小洁,也是我在尼斯最好的朋友,是知道的。她提醒过我,这么大的数目,还是要谨慎点。她问:“上次你借他一千欧的机票,他还给你了吗?”
“他还了250,剩下的他当下没有钱。你知道的,他老婆把他所有钱都拿走了。”我义愤填膺。
“你这是听他说呢。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只是要你的钱?”小洁婉转道。
“怎么会!我们都认识他啊,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我自信不疑,“何况,他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都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是吗。其实我和马修根本不熟。”小洁叹道,“你既然决定了,多说也没有用。如果是骗局,就当花钱买教训了。”
我不以为然。想她只是和马修不熟,没有足够的信任感罢了。
又过了小半年,小洁找到了好的机遇回国。
我继续忙着工作,偶尔会和马修在Skype上说说话。可能因为时差,每次对话都很简短,他不是正在去上课的途中,就是忙着要临时授课。
我们彼此再也没有提过钱的话题。
汇钱后整整一年,我没有半刻怀疑过马修,甚至没有过想要催钱的念头。每次对话,我最先问的总是功课还好吗?孩子还好吗?离婚有结果了吗?
我是那么相信他。相信我们共同走过的美好又艰难的一年。
直到一年后,奥比有天突然在脸书上和我说话。马修自己没有脸书账号,很早就给了我奥比的。不过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对话,奥比也很少更新。
奥比的头像还是全家四口的合照。我又是惊愕又是欢喜。惊愕的是奥比怎么会在一年后联系我。欢喜的是,我终于可以和她对话,劝她有没有回归家庭重修旧好的机会。
我按捺不住,几句寒暄后就直接问她,为什么要消失,为什么要出走?
她给我发了一连串问号和惊叹号。她说,给我你的电话,打字说不清楚。
在窄窄的楼梯间,我抱着手机和奥比说了两个小时。面试巴黎银行的时候,我都没有过如此的心跳。
奥比告诉我,马修从来都没有找过她。她却一直在找马修。两个孩子也喊着要见爸爸。可是马修回来后就消失了。
然后她收到了马修的离婚协议书。她看到马修和别的女子开始出双入对。她找到马修家里的人,全家人都不明白马修是怎么了。她现在除了上庭能见到马修,再也找不到这个人。而马修,除了法庭强制传召,一概缺庭。
这简直颠倒乾坤!
我愤怒了,我不相信她。她说的每个字和Uncle说的都是相反的。
我说,马修也和我说过你们之间的事情。他说你和别的男人走了,带走了孩子,带走了他所有的钱。他没能留在英国,现在去了澳大利亚。
奥比沉默了。
过了良久,她问:“你知不知道马修是什么样的人?他如果没有我,根本不可能去英国。”
“?!”
“因为他之前在尼日利亚银行做过不规范的行为被开除,被英国永久拒绝签证。他能去英国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家庭。所以上次我来法国,一起去办了签证。”
“他被开除?”马修告诉我,他离开尼日利亚,是主动辞职的,想要来欧洲发展。
“是。当时还闹得很大,他们单位在全国都发布了声明。我可以扫描给你看。”
奥比凄凉道:“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一直没有想到我嫁了个这样的人。他坚持要小孩也是谎言。他发给我的离婚协议上,完全没有提及小孩。他要和别的女孩子好,怎么可能会要孩子这个累赘呢。”
我脑子嗡嗡响。不知道去相信哪一方。
“他有没有向你借钱?”奥比突然问我。
“有。”
“上帝啊!”她叫起来,“请千万告诉我数目不大。他在这里借了各路朋友的钱,大家上门向我讨说法,我真的很羞愧。”
“你是说,他不会还钱的吗?”我抖抖地问。我的心开始慢慢往下跌。
“上帝保佑他会还给你。如果他还有点良心的话。”奥比是很忠诚的基督徒。在电话的最后,她一直重复这句话:“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我想马上联系马修。
我发现,除了Skype这个方式,好像再也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联系得到他。上学那会一直联系他的邮箱是学校的,现在已经废置了。这么一路走来,从未觉得他如此远不可及。
马修的状态是离线的。我安慰自己,是时差罢了。我给他留言:Uncle, 最近好不好?
马修在学校的时候,回复Skype一直是非常快的。
我等了一天,没有回复。却收到了奥比的邮件。
如她在电话里的承诺,她扫描给我马修单位的声明文件还有他们的离婚协议书。如她所说,马修之前工作有问题,他也没有要孩子。
我想说服自己,奥比才是骗人的。
可是她为什么要来骗我?她在我这里无利可图。如果她要消失要私奔,为什么要来找一个马修的朋友说话。
我给小洁电话:“小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个骗局?”
“没有。只是这么大笔数目,加上他之前又没有还你的钱,难免疑心。”
“是吗?”我呆呆地挂下电话。
我真的很震惊,真的很伤心。
如果说我震惊的是马修骗了我,那我更震惊的是在与他相处的一年多的日子里,我竟然没有一秒怀疑过他。我不仅相信他,甚至连小洁警示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在心底里维护他。
如果说我伤心的是我不知所踪的钱,那我更伤心的是原来一直以为在异乡最艰难一年共同走过的好朋友,只是我的一场幻觉。我的掏心掏肺不仅是一厢情愿,更可能是助纣为虐。
这样的现实太残忍。
我在心底某个角落还是留给自己隐约的希望,希望自己没有瞎眼,希望马修心里还有我们的友谊。
马修在一个半月后终于回复我。他说最近身体出了问题,住了一阵子院,所以没能和我联系。
我知道我在心里已经不信任马修了。我没有告诉他我和奥比的对话,只是再普通不过地问候他的学业,问候他离婚的事宜,让他多保重。
马修的回答一如既往,学业很忙,离婚无进展。
我终于忍不住:“马修,你还记得借我的钱吗?什么时候能够还我呢?”
马修很快回复:“当然,我亲爱的小姑娘,我怎么会不记得呢?这里博士的工作四月末会发薪水,到时候我一定给你。”
他又说:“下个月我会来尼斯,学校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我们见见吧。到时候我直接把钱给你。”
我心里燃起一线希望,难道说,马修其实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马修?
一个半月很快过去。那天我照常在单位上班。
午饭过后去茶水室,一出门,马修高大的身形立在我面前。他看起来完全没有变。我看着他,情绪有些复杂。没想他一把横抱起我,原地绕了一圈。“嘿嘿,我的小姑娘,晒黑了啊。”
我措手不及,跌在他怀里。突然也高兴了起来。“Uncle,好久不见。”
我们在走道聊了一会,我说:“Uncle,我现在上班不太方便多说,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的飞机,你今晚有事吗?”
“我空,出来吃饭好不好?”
“好。”他亲切地看着我笑,一如当年。
我趁兴问他:“你方便还钱给我了吗?”
他保持着笑容。“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又有些紧。我下个月打你账号上可以吗?”
我心里黯淡了下去。木然地点点头。不然又能怎样呢?
“马修,你还用法国的号码吗?晚上我怎么联系你,我们哪里见?”
“这是我非洲的号。你也可以给我邮件。”他在纸上写了两行。“我去了市中心,找了地方,告诉你。”
回到办公室,我意兴阑珊。在心下隐隐约约的疑惑和猜忌慢慢浮现上来。
直到下班,我没有收到他要告诉我见面的地方。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邮件。
我拨他写的电话。拨了三遍,是空号。
我给他邮件,简短三行,马修,哪儿见?盼复。
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回复。
看着他熟悉的字迹,心彻底冰冷。
过了几乎半年,马修回复了我的邮件。依然是:抱歉,有急事,没能回复。
每次看到他在Skype上线的消息,我总是忍不住等待,等待他会和我说些什么。
他什么也没有说。
如果我主动问候他。他会一如往常地回复我,一切都好,很忙,还没有离婚。
如此又过了半年。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又要来尼斯。
在这半年里,我忍不住反复想。
我想我们一起念书考试的日子,那些整齐的笔记,大片的演算,现在还存在书架上。
我想我每次回国前,20KG的大箱子,他一手一个一直送我到安检门口。
我想我在接到第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他一把抱起我,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先把握。小姑娘,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你会得到最好的。
可我又想,难道瑞信的拒绝不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者,而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背景调查。
难道他那些对奥比还有两个宝宝关爱的举措都是一场戏,那些担心忧愁愤怒都是假的,而抛弃妻子和对奥比的欲加之罪才是真的。
难道像奥比说的那样,他离开尼日利亚,又离开法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在这些地方继续他的谎言。或者其实他现在根本就不在澳大利亚。
难道他从买飞机票开始就在算计我,甚至更早。可是他却也从来没有主动开口。
还是他算准我会开口,好像当年他和奥比那般。他知道,如果感情到了,谁开口只是时间问题。
又或许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真的一时没有经济能力来偿还。好像他解释的那样,他羞于开口,所以选择沉默,选择逃避。
我头痛欲裂,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是什么。
可我确定地知道,马修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听信谗言也好,我计较回报也罢。我对他的信任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慢慢分崩瓦解,散落了一地。
我再也不能忍受彼此这样假情假意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