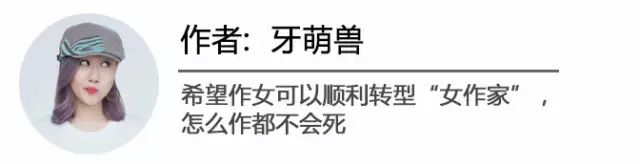《当男人恋爱时》剧照
交了五万块之后,他们就开始教我如何“带人”了。我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过去遇到的所有“巧合”,无非都是精心安排的结果。
前言:
当李文星的尸体出现在天津静海的水坑里时,网络上关于南派、北派传销的各色曝光才终于热闹了起来。
两年前,在毕业一年后被骗到异地做传销我,曾一度不愿意面对那段过往。
最初那几个把我连哄带骗拉入伙的人,他们真实地出现在我刚毕业、最迷茫的那段时间里,以朋友的身份靠近,以骗子的身份远离。
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没办法把自己和他们完全对立起来。
大学毕业后一年,公司项目中止,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业。早已不可能像应届毕业生一样去参加校招,而社招也因为经验不足,接连宣告失败。
在焦虑且没有目标的日子里,家人和老友的关心,让我喘不过气来。趁虚而入的“新友情”,越发容易获得信任,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
把那些“新朋友”介绍给我的人叫沐元,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一个小创业团队做运营。
再次和我联系的时候,沐元已经离职。那时候百无聊赖的我去西藏旅行,一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手绘的漫画,把纳木措湖画成了一只猫的脸,朋友都说我,“你又不能靠画画赚钱,净干些浪费时间的事。”我无力反驳。
只有沐元点完赞后,还配上了好玩的点评。
● ● ●
那时候,我执意要留在北京,妈妈拗不过,只好把我托付给亲戚照看。可亲戚也只是劝我,“刚毕业都不好找工作,你自己很难在陌生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听话,回家去,我和你妈都会想办法。”
大学同学都有了不错的工作,有几个甚至开了自己的画展,得到了有名气的批评家的赏识。他们愉快地抱团取暖,我只能退缩。
只有不算熟悉,交情尚浅的人,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联系。
旅行回来之后,沐元约我见面。他鼓励我,完全可以留下来做自由职业,无论是靠写文案,还是画漫画,深谙运营之道的他,愿意帮我去找客户。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喜从天降。
而且,他也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在之后的一个礼拜,沐元为我介绍了两拨人,一类是有可能成为我客户的人,几个留学生,一个个年轻、聪明。另一类则是他的“朋友们”,聚会时,他们似乎都非常贴心,像认识很久一样,安慰我、听我倒苦水,让我感觉很温暖。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沐元专门为我安排的家族成员——在这个“家族分支”里,我是沐元选择出来的下线。
他已经开始为后续的一系列“控制”做准备了。
我和沐元的“朋友们”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一个男生叫文森,画着细细眼线,留着寸头,长相清秀;一个叫姜山,喜欢戴着印有“北京暴徒”字样的鸭舌帽;还有一一,略带些神经质的漂亮姑娘。
后来,在我正式进入组织并接受培训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都在一个济南传销组织的“家族”里,一一是“家长”,是他们几个人中级别最高的,“二家长”是姜山,他的“孩子”是文森和沐元。
按照他们体系的划分,我是沐元的直系“孩子”。这种叫法,很难在真实世界里叫出口,但是在济南他们租的那十几座房子里,彼此报家族、认家长,是每天都要重复很多遍的事情。
一开始,我就对文森尤为信任——如果信任是彼此暴露秘密,那么发现他的同性恋身份并得到他的肯定,的确让我和他迅速熟络起来。
文森有女孩子的细腻,声音温柔,那时候,我们常常聊天到半夜。
“相信我,你没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是那个男人瞎!”他总是这样,让原本还在默默流泪的我,在深夜破涕为笑。
● ● ●
许多事似乎都是因果相连。自始至终,我都对文森充满了信任。
那时候,文森在二环内一家叫“野樱桃”的咖啡馆上班,自从认识他之后,那里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画画、写作,或者只是坐着发呆。复古的装饰,吧台上一串串小灯亮起来像星星一般。
当然,后来,当沐元把我第一次带到济南之后,再回到北京,我才发现,这家咖啡馆原来就是家族众多联络地之一。
可那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
很快,沐元得意洋洋地告诉我,有一个项目需要插画师,而且负责人和他很熟,他觉得我很合适。
我也很开心,当即让沐元帮我定了车票。
到济南的那天,我并没有住进宾馆,而是住进了他们安排的在一个小区里的三室一厅,刚进屋,我就连着问了许多关于这次行程和“面试”的安排。沐元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但尽量表现出幽默机智,边和我开玩笑边安慰我说,“不要担心。这次你能来,是件大好事儿,明天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起床洗漱完,吃着沐元买回来的早餐,满心期待着,到底会有什么好事儿发生。就见沐元掏出一只老人机,接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一个卷发的姑娘走了进来。
她自称是一名剪辑师,聊了一会儿天,开始给我讲述起一套闻所未闻的“经济理论”。我还挺奇怪,不知道这和自己即将做的“项目”有什么关系。从数字裂变实验讲起,到“五进三”模式,我一头雾水,她甚至掏出笔和纸,认真地画了起来。
我忽然有点警觉,借口上厕所的时候,迅速用手机搜索起这些名词。它们无一例外,都指向另一个关键词——“传销”。
从厕所出来,我直接回了自己房间,关起门,不再理会屋外的沐元和陌生女人,紧张得收拾起行李。
“她已经走了,你出来吧……”屋外,沐元声音有点怯生生的。去意已决的我,开门的时候却傻眼了,客厅里赫然站着文森、姜山,还有一一。
当时,没搞清楚状况的我,一下又看到了这么多老朋友,除了惊讶和惊喜还能说什呢?
文森拍拍我的肩膀,“我们也是好心,真的想帮你,也怕你有误会,回去的票就在这,你要走现在就可以走。”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无奈,反倒像我误解了他们的好意。
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屋里一直在来“客人”,沐元他们去忙碌的时候,文森就留下来陪着我。
短短一早晨,屋里就来了三拨陌生人,每小时一换,中午午饭过后,沐元、一一开始带着我去“串门”。都是在相邻小区的不同房子里,两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这套“带人”模式,上楼之前,先打电话,进门介绍,离开时带垃圾下楼,礼貌、有序,像经过了特殊训练。
回想起来,这一天见过的所有人,都和我有某些关联,要么是念过同一所大学,要么就是学过画画或者设计。话题也都从聊天开始,以组织结构介绍结束。
所有人讲得内容都类似,大体就是,这个组织,是把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带到济南,组成一个“俱乐部”,大家一起玩一个叫“五进三”的游戏。当说到“这个游戏能赚多少钱”的时候,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扬起野心勃勃的脸,告诉我这里发生过了哪些“奇迹”。
一天下来,我听了太多故事,回到住处,没有时间多想就沉沉睡去了。
接下来的两天,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运动轨迹。
“我们资金是安全的,你看我们租了那么多房子,还能跑咋的?”
“你还小,就遇到这种好事,说明你遇到真心对你的朋友了。”一位东北口音的胖女人言之凿凿地对我说,后来,她的话像印在我的脑子里一样,不断地回放,再回放。
“我们怎么会是传销呢?传销都会打你,饿着你,可是你看你是自由的啊。”
这是文森说过的、也是所有人对我说过的话里面,最动摇我的一句。
第一次济南“考察”之后,我想过报警,也试图联系北京的朋友,但最终都没有实施。最让我犹豫的,就是文森。他那么真诚,怎么可能骗我呢?
从济南回到北京之后,我下意识地警觉起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在文森给我灌输的新价值里,从前所谓的“朋友”,都是利用、欺骗过我之后,把我从他们的利益圈子中远远地推出去,只有沐元和他们济南的这些“朋友”,才是值得信任的。
很快,文森的情感攻势更加猛烈起来,“只要你交钱,你就是家族的成员,你是沐元的朋友,我和一一他们在帮你,也是在帮他,他上了新的级别,就会有钱分。”
沐元也一直追问我。我只好用现在钱不够的理由拖延着。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沐元也带了别的人去济南,他很着急,因为一个人只能邀请三个人入伙。
一天下午,在咖啡馆,文森从我的手机通讯录里,翻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与我联系密切的人,“你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去检测,测验你通讯录里的这些人,谁会借钱给你,谁是欺骗你的感情。”文森提议我去向别人借钱。
随后赶来的姜山提出了另一套说辞,“你现在找他们借钱,以后从俱乐部里赚到了,再还给他们就是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随后,我用了三天,问过去的朋友们借了三万块,加上自己的存款,一共五万,一起交给了姜山,而他把钱带去了济南,交给了更为神秘的“大家长”。
等我第二次到济南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家族里的“三星会员”了。
来到济南的第一天,他们就开始教我如何“带人”了。
我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过去遇到的所有“巧合”,那些“信任感”的建立,都是精心安排的结果,恐惧油然而生。
我依旧对文森还是抱有信任的,第二天晚上,我发微信向他求助,“我现在该怎么办?你也是被逼的吧,我的钱现在是不是在姜山那?你告诉他我退出,骗人我做不到的。”
可没想到,自己的求救很快使我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地。因为文森把我对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了这一分支的上级。
转天,一位五星级别的“家长”便来找我谈话了。和在这里见到的其他人不同,那些人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可这位家长则是长久地坐在沙发里,面色凝重,他知道我的所有过往,他把那些悲伤的回忆添油加醋的再重复一遍,一句一句,像耳光一样。
一个小时的逼问后,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下午,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按照电话指令,穿梭在不同楼栋之间,乖乖地听那些规章,器械地背诵着。
等再次回到住的地方,已经有“新人”来做客了,我被要求着,参与聊天,参与游戏。游戏的时候,早就神情恍惚的我,接连犯错,甚至认不清自己手里扑克牌的图形。
文森总会在一边打圆场,替我圆过去。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但唯一确定的是,如此善良的文森,肯定不是故意在骗我,这里的每个人都被什么东西胁迫着,像是着了魔。
● ● ●
夜晚十二点已过,这里的人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睡觉,但是只要有谁睡不着,其他人就会来找你聊天。
假装睡觉的时候,我发了疯一样发信息给文森,“不要再告诉别人我说的话,现在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
“我知道你也被迫的,我的钱还在姜山那里么?我要退出。”
在几十条这样的问句后,文森回复我,“你从这里拿不出来钱的,除非继续骗下去。”
我告诉自己,钱可以不要了,但必须摆脱他们的控制。
第三天清晨,我开始雷霆大作起来,骂每一个看到的人,破坏性地摔东西,像失心疯了一样。
没人敢拦着我,我带着行李直接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除了尖叫,就是大哭,用上全部能量吸引路人的围观。
我想这样,他们就不会来追上我了。
回到北京,我立刻打电话给撸总求助,撸总是沐元之前所在的创业团队的领导,也是我和沐元共同认识的、最后一个和此事无关的人。
撸总告诉我不要再联系山东认识的所有人,还挨个打了很多电话,告诉所有他和沐元共同认识的人,远离这个魔鬼。撸总告诉我,“一个人去战胜心性的魔障很难,一千个人没准能战胜,但也不要迷恋归属感。”
也许是撸总的扩散起了作用,沐元和我通过沐元认识的所有人,都没有再找过我。这件事最终留下的,除了债务,还有更加脆弱的神经,无异于一次信任的灾后重建。
上班,打工,远走南方,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偿还了所有债务,可心理的余震却迟迟难以消除。
在很长时间之后,我给文森打过电话,所有在济南认识的人,我都没再联系过,只有他。我至今仍旧相信,文森并不想强迫我做任何事,只因为他同样是被强迫的。
我问他有没有继续在做这个,文森语焉不详,我不知该说什么,甚至连劝他离开都没有说出口。
编辑:沈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