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剧照
天空忽然劈下那道闪电时没有预警;我在车上偶尔往窗外看,发现那具尸体时没有预警;白衣年轻人在凶手拿出刀来之前没有预警;拉架的人忽然决定不打车而是坐公交车时,也没有预警。
回国一趟,出门办事,坐车路过家门口的公交站,看到马路旁有人围成一圈,像是出了车祸的纠纷。车开得近了一点,看见公交站牌前的马路牙子上躺了一个人,第一反应是有人喝醉了,仔细一看,发现他胸前一片殷红。
“有人被砍死了。”我镇静地对车上的人说。
下了车,步行过去看。那是你经常在新闻和微博上看到却不敢点开放大的画面:那人躺在垃圾桶旁边,还很年轻,30 岁左右,胖胖的,是那种毫无特征的长相——一时竟然判断不出是他本身长得就普通,还是死亡剥夺了他的相貌特征。他穿着白色的 T 恤和蓝色的运动鞋,左胸和右胸各有一两处刀口,致命的应该是砍在左胸口附近的一刀。
自行车道上——我原以为是车祸纠纷的地方,还有另外两个伤者,一个躺在地上,看起来已经没有了意识;另一个靠墙坐着,捂着肚子上的伤口呼呼地喘着气。
围观者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路过,骑在自行车上不断扭头衡量着事件的严重程度。固定的围观者是住在附近的老大爷们——
老太太们都在马路的另一边远远看着。老大爷们很冷静,不拍照也不呼叫,只是和事发现场保持着亲密而谨慎的距离。
● ● ●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把躺在垃圾桶旁边的白衣年轻人搬进救护车里。
“还有救吗?”围观的人问救护人员。
救护人员摇摇头,说:“没气了。”
自行车道上的两个伤者也被抬到了救护车上,只剩下两摊血迹。
警察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我听到他们打电话说要调附近的监控。
“凶手跑了啊。”我身边的老大爷向后到的围观者讲述案情。
“为什么砍人啊?”我插嘴问老大爷。
“等公车的时候,一个人踩了另一个的脚,那人就拿出一把小刀,扎进去……”大爷比画出一个手掌的长度,然后用食指戳着自己胃下面鼓鼓的肚子,接着说,“把拉架的人也砍了,然后就沿着天桥跑了。”
“以后不敢来这个公交站了啊。”有听众感慨。
● ● ●
这时,出现了一道闪电——一道如同恐怖电影里特效般标准的闪电劈开了灰蒙蒙的天,路人们皆受惊,或许想起了要在下雨之前赶紧回家,蹬了几脚自行车,都快速离开了。
“前方高能预警。”我脑海里忽然想起这句话来。准确地说,这是一句弹幕,看视频的时候,当主人公要进入一个黑暗的屋子之前、打开冰箱之前、刚结束一个愉快的约会之后,屏幕上方就会出现几行来自陌生人友善的提醒:“前方高能预警。”
看到这句话的观众,开始收敛原本轻松的心情,凝固住笑容,把电脑的音量调小,喝了一口水。然后看到主人公被一双手捂住嘴,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只手,在掏出钥匙开门之前被人用棒球棒打中后脑勺。观众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终于没有受到预先设想中的惊吓,纷纷留言:“感谢提醒。”
我一直怀疑,那些对后来的观众发出“预警”的人中,会不会有一些只是为了向后来者发出警告而重新看一遍这些视频?就像是好心人跑完一段全是埋伏的路,然后不断折返,为那些后来者指出埋伏的位置。
● ● ●
我们被大众媒体和影视剧惯坏了,总有种幻觉,觉得危险——尤其是死亡来临之前,会有些暗示。死亡会隐隐发出气味,或是稍微调暗了我们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我们控制生存本能的神经敏锐地接收到了这种信号,然后脑海里开始浮现巨大的黑体字“前方高能预警”。
这次近距离目睹死亡的经历对我最大的震撼就在于:这种预警机制是不存在的。天空忽然劈下那道闪电时没有预警;我在车上偶尔往窗外看,发现那具尸体时没有预警;白衣年轻人在凶手拿出刀来之前没有预警;拉架的人忽然决定不打车而是坐公交车时,也没有预警。所有目睹过这种突发死亡的人,人生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型机关被开启了。
对我来说,最显性的变化是我看视频时关掉了弹幕,我不需要预警了,我把它看作一个小小的练习,一个锻炼自己接受“无常”的练习。

作者蒋方舟在她的新书分享会上提到了自己近距离观察死亡的经历,以下是活动中她和陈丹青的对话。
● ● ●
陈丹青:你当中回国了一次,然后在路边看到了杀人。杀人写得这么感性、冷静,但是很有力量,一层一层写下去,最后写到什么“弹幕”?我没有搞明白这件事情。
蒋方舟:看视频的时候,屏幕上方会飘过一些字,这是之前看过视频的人留下来的,比如1分钟之后,第39分钟马上会有杀人案了,会有特别血腥暴力的场景,之前看过视频的人就会在上边写上“前方高能预警”——要出现恐怖的事情了。我觉得有点像点评粉,有点像《红楼梦》点评粉一样,能够看到前人留下的笔记。
陈丹青:我很爱写作,我要像你学习写得这么简单,你没有很冗长的议论和描述。我记得福尔斯写过看人杀头,也非常简单,两行字就没有了,后来我发现这是有效果的,他知道写长了没有效果,写短才会有效果。你写那么短我非常佩服,如果我看到一个人被杀了,就想注墨描写,结果你没有。
蒋方舟:会有很多心理活动,但可以调解到几乎为零。
陈丹青:好像用不着调解,是天生的,女人看到血和男人看到血不一样,女人比男人勇敢冷静多了,男人看到血一塌糊涂,我现在非常怕看到血。小时候亲手杀鸡、杀蛇,现在想起来跟野兽一样,现在电视都不看,很反感看到暴力,会遮起来,非常的奇怪。
蒋方舟:死亡是不好的,杀戮是不好的,但是对于作家来说,能够近距离的看到死亡,其实是一个挺宝贵的财富。
陈丹青:三个人为了被你看到,死了。我有一个观点,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被写出来等于没有发生,一点用都没有,白死了。
你写他在那儿躺的样子也特别好,一点特征都没有,而且是死亡让他没有特征,这很厉害,非常会写。
蒋方舟: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写,有过近距离观察死亡的经历。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和爸妈去公共澡堂洗澡,出门时看到对门的门是敞开的,觉得很奇怪,但不以为意。大概两个小时后回家,发现这个门还是敞开的,我妈就说你去看看,看看对门出了什么事。我进去看,发现对门的人头被砍掉了,有一点脖子连着,手掉在他的旁边。
当时,我在想他的手为什么掉了,可能是因为他用手去挡了刀。我很认真地观察死亡的样貌,具体的样貌,包括沙发印花的纹路和血对它颜色的改变。我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回去跟爸妈说,那个叔叔死掉了,你们报警吧,然后自己写了一篇日记去讲这件事。
日记是手写的,没有发表过。小时候觉得这种事没有意义,但是现在看,还是有的。
从那开始,我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写作之间的联系,有一种很强的意识。我要怎么利用这个经历,像您说的,我也觉得一个经历它没有被写出来,就像一个森林没有被看到或者一片海没有被看到,它似乎没有那么有价值。所以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陈丹青:我到现在还有点懵,我要调整一下,重新看待你,这些都发生在你七八岁的时候?
蒋方舟: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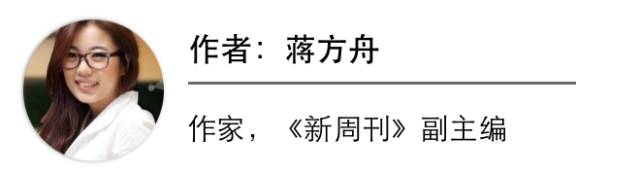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东京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