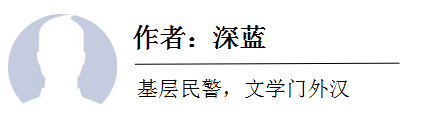《外科风云》剧照
“反正我男人死在医院了就得医院赔钱,还走什么法律程序?”
“照你的意思,你男人如果死在马路边还得让修马路的赔你钱呗?”
2013年11月的一天,110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出事了”。
“咋了?又送来死人了?”钻进警车,我急切地向接警的同事询问。
“比这还严重,送来个病危的,人还没上手术台就断气了,家属赖上医院了。”同事边开车边回答我。
到达现场,一条长长的白布调幅横扯在医院急诊室的大门前,上书 “草菅人命”。条幅之下,隐约看到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和一群人纠缠在一起。
“完了,又要闹一场了!”同事无奈地说了一句后,打开警笛,把车停在了急诊室门口。
保卫科张科长看我们到了,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快步往警车跟前跑,身后跟着两个从人群中扔过来的空矿泉水瓶。
“哎呀你们可算到了,大门马上守不住了,让他们冲进急诊室就麻烦了!”张科长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冲我们喊道。
张科长说,死者名叫刘斌,徐庙村村民,三天前的深夜,他被一辆农用车拉来医院,家属说是在小诊所挂吊瓶时青霉素过敏,要求医院治疗。值班医生赶紧组织人员抢救,但没能救过来。
“青霉素过敏死亡,要闹也是去闹小诊所,怎么闹到你这儿来了?”我诧异地问。
“哪儿是什么青霉素过敏!值班医生查了病历,这个患者是癌症晚期。之前一直在他们村的卫生院挂水(打吊针)维持,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呼吸。”
“现在遗体在哪儿?”我转头问张科长。
“在太平间放着呢,有四个保安看着。”
“一定守好遗体,现在这阵势,万万不能让家人把遗体抢出来!”
遗体是医疗纠纷中的重要筹码,在以往的医闹案例中,家属只要把死者遗体往医院大厅一摆,医院便不得不就范。
“放心,他们只要不冲进医院里面来,遗体不会有问题。”张科长抹了一把汗。
刘斌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我想起了一个人,向张科长求证,张科长连连点头,“没错,就是他。”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他生前是一名职业医闹。
刘斌在医闹行当里颇有些名声,据说只要他出面,没有要不到的钱。几年前,公众对于“医闹”二字还陌生的时候,刘斌便组织起一帮游民游走在周边各大医院,专门帮人“维权”。
停遗体、摆花圈、搭灵堂、放鞭炮是刘斌一伙的拿手好戏。只要这四招一使出,医院大多乖乖就范。
眼前的这家医院之前便吃过刘斌的亏,那年,刘斌曾“代理”过一起医患纠纷,凭着摆在门诊楼里的一具遗体,最终从医院要走了40多万。
刘斌团伙后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打掉,但他浑身是病,一直取保候审,至死仍是戴罪之身。
他的死出乎我的意料,也让医院和警方十分紧张。这些年我没少和刘斌打交道,他那一幕幕“专业”手段令人记忆犹新,而如今,躺在太平间的成了他本人。
我和同事打开执法记录仪,紧跟着张科长挤进人群。
披麻戴孝的家属带着香炉、纸钱、鞭炮、花圈堵在急诊室大门口,医院保安围成人墙阻止他们进去,急诊室的玻璃门已经在混乱中碎了一地。
现场乱得一塌糊涂,急诊室大门前上百人在围观,很多人拿着手机拍照摄影。
现场几近失控,我和同事上前进行劝阻,但毫无效果。家属和保安此时都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哭闹推搡声响成一片。
好在治安支队的增援及时赶到,远处的扩音器里传来同事的喊话声。
“我们是XX公安局民警,请围观人员马上离开现场!”
“冲击和打砸医疗机构涉嫌违法犯罪,请现场人员稳定情绪,理性对话!”
一队防暴警察开始上前疏散人群,外围看热闹的群众逐渐离开。
防暴警察的出现暂时平息了现场的混乱,死者家属放开了保安。治安支队领导上前劝说双方保持理性,家属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谈。
“他们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怎么谈!”刘斌的妻子激动地说。
“不是不让你们进来谈,你们要抱着鞭炮花圈火盆进急诊室,这是来谈事的吗?”张科长也激动回应。
“谈不好我们就把灵堂设在这里!”刘斌的妻子说。
“你听,你听,有……有这样谈判的吗!”张科长气的说话都结巴了。
“不这样谈怎么谈,我们是弱势群体,斗不过你们!”另一名家属在一旁说,边作势又要往急诊大厅里冲,我急忙阻止。
暂时平息了急诊室门口的骚乱,刘斌的妻子同意和医院谈判。
医院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尸检、查明死因;二是医疗事故鉴定;三是赔偿金走司法程序。
刘斌妻子立刻否决了医院的意见,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进行尸检,遗体由家属领回。二是医院提供一次性补偿,数额为170万。
双方从中午12点谈到晚上8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你说这不是讹人吗!170万?还不让尸检,不走司法程序,这不是做梦吗!”副院长忍不住指责刘斌的妻子。
“别的我们不管,我男人送进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现在死在医院了,我们一家的顶梁柱倒了,他们医院得负责!”刘斌妻子说。
不出所料,谈判不欢而散。
“你看你看,和当年刘斌的套路一模一样。”张科长在会议室外愤然拉着我说。
首次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同来的家属扬言第二天继续来医院“讨说法”,言下之意大家都明白。医院是公共场所,急诊室又是要害部门,此事谁也不敢怠慢。公安局与医院协商后,决定第二天继续派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天一早,刘斌家属来到医院,开始和院方进行第二轮谈判。
刘斌妻子拿出了一张“清单”,上面列明了包括死者丧葬费、医疗费,死者子女抚养费在内的一系列费用,加上精神抚慰金,共计170余万。
医院的态度与昨天一样,要求走医疗鉴定程序。双方你来我往,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上午10点,双方谈崩了,刘斌妻子一个电话,几辆农用三轮车载着20多名自称刘家亲戚的人来到了医院。
这群人虽然尽是老人和怀抱孩子的中年妇女,但一看便训练有素。一进医院即兵分两路,一路奔向医院急诊室,另一路奔向医院行政楼。
好在医院和公安机关早有防范,把人群拦在了急诊室和行政楼外。抱孩子的妇女开始哭天抢地,老人们也上去拉扯守门的保安和民警。刘斌妻子则披麻戴孝抱着刘斌遗像在急诊室门口席地而坐。周围很快又有人上来围观。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同事无奈地对我开玩笑。
“抓人吧,这么闹下去可不行。”我没有心思接他的玩笑。医院在我的管区里,我不想出事。
“等等上级命令吧,毕竟他们家刚刚有人去世,现在抓人有些欠妥。”同事说。
“丈夫去世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你要么谈要么告(走司法鉴定程序),可这样闹下去,性质就变了啊。”我蹲在刘斌妻子身旁劝她。
刘斌妻子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似乎划过一丝犹豫,但转眼便消失了。
“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要你提的要求合情合理,他们(医院)该赔你多少钱一个子儿也少不了。”我继续劝她。
“警官你说说,丧葬费、孩子的抚养费、我们一家的精神损失费,哪一样不合理?这么大个医院,170万对他们来说算得了啥?”
“那你得先同意尸检啊,不走法律程序,医院为何赔你钱,赔你多少钱都没有个说法嘛。”
“那不行,反正我男人死在医院了就得医院赔钱,还走什么法律程序?”
“照你的意思,你男人如果死在马路边还得让修马路的赔你钱呗?”一个看热闹的人突然插了一句。
刘斌妻子狠狠瞪了那人一眼,我赶忙示意那人别掺和。
我想再劝劝刘斌妻子,她却不再搭理我。
刘斌的遗体没能抢到手,灵堂也没能在医院搭起来,同来的刘家亲属没有可以凭借的“抓手”,只有一众老人妇女与医院对峙,也慢慢安静下来。有个别试图再去扯条幅、摆花圈、放鞭炮的人,被警察制止,骂骂咧咧又坐回到一边。
调解和劝说一直在继续,派出所、刘斌所在的村干部轮番上阵,但医患双方谁都没有松口的迹象,只好僵持着。
“你们赶紧想个辙,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同事对张科长说。
“村委会干部不是来了吗,院领导说先等他们做工作。”张科长说。
同事苦笑着摇摇头。
不是不信任村干部,照以前的经验来看,这种事情村干部能起的作用很有限。一来村干部没有强制力,来了也就是继续劝,而事主如果听劝的话,他们就不用来了;二来村干部本身也不愿掺和这种事,万一自己话说多了,真要是挡了人家的“财路”,人家回头非把村委会闹翻天。
和预料中一样,村委会象征性地派了两个人过来,劝了几句没有效果,也就回去了。
“吃一堑长一智吧,刘斌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接,忘了当年那大几十万是怎么赔出去的了?”同事跟保卫科的张科长说。
“瞧你这话说的,哪怕明知道可能出事,病人拉来了我们也不能不救啊!”张科长说。
想想也是这么个道理。
刘斌妻子提出的不走法律程序的170万赔款,被医院称为“梦幻170万”。但说归说,医院不掏这笔钱,刘斌妻子就不撤人。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医院几次通知刘斌妻子“开会”,刘斌妻子回应,“除了赔钱,别的不要谈!”
“你这不叫‘维权’,叫‘敲诈勒索’,懂吗?”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别跟我说什么违法,我没文化,不懂法!”
“不懂法不是理由!你真是想走刘斌的老路吗?”我压制着心中的怒火对刘斌的妻子说。
她不再说话。
医院快撑不住了。半个月来,几十号人在医院,虽然不闹了,但一天到晚披麻戴孝坐在大院里,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有人说他们是职业医闹,来找医院发财。但更多的人在指责医院管理不力,个别人还添油加醋杜撰了好几个医院“治死人”的故事。
尤其是前来治病的病人和家属,看到这群手捧遗像、披麻戴孝的人感觉“晦气”,不断向医院投诉。
“他们少要点的话,双方还有继续谈的可能,开口170万,胡闹。”一位医院领导私下抱怨。
从“不走司法程序一分不赔”到“少要点还有谈的可能”,医院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刘斌妻子那边也有些兴趣索然了。半月来,前来“维权”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减少,来到医院也不再哭闹,只是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期间,刘斌妻子还与一名“亲属”发生了争执。
公安机关继续维持秩序,刘斌的家人不哭不闹不堵门,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在医院大院里坐着,因此警察也无法把他们强制带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向同事抱怨。
“快结束了。”同事意味深长地说。
“为什么?”
“明摆着的,都快撑不住了。‘维稳’要花钱,‘维权’也要花钱,半个多月,得花多少钱。”
经过半个月的走访调查,公安机关基本确定了前来“维权”的“亲属”身份,其中大多数人并非刘斌的亲属,而是受雇于一个名叫“王拐子”的职业医闹牵头人。
搜集了足够的证据,随时准备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毕竟刘斌的遗体还在医院太平间里放着,医院还是希望能够平和处理,因此提出最后一次谈判。
“领导说,只要刘家人同意走司法鉴定程序或者把遗体拉走火化,不再闹了,医院愿意出两万块钱的‘救济金’。我们花钱求个平安吧。”张科长告诉我。
谈判桌上,刘斌的妻子也显得急躁起来。两万块的“救济金”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死者妻子开始歇斯底里谩骂起院方谈判代表来。
谈成这样,也就没法继续下去了。双方散会,我们开始做强制带离的准备。毕竟对方都是老人和妇女,公安局增调了女警,医院也备好了十几张床位,以防各种意外事件。
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刘斌的妻子跑了。
从谈判室里出来之后,刘斌的妻子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他们的“亲属”那里,而是悄悄地混入前来医院治疗的病人和家属之中,溜出了医院。
医院门口的“亲属”开始以为刘斌妻子被警方扣留,哭闹着要求警方和医院放人,但后来发现警察和医院也在找她,方觉不妙。
有人想趁乱离开,有人缠着警察要求找刘妻,有些“业务不熟”的“家属”,情急之下说漏了嘴。“她还欠着我们的劳务费呢!”
“都别走,全都带回公安局去!”局领导一声令下,所有参与“维权”的“家属”都被带进了公安局。
办案大厅里热闹非凡,“家属”们形态各异。很多人交代了自己的“光辉事迹”,纷纷承认是王拐子招聘来的职业医闹。最终,一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其他人被拘留(11人因年龄超限不予收监)。
一场医患纠纷就此落幕,刘斌妻子自此从徐庙村消失。后来医院曾接到电话,来电人自称刘斌妻子,要求医院兑现谈判时所承诺的两万块钱。医院让她来医院处理刘斌的后事。但此后刘妻没有来领钱,刘斌的遗体也一直停在医院太平间里无法处置。
医闹们供出了王拐子的下落,他很快被抓获归案。
在对王拐子的讯问中,我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死者刘斌和王拐子是同行,都是吃职业医闹这碗饭的。一天晚上,刘斌的妻子突然联系王拐子,说有事情要谈。
王拐子来到刘家,得知刘斌快不行了。刘斌的妻子让王拐子“帮个忙。”
刘斌的妻子对王拐子说,刘斌一辈子吃喝嫖赌,现在一分钱没给家里剩下不说,还在外面签了一屁股债。以后人没了,自己还得替他还债,怎么想怎么亏。现在看刘斌“差不多了”,想起以前刘斌做医闹能赚死人钱,自己也想做一把,让王拐子帮帮忙。
王拐子万万没想到刘斌的妻子找他做这事儿,本来打算推辞,但转念一想,反正自己就是干这行的,赚谁的钱不是赚,虽然心理上有些过意不去,但自己和刘斌也算是“兄弟伙的(朋友)”,就当帮他家一个忙,便答应下来。
村卫生院不能闹,一来乡里乡亲的,实在抹不开面子;二来也闹不来多少钱。所以二人商量趁刘斌还有一口气,赶紧把他转到大医院去。
二人知道刘斌当年曾在第二人民医院闹到过几十万,觉得那家医院有钱又好说话,便决定连夜把刘斌送去。
谁知刘斌“不争气”,去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王拐子本想算了,但刘斌的妻子说来都来了,就试一试吧。
双方约定,王拐子负责组织人员,“赔偿金”一九分成,刘斌妻子负责支付医闹的“工钱”、“车马费”、“午餐费”等。
二人本以为会像刘斌几年前那样,闹上个三五天,医院便承受不住压力付钱。不料刘斌妻子寄希望于通过此事一夜暴富,开出了170万的天价,直接堵死了与医院对话的大门。
“都怨她,我一开始就劝她,要个三四十万就算了,但是她不愿意,她太贪了!”王拐子抱怨道。
“哎呦,你还有理了是吧?接着说!”我怒斥王拐子。
王拐子给刘斌妻子找了20个人,价格是每人每天200元,30块午餐费和两包黄鹤楼“硬蓝”香烟,抱孩子的每人每天加50块。如果医闹被拘留,刘斌妻子还要按照拘留时间每人每天出500元的补助。
“维权”半个多月,账上一共要花十几万,刘斌妻子支付了两万块钱预付金后便再也拿不出钱来,后来的钱一直由王拐子出面欠着。
最后一次和医院谈判之后,刘斌妻子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闹了半个多月,眼见成本越来越高,不但自己的发财梦彻底破灭,另外还要支付医闹的巨额费用,便动了逃走的心思。
刘斌妻子甩开医闹匆匆回家,带上孩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一跑,王拐子不但拿不到当初协议的10%的劳务费。连雇佣医闹的钱都要转嫁到自己头上。医闹们没拿到钱,天天成群结队地去找王拐子要账。
“警官,你说我冤不冤啊,我也是受害者!”王拐子竟然冒出这么一句。
“放屁!你这是自作自受!等着吃牢饭去吧!”我骂了王拐子一句。
● ● ●
后记:
找不到刘斌的妻子签字,刘斌的遗体无法火化,就这样停放在二院的太平间里。
一次,我去医院办事,保卫科张科长拉住我,“他老婆有消息吗?遗体就这么放着怎么行?”
我告诉他,公安机关也因为医闹的事情一直在找刘斌的妻子,但至今毫无消息。
“活着折腾医院,死了还折腾医院!”张科长啐了一句。
我也暗自叹息,刘斌这位“老熟人”当年在医闹这个行当里混得风生水起,恐怕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半辈子医闹,最后却也因医闹落得个无人收尸的下场。
编辑:侯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