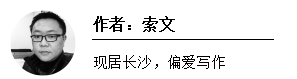《母亲》剧照
照片里,年少的峰伢偎着母亲,在阳光下皱着眉。年幼的艳妹坐在引擎盖上,似控不住身子,前倾着,诧异地抬头。那时萍婶尚年轻,披着我母亲的红大衣,扶着轿车后视镜,一脚在前,挺直腰杆,脸上漾着满足的笑。
文初叔是父亲的堂弟,父亲说是“同根把(同宗)的兄弟。”是隔得非常远的亲戚。究竟有多远,父亲也说不清。
祖父在的时候,曾经算过,绕来绕去,把自己都绕糊涂了,“文运开世兆,贤声记祖功。”(族里排辈份的诗句)祖父说:“都是文字辈的,是兄弟总没错,等建了族谱就弄清了。”
初见萍婶还是在小时候,某次随父亲回乡双抢。
那天,祖父、父亲下地了,我在堂屋的竹床上午睡醒来,瞥见一个粗壮妇人站在门口,一根扁担搭着箕筲斜斜地背着,一脸的油汗。
“你家大人呢?”她嗡声嗡气地说。
“我不知道。”我小声答。
她应了一声,转身走了。
晚间妇人又来了,未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婶婶,到你家吃夜饭咯!”
“要得,”祖母笑着站起身,唤我叫人,“这是你萍婶,文初叔家的。”
我家有个小磨,萍婶来借,“娘家带了点黄豆回,磨了做豆腐,到时送点过来给您老。”萍婶的声音像漏风的皮鼓。
磨再小也沉,萍婶却拿得轻松,胳膊夹着磨盘,扛起底架就走了。夜色中出门去,臃肿的身形,像杂技团里背自行车的熊。
后来萍婶还磨回来,果然送了盘豆腐,祖母切成片煎了,又放点豆鼓、葱花加水吊汤,外焦里嫩,又香又甜。
“双抢”过后,我们回了城。不久,萍婶也到了城里。
“我来看看哥哥,”她跟着文初叔叫父亲哥哥,“还想看看病,要麻烦大嫂帮我找找人。”
“好啊,哪里不舒服?”母亲爽快地回答。
萍婶来的那天,母亲买到几只猪蹄,剁成小块卤了。萍婶吃得欢,不停地添饭,啧啧地称赞。她右手执筷,每夹一口菜,都要把筷子伸到左腋下,手臂一夹,筷子一抽,揩干净了,再抻出去,夹下一口。
“你干什么呀?”我问。
萍婶嘿嘿笑着,并不答话。
母亲拉了拉我,“别说话,快吃!”可没吃两口,她又起了身,将我拉出屋去。
“你萍婶是讲卫生呢,”母亲轻声对我说,她皱着眉头,“但是你不要学,每个人讲卫生的方式不一样的。”母亲艰涩地说,末了推了我一把,“回去吃饭,别吃猪脚了。”
那晚,那盆猪蹄被萍婶一个人吃了,她吃肉吃得细致,骨头缝里的肉末都剥干净了,骨头还要在桌上墩一墩,吸出骨髓。碗底剩下的卤汁,她也倒出来拌了饭。
饭后,母亲洗碗,父亲陪着萍婶聊天,萍婶喝着茶,嗝打得山响,不停地要父亲评理。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哥哥你说对不对?”
“他是自己脸皮薄,使着我来看,哥哥你说对不对?”
她说到一半,父亲找借口走出去了。
父亲走到家门口的玉兰树下,点燃一根烟,我跟了过去,陪他站着,头顶是大片的麻蚊飞舞,被父亲吐出的烟驱散。
“爸爸,萍婶来干嘛?”我问父亲。
“你文初叔想要孩子。”父亲说。
“那萍婶来干嘛?”我又问。
父亲没有作声。
机关有一台电视机,锁在机关大厅的高柜里,晚上打开,供大家观看。家前的走道上,有邻居经过,提着板凳,端着茶水,“看电视去!”邻居们跟父亲打着招呼。
“就来。”父亲笑着回应。
一年多以后,又逢年节,一家人回了乡。某日上午,父母外出拜年了,祖父在堂屋迎客,我在厨下陪祖母。
大锅是嵌在灶台上的,祖母将洗净切好的菜倒入锅中,与热油接触,发出悠长的、仿佛彼此厌恶的“嗤——”声,一会儿,扑鼻的菜香便在厨房里弥散开了。
“婶婶啊,给你拜年啦!”久违的、嗡声嗡气的声音在侧旁响起,萍婶一脚迈进了厨房,怀里抱着个婴儿,小被子裹得紧实,只露一张粉嫩的小脸。
萍婶比去年更胖了,熊一般笨拙,生怕被子搭拉下来,不停地低头掖着。
“好好,恭喜你过了热闹年。”祖母笑着,从灶台后绕过来,在围裙上揩了揩手,伸着小指轻轻碰着婴孩的脸蛋,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戳坏了。她从怀里掏出个小红包,塞进包裹孩子的小被里,“峰伢发狠长,健健康康,顺顺遂遂。”祖母说。
“大嫂给了!”萍婶推搪,想要翻出红包来还给祖母,翻了两下没找到,就罢了手。祖母返回灶上做饭,萍婶陪在旁边聊天。
“要记你们家一世的恩,全靠大嫂找的医生,峰伢才能出生。”萍婶说。
“莫挂在嘴上说,”祖母说,“你们命里有的。”
“命里有贵人帮咧。”萍婶说,“总说峰伢要认了大哥当干爷(干爹),他又不肯。”
“本来就是亲戚,还搞这个做什么?”祖母说。
“给……我……梳头!”萍婶蹩到灶下,翻着白眼吓我,我瞪着眼睛看她。
那是一部电视剧(《炮队街的守夜人》)的桥段,萍婶年前来我家玩时看过,回乡后编成故事讲给人听,四处吓人。
萍婶笑着将我赶开,孩子用橡皮绳一绑背在背上,接替了烧灶的活。
不出两年,萍婶又给峰伢添了个妹妹,取名红艳。月子里,文初叔被镇上抓去结扎,要罚款,家里交钱不出,牵走了一头猪,出了月子,萍婶提着镰刀去镇上要猪钱,半路上被本家叔公拖了回来。
那年秋天,萍婶搭车到我家,诉了一夜的苦,红艳没断奶,也带来了,萍婶有说不完的委屈,“一个男人做结扎,线鸡(阉了的公鸡)样的,没用了怎么办,你们说是不是?”
母亲唤我去睡觉。
“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提醒她。
“还牵我的猪,那条母猪下过崽的,吃了会得猪婆疯,是不是啊?”萍婶高兴了些。
萍婶掀起衣襟奶孩子,父亲站起身,拉着我出门,“去办公室做作业,我正好改个材料。”
“快去吧。”母亲说。
第二天,萍婶走时,母亲买了罐奶粉送她,萍婶又高兴起来。
“我夫家哥哥在县里当干部,大嫂在公司里。”萍婶回娘家时,常跟人说,萍婶姓刘,外村嫁过来的,因她的宣传,我家又多了一些额外的客人。
“我是萍妹的二哥,她提起过吧。”
“我是刘萍的舅舅,她说这个事情只有你家能帮我。”
常常有陌生的人,打着她的名号来。
● ● ●
再回乡时,萍婶总会带着一双儿女过来,陪父母聊天。
“我总教峰伢要学伯伯,好好学习,以后当干部。”萍婶说:“艳妹就要学婶子,贤惠,里外一把手。”
父亲不作声,母亲微微笑着。
“昨天我帮婆婆(祖母)整菜地了,我说种萝卜,她非要栽红薯,萝卜爽口,是样菜,你们说是不是?”萍婶在父母亲面前表功。
父亲不作声,母亲微微笑着。
“锄了两锄头,扯了半天闲谈,喝了一壶茶。”祖母在里间揶揄。
“我说我家有萝卜种子,你不肯要啦。红薯又不费工,随便种都长。”萍婶转身冲着里间申辩。
“两老年纪大了,要你多照顾。”父亲忙说。
“那是,远亲不如近邻,何况我们是亲戚,你说是不是?”萍婶回过身来,笑嘻嘻的。
九十年代初,夏秋之交,祖父突发重病,父亲从县里叫了台救护车,去了镇上,那一夜大雨滂沱,我们在镇医院见到了吊着水、已经昏迷的祖父。祖母跟着来的,急得犯了哮喘,躺在旁边的床上吸氧。
“哥哥、大嫂你们来了。”熟悉的破皮鼓嗓音在旁边响起,萍婶端着个海碗,蹲在床边吃,见到我们,将碗撂在地上,站了起来。
父亲俯下身子看祖父,值班医生在旁边说着病情,末了,母亲请医生办转院手续。萍婶弯腰捞起地上的海碗,接着吃。
“辛苦了。”父亲对她说。
萍婶大口地嚼着,不及回答,筷子使劲扬,让父亲不要客气。
● ● ●
是萍婶两口子借了一台板车将祖父送到镇医院的,文初叔心细,临时在车上搭了个塑料棚子给两老遮雨。
“真是,”父亲啧着嘴,很是感激,“让你们费心了。”
“文初小意,手也巧,就是没力气,车还是我拉的,”萍婶口里包着饭,嘟嘟囔囔地说,“硬是结扎了,当不得男人用。”
“文初呢?”父亲不接她话,问道。
“喊他回家换衣服,他身子弱些,雨淋得透湿,怕他感冒了。”
“那你也回去啊,你也淋湿了。”父亲说。
“这会都干了。”萍婶终于吃完了那一碗冒着尖的饭,打着饱嗝,眯着眼,很满足的样子。
“哥哥,有个事……”萍婶期期艾艾地说,“那碗饭是赊的,要八角钱,我没带钱。”
父亲赶紧掏钱包。
“我没买荤菜,就点了个煎青椒,饭要得多了点。”萍婶解释说。
祖父在县医院连做了两个大手术,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亲戚乡邻们都来探望,萍婶也来了,提来一只老母鸡给祖父补身。一来家里,她便亮着破皮鼓嗓子,不住口地夸赞祖父:“您老人家硬是有福咧,一个崽顶得十个崽用!”
继而又说起村里事情:
“戴家大崽终于考上了大学,摆了三天流水席,不枉复读七年,毕业就是公家人了。”
“阳初不懂事,跑到山里去偷树,被抓了。”
“桂初家起了新屋,出去做事有钱赚呢。”
祖父眼神变幻,听得津津有味。
● ● ●
近年底时,父亲请萍婶一家来城里玩,文初叔不得闲,萍婶领着一双儿女来了,招待她们住在招待所,母亲领着看电影、逛商店,给峰伢买玩具,给萍婶扯布做衣服,带他们娘仨下馆子吃饭。
“汀兰酒家的蒸饺,她一人吃了七笼,只怕是没饱,没好意思再吃。”母亲后来说。
临走,母亲请邻居龚伯伯,给萍婶一家照了几张相,萍婶喜气洋洋,借来母亲的红大衣穿,扣不上,敞着。龚伯伯让她选背景,她领大家在院子里转了半天,终于找到了那台停在树荫下的白色小轿车,“这车好咧,乡里看不到的。”她将艳妹放在车盖上,将峰伢拉到身前,紧贴车子站着,侧了身,手搭着后视镜,“麻烦你,师傅。”她对龚伯伯说。
流年变幻,心思活泛起来的乡人们,开始在农闲时拉帮结队外出打工,尝到甜头的,索性撂荒了田,整年在外头,省省抠抠几年下来,回家置彩电、修房,这一趟就没白忙。
文初叔也学着外出打工,两、三年光景,就拆了旧屋盖新楼,萍婶却始终不肯荒了田,家里两亩多的水田,自己打理,一百斤的谷子仍能挑起就走。“我们又不是吃商品粮的,荒了田是败家咧。”萍婶总说。
村里的娱乐丰富了起来,到了夜里,看电视的聚在几户人家,开牌局的聚在几户人家,多年未有的麻将声,渗进了小山冲的夜。
● ● ●
1997年,祖父、祖母终于禁不住父亲的劝说,搬进了城。
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城东,单位宿舍的三楼,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对面低矮的屋舍和挺立其中的一棵老樟树,更远处,浏阳河水蜿蜒曲折,泛着粼粼的波光。
第二年春上,萍婶和文初叔来了我家,文初叔肩膀受了伤,到县里看病。
“治了几个月,老不好,镇上医生硬不如城里咧,是不是啊。”萍婶说。
原来,文初叔开始做苗木生意,经人介绍,乘火车下福建,联系业务,辗转认识了几个老板。老板们的胃口刁,多年的老树才奇货可居,文初叔带着人四乡找,在偷挖一棵百年桂花树时,被乡民发现,发生了械斗,文初叔的肩被打伤,镇医院治了好久,老是痛,使不上劲。
“怕是要去社港。”母亲说,联系车子陪着去了。(社港,浏阳的一个镇,镇医院有一位骨科圣手。)
“一针下去,脓血就冒出来了。”母亲回来说,“里头淤了血啊。”
治完病回乡,母亲买了些文具给萍婶带去,彼时,峰伢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一塌糊涂,艳妹上着小学,乖巧懂事。
我上班不久,便是千禧年,那时起,回乡拜年成了我的活,我会在节前去拜年,请朋友开车,装着一后备厢的礼品,去永和跑上一天。
萍婶家是要去的,文初叔的肩伤好了,没有再做苗木生意。
萍婶拿出积蓄,购置了机器,在家里扯筒子(鞭炮的上游产业)。文初叔歇了工,整日游手好闲,萍婶也都随他。
我第一次独自提着年节礼物站在萍婶家门口时,看到的是峰伢,这个十多岁的男孩,仍旧汲溜着鼻涕,正坐在堂屋的火屉箱上抽烟。
萍婶家的坪是卵石地面,靠近檐下的地方结着青苔,一株大枫树挺立在坪的一角,巨大的躯干要数人合抱才围得起来。抬头往去,虬劲的枝杈撑着天,青灰的天空被光秃秃的树枝分割成不规则的方块。
“哥哥,来拜年咯。”峰伢认出了我,麻利地起身,开了根烟给我,我推掉了。
他搓着手,将我引进屋,目光在我提着的节礼上扫着,回身大声喊着:“姆妈,来客啦。”正是变声期,声音在转粗,有些男子汉的味道了。
萍婶从里屋迎出来,胖得步履拖沓,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颊的肉松弛下垂。她微笑着,嗡声嗡气地寒喧:“这么早就来了,还是你家礼性足。”倏地眼一横,扫了扫峰伢:“畜生,快去泡茶,好不懂事!”
祖父祖母进城,嘱托萍婶帮忙照看我家老屋。在萍婶家略坐一会,她掏了串钥匙,挟了挂鞭炮,带我去坡下看老屋,峰伢跟着来了。
“杂种不守屋吗?”萍婶斥他,峰伢不作声,萍婶没口子骂,“像你爷(父亲),小的大的都不懂事,你就不学好,他就一天到晚打牌,冇看见往屋里拿一分钱!”我不作声,默默走着,在家里,听祖母偶尔提起过,文初叔牌打得很大,败了家。
老屋前坪已蒿草丛生,鞭炮声中,厚重的木门被萍婶推开,屋内,家什上积灰不多,诸物静默。
“我隔一向过来敞敞,搞搞卫生。”萍婶说,“总不能荒了。”
“辛苦你了。”我由衷说道。
萍婶使劲摆手,“坝上(河上,浏阳东乡以坝称河)修了新桥,水泥的,可以过得车子,”萍婶朝前一指,“以后走前面来,可以开到坪里的。”
“你帮我教教你老弟,不好好读书,一天到晚混。怎么考得上大学咯?”回程时,萍婶念着。
峰伢不知几时又叼上了一根烟,被萍婶看到,一巴掌打掉了,反手又是一巴掌,打得峰伢一个趔趄,峰伢涨红了脸,怪叫一声,跑掉了。
“死畜生,硬是不懂事。”萍婶望着峰伢跑远的身影,狠狠地说。
峰伢是他十八岁生日前几天没了的,据说那天,他与萍婶吵了大架,躲在柴房里喝了一瓶钾氨磷。待发现时,人已经没了。
亲族大事,族亲都要出力帮忙,母亲陪祖母回乡,母亲在某次打电话给我时,说到这件事情,连说萍婶可怜,白发人送黑发人。
回到家时,祖母倒拉着我絮叨了半晌,仿佛生怕我会学他,反复说着:“心里放大些,什么事情都过得去的。”又拿自己做例子,“你爷爷逃饥荒,不管我们,我也过来了……你要听话啊!”祖母叮嘱着。
我哭笑不得,问道:“萍婶还好吗?”
“伤心啦,哭得在地上打滚,三天水米不进,”祖母说,“第四天早上,在厨下吃了一锅饭,就着一碗猫鱼(腐乳),差点没噎死。”
“峰伢葬在哪里了?”
“茶山上,少亡不进祖坟,得另找地方。”祖母说。
母亲告诉我,峰伢想去学美发,萍婶不准,两人才杠上的。母亲说,萍婶很悔,一个劲地对她说:“美发也不是坏事,早晓得会这样,就让他去学了。”
那一年年节回乡,是大年初二,到得萍婶家,文初叔和红艳迎的客,萍婶去峰伢坟上了。
艳妹在读职高,成了大姑娘,“哥哥、哥哥”叫得欢,文初叔越发瘦了,听说他戒了赌,租了块地,又开始种苗木。
“别人也是靠劳力,我也是。以前赚过,再想办法赚吧。”文初叔忝然说。
我家的老屋已经借给同族的华初叔住着,父亲另备了给华初叔家的节礼,文初叔锁了家门,带着艳妹陪我同去。
下了坡,文初叔在院墙前放起了鞭炮,华初叔迎了出来,也放起了鞭炮迎客,老屋前坪的荒草已经修葺了,进得屋里,一切家什有了用度,又鲜活起来。
华初叔只是辈份比我高,年岁略长,他的儿子尚且蹒跚学步,待我坐下,丢了手里玩具,扑上来抱我。“叫哥哥。”华初叔在一旁喊着,我忙在他襟里塞上一个红包。
华初叔留饭,文初叔陪着,艳妹子没有回家,跟着父亲,腊鱼、腊鸭、肉丸子、和菜(猪皮、笋条、萝卜丝、肉丝、肉丸炖在一起的汤菜)摆一桌。华初叔开了瓶酒,文初叔陪饮。
那一顿吃得很香,饭菜都是从前的味道,箬叶粑粑蘸上糖,清香糯软,乡野间的鞭炮声响得零碎,年味终是淡了许多。
饭吃到一半,门被推开了,人未进门声先至,“自己屋里冷火炊烟,饭都不搞了?!”是萍婶,她的头发全白了,声音仍是中气十足,她踅到桌前,自顾拉过一张椅子坐下,艳妹乖巧地盛上一碗饭。
“要得,菜要得。”萍婶接过碗,拿起筷子就吃。
“你们喝酒,陪好格伢,莫管我。”她饭菜塞了满嘴,嘟嘟囔囔地说。
“我不喝的,萍婶。”我提醒她。
她一愣怔,望向我,嘴里咀嚼着,用大勺喝了口汤,用力吞下,“那也要陪啊。”她咧着嘴笑,脸上肉鼓鼓的,眼睛眯得看不见。
“我去看峰伢了呢,”饭吃过一碗饭,萍婶幽幽说:“他也过年,我给他烧纸,跟他说了半天话,让他投个好人家,莫要再碰上我这种恶娘。”说完,伸手将空碗递给艳妹。
一桌人都噤了声,她又自顾吃起来。
艳妹二十四岁才结婚,在农村,这个年纪结婚,算顶迟的了。回门那天,我开车载着祖母回乡喝喜酒。
艳妹不像萍婶般粗犷,像父亲,模样清秀,话语轻柔。之前对过不少亲(相亲),男方多是钟意的,可萍婶强硬,非要男方入赘,终是无人肯应,艳妹磋砣了几年,后来文初叔发了火,以离婚相要胁,逼得萍婶松了口。
宴席设在萍婶家前坪,路口设了充气拱门。请了邻居戴家二哥的酒席班子,大枫树下摆开了几十桌,亲戚乡邻悉数请到,热热闹闹地坐满一坪。
正是入秋时节,门前大枫树叶子半红半绿,犹如一把朱翠大伞,给坪中喜宴遮蔽荫凉。喜乐响起,喜炮鸣过,一对新人在堂前久立,不见萍婶。
众人四下寻找,终于在早已弃置不用的柴房找到了她,她坐在柴房角落,斜靠着一个木桶,任吉庆的新衣沾满灰尘,魔症了一般默默无语,眼泪潸潸而下。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架出来,按在高堂席上,接受新人行礼。艳妹的头磕下去,萍婶“哇”地放了声。
● ● ●
那天饭罢,我经过堂屋,看到了多年前萍婶在县里照的那张照片。在堂屋东面的墙上,挂着许多旧照片,那张彩照用框装着,挂在正中的位置。
照片里,年少的峰伢偎着母亲,在阳光下皱着眉,年幼的艳妹坐在引擎盖上,似控不住身子,前倾着,诧异地抬头。那时,萍婶尚且年轻,披着我母亲的红大衣,扶着轿车后视镜,一脚在前,挺直着腰杆,脸上漾着满足的笑。
三年后,我送祖母回乡小住,途经萍婶家,进屋坐了会。
萍婶仍是胖,精神却极好,坐在檐下择菜,艳妹也在,儿子两岁了,跌跌撞撞地在坪里赶鸡,艳妹的肚子又挺起了。
萍婶坐着不动,艳妹张罗着搬凳倒茶,一双眼盯着孩子,大声呵斥着:“慢点跑,莫绊(摔)哒。”
话音未落,孩子扑在地上,大人未及近前,自己爬起来了,奶声奶气喊:“绊哒咧。”又跑去抓鸡了。
祖母笑,萍婶也笑了,择菜的手不停,嗡声说道:“细伢子是绊大的,是不是啊。”
祖母点头。
“我想这个跟她爷(文初叔)姓,女婿不肯呢。”萍婶恨恨说着,“艳妹子不作声,女生外向。”
“跟谁姓都没事,顺遂就好。”祖母劝道。
萍婶啧了一声,又摇了摇头,手里停了动作,歪着头沉吟半晌,叹道:“是啊。”
编辑:罗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