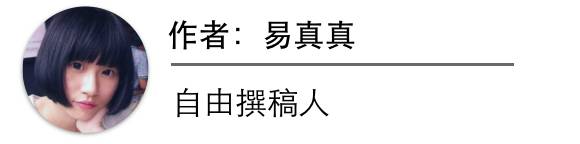图 | CFP
年轻人眼中的董家渡陈旧又保守,是上海传统生活的最后喘息,却吸引着大批外国人来此打捞一种体面的可能性。在老住户看来,董家渡是“破地方”,可对年轻人而言,这里是“高级定制”的代名词。
前言
对我而言,这是一场错误的旅行。
所有随身物都被压缩进迷你箱中,连同过去几个月来对旅途的想象与忧心忡忡,一并交付给无尽的铁路线。从上海到喀什,5000公里,4个月,将海洋、高架桥、超短裙与咖啡馆统统抛诸脑后,以一种不确定的速度,驶向西边的西边。
“旅行半是逃离,半是追寻。”保罗·索鲁说。
而我就在这样的逃离和追寻中来到上海,他人梦想的终点站成为我此行的始发地。2016年6月29日,我在上海董家渡。
“你以为我是什么小人物?”蒋叔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心里确认这件事。“我是个皇帝呀,等一动迁我就能拿到一百万。”
他信心百倍,粗眉毛顺着眼角扬起而抖动。在他面前的水果摊上,5元一只的泰国西柚为这条街道涂抹来自异国的明快色彩。
站在董家渡路和篾竹路路口,遮天蔽日的屋棚挡住了6月末的上海暑热,天空蓄积着重量,将成片的房子压得很低,仿佛连行动其间的人都被压缩了。蒋叔微驼着背,约莫50岁出头,如果忽略他的蓝色运动衫和猫咪拖鞋,看上去倒有几分像梁朝伟的形容。他以一种领导人阅兵的风度,缓缓抬起右手,示意我为他拍照。
“你是不是记者呀?是呀?哎呀,我经常上电视的你晓得伐!”蒋叔一口上海腔滑溜溜的,动作敏捷地从身后凉棚搬出板凳。用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语气对我说,“来,你坐这里记下来,我跟你好好聊。”
在董家渡一住就是30年,蒋叔的生活一言难尽。
也许有人会短暂忘记地处城中心的董家渡也是上海。在这里,苍蝇馆衔接着蔬菜摊,鸡血鱼鳞滚落石板路,缝隙被市井笑话填满;房子在弄堂尽头延伸,方盒子里三代同堂重复上演;衣裳是当街晾晒的,年幼者如此乐观以至于露天沐浴变为一场游戏。在这里,街道的功能一再扩展,下厨、洗衣、打牌、闲谈全在太阳底下进行,消息从街头迅速流入街尾。生活相互串联,放弃隐私成为一种生存策略。
在蒋叔嘴里,董家渡不叫董家渡,而是“破地方”。能在这里住上几十年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比如他,比如街坊们,“能屈能伸呀。”
这里地处黄浦江岸,因董家渡口而得名。往前数到嘉庆年间,沙船业兴盛带动商业繁茂。那集市栉比人声鼎沸的南外滩,是记忆里的事儿,与现在无关。在外滩与陆家嘴的夹击下,董家渡那一片叠床架屋的棚户区显得颇为尴尬。有人说这里是上海市井文化最后的缩影,不过这最后的缩影也要散尽了,拆迁步步逼近。
而在户口上与董家渡捆绑一处的人们则企盼着能逃离此地搬进公寓楼,尽管他们也无法掩饰对于未来的无力,因为拆迁价格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在董家渡,只有天空是古老又崭新的。
上世纪80年代,蒋叔在上海南站以海鲜批发生意起家,按他的话来说,一天能挣几千块。“我的脸值钱嘛,生意就好。”起早贪黑的奔忙并没有消磨掉锐气,那会儿还年轻英俊的他并不明白好运气不会一直眷顾。
“我一喝酒,一打架,就给抓进去了。后来店也给封掉,老婆卷了17万跑掉了。”此后蒋叔蜗居董家渡,贩卖水果,但从不招揽生意。
蒋叔傲气,每当有路人过来询价,他总是撇着眼,努努嘴,示意客人自己看他手写的价签,从不多说一句话。或许他也明镜似的了然,只是靠5元一只的西柚永远无法重现昨日辉煌。“要不然我现在还是个大人物。”
蒋叔反复强调自己很伟大,一家人都是“伟人”,连跑掉的老婆在他眼里也闪着光。他并不怨恨妻子,反倒佩服她能干,有才气,是“可以和上海市长对话的厉害女人”。转念又开始同情她。这个卷款而跑的女人最终和他离了婚,“她也很可怜,她后来给人啊,杀掉了。”
他叹息着,粗眉毛猝然抖动。在他口中,这个碎裂的家庭,还有一个“伟人”儿子让他牵挂。儿子自小在英国读书,是个电脑专家,他们失联多年。这个男孩就像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消失在遥远模糊的英格兰。
而眼下全是董家渡。
 △5元一只的泰国西柚为这条街道涂抹来自异国的明快色彩。 作者供图
△5元一只的泰国西柚为这条街道涂抹来自异国的明快色彩。 作者供图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往东500米远,一家晓贤生煎频频在美食节目露面,却仍挡不住店铺脏旧。再往东,一座1847年建成的董家渡天主堂夹在两个正在施工的工地间,“上海建工机施集团”和“中建八局”的招牌在半空摆荡,古老教堂前乏人问津。
从老街名中还可一窥此地旧影。过去糖坊弄终日萦绕着麦芽糖那甜蜜的气味,在夏日的浓热中瘫软;芦席街上芦苇与芦苇搭绑交错,几何纹理上浮起河流;花衣街是诱惑女人的始作俑者,遍地棉花行,一批批彩色绸布从滚滚棉花海里诞生。
诱惑无处不在,牵引人心。
自2002年开始,董家渡进入动迁改造。受拆迁价格挟持,进展缓慢,时断时续。老房子在缓慢的进程中被推倒,断壁残垣宛如一条伤疤。2014年董家渡区域从王家码头到东江阴街被拍出248亿元高价,刷新了徐家汇地块的记录,媒体聚焦此处,新一代地王诞生。如今,新一轮的拆迁潮水翻涌,有人雀跃,有人心忧。街坊们不时谈论起未来何去何从,不久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百万富翁。
蒋叔也许会是百万富翁中的一员,拆迁成了他最大的牵挂。“那就不用卖水果了。”我像是替他松了口气。 “人总要做事情的嘛。”蒋叔规划起未来,“等我有了一百万,我就去搞水果批发。你坐在家里吃喝嫖赌,一百万不够你花的呀。”他笑着说完,顿了顿,“不过现在钱对我来说也没用了,我的痛苦比钱多。”
遁入东江阴街,老弄堂的气息让人想起南方小城。空间和时间在记忆中挪移,向西南900公里,时间仿佛回退20年,那种狭窄巷弄里滋生的,人与人的触碰,石板与石板的推搡……没有咖啡厅,威士忌吧,也没有米其林几颗星,从8元一碗的馄饨到20元一件的衬衫,还有12元一次的剪发,董家渡以低廉价格供应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
12元理发店里没有年轻人,只有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大家彼此相识。来自扬州的老板娘小心将围裙裹上客人脖颈,“你这个衣服可不是一般的衣服诶。”
“哎哟你看得懂!”白衬衣上海先生表示赞许。
“那当然。”老板娘轻轻巧巧地回应。10平米的房间,因为三四个等待理发的客人而显得热气腾腾,桌上的矿泉水瓶里悬着绿萝,翠翠的。
“焗油膏没涨价,”老板娘熟练地将灰白色糊状物往客人头发上抹,“房租1600的时候就这个价,现在房租4000了,也还是一样。”
在本地人眼里,拆迁像是承诺一个新世界,而对外地生意人来说,则是要将过往的努力一笔勾销。远处工地的噪音规律运转,不慌不忙改天换地。
上海作家金宇澄曾谈及被拆除的老建筑,“旧东西旧建筑有如此大的凝聚力,但拆已经拆了,比如上海外滩的江沿,过去栈桥密集,船樯林立,十六铺、董家渡复杂的民生风景线,尤其是那些普通的旧细节,最后都是被简单线条的堤岸、乏味的绿化大道抹平了。”
电子音乐人马海平(MHP)则对上海的变迁保留一份乐观。他打小在长宁区的弄堂长大,街巷生活的粘稠质感保存在少年记忆中,既有人情味,又有不舒适感。这种不舒适的感受他在北京亲戚居住的胡同里也同样体会过,居住空间狭小,缺乏卫生设施。
“因为海派文化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让一些有上海情结的本地人依依不舍,然而保守并不能守住消失的弄堂。老上海文化在消失,新上海文化在建立。”
年轻人眼中的董家渡陈旧又保守,是上海传统生活的最后喘息,却吸引着大批外国人来此打捞一种体面的可能性。
对他们来说,董家渡是“高级定制”的代名词。成片的彩色布料从南仓街一直延伸穿入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内,不起眼的三层大楼里涌动着异国面孔,“做衣服”是他们共同的目的。在这里,你只需花上800元,就能自己挑选面料、款式甚至搭配纽扣、刺绣等,交给老裁缝们手工为你制作一整套西服。低廉的价格吸引着在上海工作和旅行的外国人,关于面料市场,他们远比本地人更了解。
迷宫一般的市场由一圈圈商铺围合而成,每间不过几平米,在悬挂的成衣与布料间争夺注意力。招牌大多有种老派作风,以店家名字命名,一眼望去满满的Tommy、Mike和Jenny Tailor。
每一间商铺都是一个外地生意人在上海的奋斗史,填充着汗水、眼泪、欲望与竞争。两间相邻的店铺,衣服款式看上去如此雷同,灵感均源自巴黎、意大利;西装、衬衫、礼服上挂着的Dior、Gucci,宣传画也大致相似,想要判断哪间更好简直无从下手。因此,不乏店家将外国客人手写的推荐语或是买家秀摆在显眼处。
每一个站在柜台后的人都心知肚明,一旦新客人选中了自己,接下来的几年,他都会专一光顾。
Jack是我在南外滩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当我第二次经过转角的丝巾摊位时,他仍不死心地招呼我过去看看,“真丝的,名牌。”Jack三十岁出头,敦实的小个子,来自江西,在得知我是湖南人后,他麻利地接茬,“半个老乡啊!”这是他和妻子Judy在面料市场开创事业的第一年。早几年前行情不错,靠着兜售山寨的包包手表,日子过得顺遂。现在则没有这个运气了。他蹲在地上,黑色短袖,卡其色工装裤,沙滩凉鞋,翻检着一摞摞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丝巾,霞光粉、芥末黄在他周身招摇,Chanel、MOSCHINO的logo从丝巾边角中倾泻。
热心肠Jack领我去见他的朋友Jeanne和JoJo,两个同样在市场做买卖的江浙姑娘。Jeanne打理皮装,JoJo则经营着一间占了两个铺位的正装店。
他们是2006年第一波入驻这个市场的生意人,从拆迁的老市场转移此地,十年一晃就过。要是算上父辈们在董家渡打拼的时间,则要往前再数二十年。两代人都将青春留在了南外滩,留在了华达呢、杭州丝绸、麂皮和山羊绒之间。
“我这是被他们忽悠了,做了两套,好不好也不知道。”正赶上一位客人来JoJo店里取此前定做的衣服,这位就职华为的眼镜先生斜靠在面料桌上,用手指尖抚摸着这套笔直顺滑的黑色丝毛西装,全然不顾身边美国朋友已经溢出来的好奇。
“拜托帮我给你朋友推荐一下嘛。”JoJo陪着笑冲眼镜男眨眼。
“我可不推荐啊,他做不做衣服是他自己的事。我又不拿好处。”眼睛男用手指拨弄着西装纽扣,一张写满原则的脸,下巴因为拖得过长而有些歪斜。在他们身旁,一个波兰女孩则将新做的橙色羊毛大衣举向空中,仰头尖叫连连,“It’s sooooo beautiful.”
“这是个老客人。”JoJo小声对我说,眼睛闪过意味深长的笑。
每天周旋在客人堆里,这就是JoJo和Jeanne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作为“衣二代”,她们还在读书的年纪就已经在高级丝绸、皮料与碎布头之间摸爬滚打,在老师傅们的缝纫机旁看着面料是如何经由丝线拼接缝合,成为一件梦想的衣裳,被带往欧洲、美国、澳大利亚,陪伴一些人经历爱情、职场中的喜悦与难关。
与老一辈不同的是,年轻的商人们无需再借助计算器应对外国客人的讨价还价,他们所掌握的英语已经足够派上用场,在久经各国口音的磨砺下越发纯熟。不看时尚杂志、不追潮流动向是不行的,他们需要迅速更新对于时髦的理解,在下一个客人进门时,便已经在心里做好了预测。
连此刻带有顶棚安有空调的凉爽室内都与过去不同,她们还记得拆迁之前的老面料市场,密集的摊位敞开在露天,苦夏暴雨烈日,严冬寒气霜雪。谁还想再回到过去?
但是生意也回不到过去了。“现在早上起来一睁眼就会担心,会不会又一整天没有人。”JoJo紧抱着双臂。欧美高街品牌遍地皆是,互联网购物也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来找裁缝做衣服的人大不如前;另一方面,不断上涨的房租和人工极大压缩了利润空间,哪怕面料比过去更低廉也无法挽救;更何况缝纫成了一门稀缺手艺。
“年轻人没人愿意做这行。”Jeanne脸上显出无奈。在她的皮衣工厂里,几位从业十多年的裁缝都已经50多岁,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以前是裁缝求着我们,现在变成我们求着裁缝。”JoJo无法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你得哄着他们,不然他们就换另一个店去做,反正有的是人要。”
忧虑随着空间的转移而变换,也跟随时间的推进而衍生,解决之道往往隐含在捋顺的纹路之中。Jeanne相信手工定制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处,非网购可以比拟。而JoJo则想通过带给这个行业冲击的互联网来寻找出路。此前有客人依着外国网站上推荐的地址找过来,让她有了新的想法。“坐在家里生意是不会自动送上门的,还是要靠互联网,多在网上做一些推广。”
没人知道面料市场和商人们的命运将会走向何处。久居这里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世界转瞬变换,无需长远思量。
如果只住在董家渡,你将永远无法理解其完整的意义。在上海的最后一晚,我来到位于红坊艺术区的On Stage livehouse,电子音乐人马海平将在这里进行新专辑《折叠痕迹》全国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
电子乐无异于一场现代巫术,利用技术手段将宇宙中散落的音色捡拾,拼接,改头换面后制造出一种如天外来客的未知快感。这种音乐天然匹配上海这座城市,两者都是属于未来的产物。
生于80年代初的马海平对老上海的格局与生活形态还有着依稀的印象。弄堂生活自有一套运行的规律。
然而,在一座不断扩张的都市里,想要停留在过去并不现实。在这场名为“未来城市之光”的演出里,马海平用音符与律动建筑想象中的城市,将电影《银翼杀手》中2019年的洛杉矶阴雨嫁接到上海这座欲望之城,是一场将过往经历与虚拟未来进行杂糅的狂欢。
晚上10点,演出即将开始。乐手们一袭黑衣,DJ Jackie、小号手夏豹、键盘手高家豪、古筝演奏家王萌在马海平身边一一就位。乐手们在做最后的沟通,灯光微弱,台下的年轻人则频频举起酒杯,等待音乐入侵的那刻,在舞池中沦陷。
波德莱尔所理解的现代生活是转瞬即逝的美和叹息。凯文·凯利则说:“我们不会照现在的样子走下去。面对明天的问题时,我们用的是明天的工具,而不是今天的……未来是一块不断扩充可能性的领土。”在马海平构想的未来城市中,时间和空间已经消亡,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绝对之中,速度之美正在成就一种新的美学。
从董家渡走进On Stage,你才发现,未来并不理所当然优于过去,而过去也未必就写满了骄傲与理智,也有荒蛮根植其中。
都市文明的意义在于人类可以拥有更多选择。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关于未来的,科技的,也包含人类经验在河滩上冲刷留下不易抹去的痕迹,是一种对陈旧生活的熟练回应。我们当然应该拥有电子乐,但是何必要消灭生煎包?
电子乐镀银般光洁的旋律在这个工业风的空间中摆荡,我吞下一口冰过的柠檬苏打水,想起了昏沉沉的董家渡,衰老的天主堂,想起了翻滚在彩色布料里的Jack、Judy、Jojo和Jeanne,自然也忘不了缓缓抬起手臂的蒋叔,西柚的橙色外皮获得了一层粗粝质感,在太阳的折射下,发出了自己的光。
● ● ●
参考资料:
1.《金宇澄:道不尽的繁花》,陈元喜
2.《对话马海平:雨季黄昏的上海像2019年的洛杉矶》,豆瓣音乐人
3.《科技想要什么》,凯文·凯利
4. 纪录片《董家渡》,周洪波
编辑:侯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