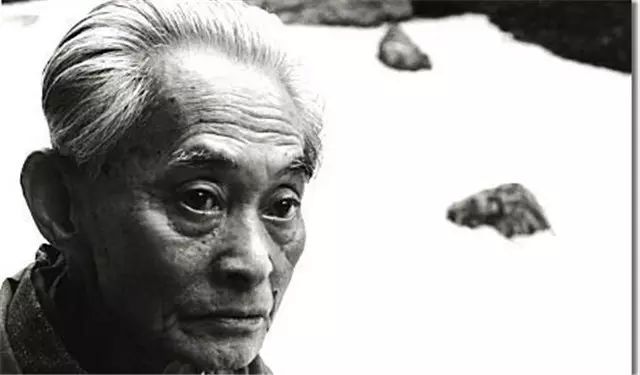
文 | 王斌
我以为,《千只鹤》是我读过的川端康成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作品,而那几部,据说皆是川端小说的代表作———《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接下来便是这部《千只鹤》了。
它让我入迷。此前,我陆续读过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乃至《古都》均没有让我如此着迷,这么的百味杂陈,感慨系之。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一边读《千只鹤》,一边悄然地问着自己,几度想提笔写下这份悬而未决的追问,可又想了想,终究是放弃了。原因是我还没有读完《千只鹤》。
没有读完的小说是不好多说的,毕竟那仅是一个飘浮着的仍在进行中的思绪与探问,它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归论,因为这份言说所依傍的主体叙事仍在持续地延展中,那个最后的结局仍未显现,由是,川端在《千只鹤》中的主题思想也就尚未真正的得以显身了。我必须耐心等待着那个“最后”的结局,由此让我知晓川端究竟想说些什么。
但它——《千只鹤》结束得过于的匆忙了,戛然而止,虽存余音袅然,但终究留下的仅仅是貌似已尽但终是未尽的尾声。这让我感到了些许的遗憾。
它是不该如此匆忙结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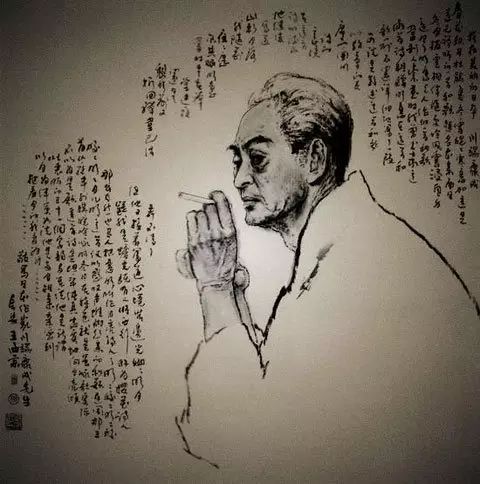
▲ 川端康成像
但细想之下,这仿佛又是川端的写作特点,或曰他的创作“个性”,也就是说,川端乃是一每每沉溺(或深陷)于感觉中而难以自拔的人,日本文坛“授予”了他以“新感觉派”,此说亦不无道理了。
川端是一个感觉器官极尽发达的人,他极善于捕捉那些微妙的、一时间难以言说的感觉,这感觉那么的纤细、游移、恍惚,偶然间的一闪现,还有的,便是稍纵即逝的人生之一瞬间了。川端的感觉犹如一台高度灵敏的照相机,当那些稍纵即逝的人与物一旦呈现,他的快门已然迅疾落下,并以文字之形式予以捕捉、凝固、定型,这便将成为永恒之一瞬了。
川端显然陶醉于此——此一令他陶然欲醉的“瞬间”。所以他说,他的小说事先从不构思。这份嗜好倒是与我的创作如出一辙,由此我深知他为何如是,其实就是为了捕捉那些个“转瞬即逝”。人生中毕竟充满了许许多的偶然和随机,它常常是稍一闪现便迅速消失在了缈茫无尽的时空中,但它作为一种缘发之“因”,无形中又带动了随至而来的“果”,而人们素常仅只注意到了那些显现出的“果”,而对于启动此“果”之因,倒是大意而疏忽了,因为它早以消失了,消失在苍茫虚无的时空中。
而这个消失的“苍茫时空”,又似乎是川端小说“物哀”之源头。他总是对日本历史中存留下的美———“仪式”般的“物事”,充满了无尽的兴趣,以致他竟有些“恋物”了。
难道不是吗?
我们只须打量一下他代表作笔下的人与物,便知晓其一二了:《伊豆的舞女》中的行走艺人——舞女,《雪国》中的百媚千娇的艺妓,《古都》中少女穿戴的和服,以及搭配在和服上的富有日本文化韵味的腰带,再就是在《千只鹤》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古老的陶器了,它们都是日本文化的经典符号,在这些经典符号中,盛满了日本的历史与文化,由是,它们便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集成了,亦构成了我们从而得以认知和看取日本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和角度,从而也可以一并认识与看取了川端的小说了。
“物哀”,此一词语在日本文化中似是一颇为奇特的意指,它的出现,好像是与日本的第一部浩瀚巨制《源氏物语》一同诞生的,人们将其流露出的那份绵绵情思以“物哀”来命名,但在中文语义的直解中,它似乎指向的乃是对“物”的哀伤或哀痛。
其实不然。
“物哀”在日语词语中确切之定义并非是单向度的,它是双向而多义的,亦即它既是对一种美之物事的礼赞,又是在对此一物事寄托的一份深切的哀愁。
一种民族词语之衍生,总是与此一民族的情感与情思密切相关的,情与物的相互缠绕,滋生出一种绵长的思绪或情愫。日本人最初是没有自己的文字语汇的,只能借道于汉语之力,抵达的却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于是“物哀”———这一在我们的汉语中未曾有过的形容词就此诞生了,而“哀”,在这里既是对美的物事之赞颂,又是对美的物事的一种日本式的不无哀愁的叹息。
由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川端的小说中,时时流露出的那种百味杂陈的日本式的思绪了,他总是在他所迷恋的符号性的物事中,寄托着他的那份独有的哀愁和叹息。
他是在隐隐的预感中哀叹一种美的历史\文化的消失吗?他好像对现代文明的大举进犯是有一份本能之抵触的。
我记得他在一文中用疑问之口吻说过:日本的美存在了一千多年了,它还能再存在一千年吗?
这是他的疑问,亦是他的一份叹惜与忧虑了。
于是物哀之忧愁,构成了川端小说的基调,他小说中的笔下之美,亦由此而染上了一层若隐或现的淡淡的忧郁,这哀愁与忧郁,一如他笔下萦绕山间的云雾(《伊豆的舞女》),一如秋叶的枯黄和飘零(《古都》),一如山路上的那条被积雪覆盖的曲曲弯弯的小径《雪国》,一如《千只鹤》中那个被少女近子摔碎的百年传承的陶器……

▲ 日文版《千只鹤》
物哀!
《千只鹤》的故事是蛮纠葛的,这里出现的那一组人物关系,远不像川端其它小说那般相对单纯、清澈、婉约,它依然是川端式的一以贯之淡色调的,但当这组关系介入了这种淡调子时,一切都变得异乎寻常且又耐人寻味了。
这组人物构筑成了一个既是碎片残迹般的关系,又彼此地映照出了人世间复杂的人生向度。
川端大多小说有一相对的固定的模式,他总喜欢借助于一个年轻的男性眼光,来打量那个神秘的女性世界,尤其是少女的世界,在他的眼中,这类娇媚迷人的女子总是那么的亭亭玉立,冰清玉洁,由此又泛起了男主人内心的一种朦胧而复杂的情愫,因了这份难言的情愫,叙述便染上了一层如晚秋般的忧郁了。在“性”的问题上,川端又总是欲“性”而未“性,给人留下无尽的诗意的遐想。
而这一次———《千只鹤》,人物关系的编织,使得“性”构成了这一特立独行之小说的一大特征,但他的美学观,依然促使他在回避直写,而是曲尽其意。
性,似乎成了川端小说无言的禁忌。
就因为他过于的痴迷于美吗?而在他执著的美中,性是否会让他倍感有违于对美的感知?
写《千只鹤》时,川端正值壮年,50岁,苍茫之人生锻造了他更深沉的情感,他不再像《伊豆的舞女》那般仅像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幻想着少女不可触碰之美艳,犹如面对一朵阳光下娇嫩欲滴的鲜花,不忍采摘。《千只鹤》让阅尽人间沧桑的川端,有了更深邃的入世的眼光,而在此前的创作中,他总是含着一丝出世的情怀。
小说的男主角菊治父母双亡,在一次由父亲的旧日情人近子举办的茶会上,见到了父亲曾经深爱过的另一情人太田夫人,她领着女儿一道前来的,而这个茶会,近子的本意是想帮仍在独身中的菊治,介绍一位貌美的女子,这位女子(雪子)身著一袭缀有千只鹤图案的日本和服。而这个“千只鹤”之意象,虽被冠之于小说之名,其实在小说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川端真正要写的,是菊治与太田夫人和他的女儿文子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
就在那个茶会之后,菊治在归途中,意外地发现太田夫人站在山间的小路边旁静候着他的到来,而菊治对她是心怀怨懑的。毕竟太田夫人曾是父亲的情人那时他还小,他感到了内心的受伤。
他们站在路边聊着,菊治偶尔会发泄一下自己心中郁积的那份怨愤,含一丝嘲讽,但太田夫人对他父亲的思念与哀愁,还是让他心中多了一点什么说不清的滋味。此后,他们一同去了一家山间旅馆。
川端从来不会明着写性,他只写感觉———事前的与事后的感觉,仿佛欲令“性”,别来“骚扰”他对美的物事的感知。但我们知道,那一段欲言还休的叙述,其实写的是他们共度那个难忘之夜,而这一夜,让菊治感受到了太田夫人惊人的温柔与女性的温暖和熨帖。
后来他还想见太田夫人,却在电话中听出了太田夫人的惊恐和崩溃,以及她女儿文子在边上的大声喝止。再后来的一个潇潇雨夜,虚弱的太田夫人突然造访了他,她说她想他,也思念他的父亲,她向他请罪,请求他的原谅,因为他从菊治的嘴里知道了,他们相见的那个茶会,其实是近子为了让菊治相亲的,由此她有了强烈的负罪感。就在这一天,她说到了死亡。
一切都像是那一夜的延续,只是多了许多哀伤与痛苦的撕裂。事后,他送太田夫人回了家。
就在当晚,菊治接到了文子的电话,说她母亲自杀了。
在菊治去吊唁太田夫人的那一天,文子向他述说了她母亲对菊治的爱,以及她的阻止,她恳求菊治原谅她的母亲。那一场会面是凄迷的。后来菊治又约了文子,而这似乎也是文子期待中的一次见面,她带来了母亲喝茶用过的陶器,说上面留有母亲的唇印。她再次请求菊治能原谅她的母亲,她向菊治深深的陪罪。菊治心如刀绞,百感交集了。
有一天,菊治突然接到文子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的电话,说是后悔将母亲用过的陶器送给他,他让菊治务必将它撞碎。菊治不解,而文子固执地不说原因。接下来,他们在菊治见面了,文子不无哀恸地说到了母亲,说到了菊治的父亲,也说到了自己的父亲,可奇怪地是,这些哀恸、伤悲,似乎在拉近他们间的距离,一切都像是意在言外,他们间意意思思地在心心相印、同病相怜了。
川端是极擅长写朦胧情感的,整个过程的叙述朦胧而暧昧,但作为读者,你的心会忽然被揪紧,甚至省悟到,那个忧郁的文子其实已然爱上了眼前的这个菊治,只是她在顽强地挣扎抗争,因为他们之间横亘着这么多难以理清的心理障碍———菊治的父亲,以及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一切都像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孽。
又是事后。
事后的文子断然摔碎了菊治珍爱的留有太田夫人唇印的陶器,离开了菊治。我们依稀感觉到了,在此一“事后”之前,他们间必是发生了一场鱼水之欢。

▲ 电影《千只鹤》海报
第二天的一大早,当菊治打电话给文子时,惊异地发现她“失踪”了,从此渺无音讯。
小说蓦然而止在这个节点上。从叙述情绪与节奏上看,这是一篇貌似未完成的小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人无限感慨的逗号,而非句号。我只能推测,作为感觉派的川端,他并没有想好他最后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尤其是从中他欲意要提取出什么样的人生意涵。
他只能如此了,欲了未了,让一个高高悬置在文字上空的大写的句号,悬而未决。
或许川端自己也犹感这是个“悬而未决”,嗣后,他又写下的一个续篇《波千鸟》,在此著中,川端让文子的失踪有了下落———那天之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都市,孤身一人开始了游历日本山川的长旅,一边走,一边给川端写下长信,信中既汇报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又诉说着她对菊治纠葛难解的思念,终于有一天,她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思念你,为了同你分手,才来到这高原和父亲的故里。我思念你,就难免纠缠着懊悔和罪恶,这样就无法同你分手,也就不能开始新的人生。请原谅,我来到这遥远的高原,依然在思念你。这是为了分手的思念。我在草原上漫步,一边观赏山色,一边还在不断地思念你。
在松树林下,我深深地思念你,心想,假如这里是没有屋顶的天堂,能不能就这样升天呢?我盼望着永远不要再动了,我全神地祈祷着你的幸福。
“请你与雪子姑娘结婚吧。”
我这样说,就同我内心的你分手了。
我承认,看到于此时我潸然泪下。我不知是在为踽踽独行中的文子,还是为内心孤独凄凉的菊治,甚或是为那个已在天堂的文子的母亲?我百感交集,心疼不已,或许,我仅是在哀叹命运的无常以及对人之捉弄,以致陷人于不幸!
这部续篇,坦率地说最好的部分便是文子写下的那封长信了,而小说叙述主体中的菊治与雪子的新婚,索然无味。
一切的阅读情感都萦系于文子的那一封封长歌当哭的信中了。
《波千鸟》是思绪未尽的《千只鹤》的延续,尽管如此,还是让我犹觉川端的言不尽意,也就是那个本当从故事中可以提炼出的形而上之命运的主旨。
在这里———《千只鹤》中,川端出人意料地笔涉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也即人性之负“罪”感,这对于一个一生都在追寻与痴迷于日本文化之美的川端而论,是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写作。川端设计了这么一组复杂的人物关系,而这组关系之存在本身,已然昭示了“耻”的存在性,由此,从不事先构思,而任由感觉行走之川端,其实是想探寻他一贯缺少的人性之深度的,而此一深度,又关涉着日本人文化心理中的“耻”的隐匿———它寻常看不见,被一层表面的仪式般温情脉脉的面纱精致地包裹着,从不示人,一如被舞女、艺妓和和服裙带遮蔽了的川端康成。川端这一次选择的是一种极端化的人性表现———乱伦。
说是乱伦,其实亦不尽然,只是父亲与儿子共同爱上了一位中年女子,而这位女子的女儿,又与“儿子”陷入了一言难尽的爱河。
这是一种爱吗?
的确,川端此次突破或颠覆了我们世俗性的爱情观,那种我们在俗世中至为普通而又流行的爱情观,他甚至瓦解了了我们固守的传统意识或规矩。川端让那些隐藏在人性最深处的“可能性”之爱情,浮出了水面。想必他也为他的此次“大胆妄为”而惊叹不已吧?否则,他为何竟会在《千只鹤》中留下一个“言不尽意”的尾声呢?
川端显然不知该如何“认识”他笔下的这些人物行为,和他们之间纠缠着的复杂关系,由是,以美感著称的川端只能随着笔涉之人性一同挣扎了。他矛盾着,纠结着,而矛盾纠结的典型体现,便是他言不尽意之“朦胧”了,既想让这些“物事”呈现出物哀之美,又被一种罪恶的“耻感 ”所缠绕。
他无以解脱了。
太田夫人对菊治之恋是不是亦出自对菊治父亲的留恋?而文子的“陷入”,是否始源之因乃是缘自于母亲的“恋情”,触发了她的那一份少女般情爱的萌动,以致陷落不幸?
而菊治呢?他对她们母女的“爱”和苦思,是否亦是父亲孽债的一种无意识的延续与拓展?这其中,从人性正常心理来看,是有变态性的,但川端则将这个貌似“变态”之人性面相暴露出来,予以书写,其实也就揭示了人性中我们所陌生的一种本然性的存在。
他们间的垂死般的挣扎与扭曲,其实是基于一种潜在于心的俗世道德,这是人类为自己的彼此共处划定的一条“界线”,界线的划定,当然源于历史,人类为了相安无事的共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为一己之行为,制定规则,此一规则后被人类命名为道德,亦即以“道”,为德,“道”是公共性的,而“德”则属人个之行为规范、规矩,或曰德行。
但文学的道德力量,有时会偏离人类约定俗成的道德轨迹,而道德的神圣之使命,又天然地是关注人性的,以及人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之流变。任何道德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诞生的,但历史语境又从来是变动不居的,遑论道德呢?由此,所谓道德,必然会伴随着历史语境之变迁,有所调整,此为一。
二:文学在时代下将承担什么使命?它的义务与职责又是什么?捍卫道义仅只是其中之一说,政治学或伦理学似乎也在做这些必要的探索,于是这就像在与文学之使命做“同语反复”,并没有显示出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表现之形式的特殊性。
在我看来,文学的必然属性乃是去蔽与启示,而去蔽一说,便是将被世俗成见遮掩的尘土予以拂除,由此而显现出人生的本然之相,尽管从世俗的角度看,文学所呈之事完全有可能是丑陋的,甚至不堪,但这种揭示亦显示了文学自身的立场与道义,它从不屈就于世俗之习见,它也不为了赢得大众的欢呼和鲜花而向其做廉价的献媚,它只以感性直观的力量,剥去被道德巧装打扮的妩媚的外衣,直见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的未被揭示的黑洞,从而完成了对人类认识自身的启示意义。
以上我只是在说一种相对完美的文学,它的使命与责任,但在《千只鹤》中,一如我之所言,川端康成表现出了极大的困惑与彷徨,他深度陷入了小说人物的情感纠葛与冲突,引发了他挥之不去的“物哀”之愁绪,由是文字都笼罩在了一种冷色调的思绪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其实一直想从中突围的,寻找一条救赎之路———既为他笔下的人物,也为他自己,但他终究没能找到,只见他在一种无奈的惆怅中,让他的《千只鹤》欲言又止,成了一个缺少了句号的“物哀”的长句。
其实在川端后续的《波千鸟》中,我摘取的那段情深意长的文子之信,若加入了《千只鹤》的尾声,《千只鹤》便不会是一部“残缺”的作品,而会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显然,当时的川康,尚未地想到最好的命运结局,他只好独写文子的“失踪”。但对她为什么失踪,失踪了又去了何处?当时的川端显然感到了茫然。

▲ 日本电影《千只鹤》光盘封面
他只能意犹未尽了。
但在《千只鹤》中,川端以感性的直觉触及了日本文化中的道德“耻感 ”,这一耻感,因了又关涉几段凄美的爱情,便呈分裂之状了,一方面,他不得不为他的人物承担负罪之责,另一方面,他又被其中的刻骨铭心所诱惑,也正是因了于此,文学完成了一次对世俗道德的“僭越”,抵达了我们人性中的陌生区域,在那里,道德之耻与真挚之爱发生了强烈的抵牾与较量,未见胜负,只有当事人以逃遁之形式予以自解,而正是这个抵牾和较量,通过《千只鹤》,我们“结识”了我们过去未曾认识和打量过的人性乃至人生。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任何冠冕堂皇的言说在悖谬的人生面前都显苍白无力,而最好的文学,就是表现命运之悖谬。
一如《千只鹤》———它没有结论,只有抵达。
2016/10/29
原标题:《<千只鹤>:“物哀”的符号》
【作者简介】
王斌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评论家、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