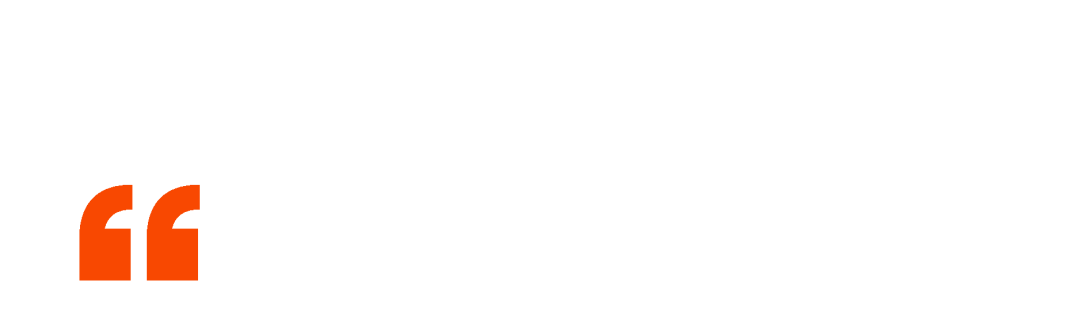
温州海鲜,食不厌精,唯快不破!
八月,东海开渔,目送一条条渔船驶向大海,沿海人和内陆人都跟着食指大动起来。
浙江,坐拥中国最大渔场舟山渔场,又有台州、宁波等一众海鲜名城。如果说浙江是站在中国海鲜鄙视链顶端的省份,那么其海岸线最南端的温州,更是把吃海鲜求鲜求精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
温州人把“鲜”字写进一日三餐,把“快”字刻进交易分秒,把“精”字融进一条鱼的每一寸骨肉。东海的波涛拍打海岸,整座城市都是一座巨大的海鲜市场,生意人的精明和渔民的豪爽同煮,就成一锅滚烫的“人情鲜”。
温州话谈吃,用词颇为浪漫。早起吃“天光”(早餐),不只有糯米饭,还可以来碗海鲜面,晚上吃“黄昏”(晚餐),酒楼有海鲜大餐,大排挡上热热闹闹的“夜厨”(宵夜)更少不了蒜蓉和啤酒味道,开海季的一整天,温州都被鲜味包裹。
温州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温州又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去那里吃几顿海鲜,就全明白了。
按秒起吃,温州海鲜的速度与激情
凌晨四点,天蒙蒙亮,苍南霞关渔港被渔船上的探照灯照的通明。打开船舱,最新鲜的鱼获像瀑布一样滑向甲板,来自各个市场的买手,以最快的速度做出选择,装车运走。
两个小时后,大大小小的海鲜市场里,扩音喇叭就开始循环播放“刚靠岸、刚靠岸”。活蹦乱跳的蝤蛑(青蟹)被绑成粽子样,望潮(小章鱼)在水盆里喷墨,最惹眼的“血蛤现撬”让人又爱又怕。满载活鲜的卡车被等候的商贩和老饕们团团围住,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惊喜,由此而来。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是刻在温州人骨子里的城市精神,而在开海季,时间就是鲜美,就是稍纵即逝的海洋风味。温州海鲜有“三杀”的说法,即所谓活杀、现杀、熟杀,操作起来,一个比一个利落。
梭子蟹,生长在蜿蜒入海、江水半咸半淡的瓯江里,因此被称作江蟹,实则是海蟹。刚起网的梭子蟹先过冰水,冰得它“晕”而不“死”,壳凉、肉紧,随后厨刀沿脐盖一挑一掰,“啪”一声掀壳,白酒、酱油、黄酒、醋、糖、姜末、胡椒粉依次加入,但最终要烘托的,还是蟹肉像冰激凌一样入口即化的口感,这就是温州传统冷盘名菜“江蟹生”,与宋代的“洗手蟹”吃法一脉相承。
现杀的生腌血蛤更是名声在外。血蛤必须选会吐舌的,壳一张一合,证明鲜活。滚水下锅,三秒出锅,壳刚开一条缝,肉挂血丝,蘸酱油醋连汁带肉“嘬”一声吸入口,像喝一小口温热的海浪。小型章鱼叫作望潮,抓住后会喷墨挣扎,离桶后先被摔三次,去腥、去墨、去筋,再下锅白灼,入口脆得能听见“咔嚓”声。
熟杀更多几分精细,但依然需要争分夺秒。黄鱼、鲳鱼先蒸后泼葱油,锁鲜同时去腥,火候差5秒就“破相”。更心急的老饕们,干脆早早等待渔船靠岸,藤壶、虾蛄被直接撬开,简单白灼下肚,抢的就是那股离水30分钟内的“海气”。
分秒必争,求鲜得鲜,离不开这座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大陆海岸线总长514千米,基岩海岸占比很高,洞头群岛是舟山之外的浙江第二大渔场,离市区一步之遥。曲折的海岸造就众多良港、海湾,与七百多座大小岛屿相望,再加上瓯江、飞云江、鳌江入海,形成滩涂、礁坪、深水槽,外海高盐冷水、内湾低盐暖水、河口富饵浑水交汇,如此复杂的海岸地貌环境,让温州海域同时拥有梭子蟹、大黄鱼、佛手螺等等种类丰富、跨度极大的海鲜。
辛苦捕来的海鲜,绝不能轻慢。几十个渔港沿着洞头、苍南、瑞安海岸线密集分布,运输半径压到最短。一把蛏子上午还在滩涂吐沙,中午就进了锅。吃不完的鲜美,有许多运往苍南灵溪镇,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之一浙福边贸水产城,把温州的鲜带到全国各地。
抹一抹嘴巴,天生会做生意的温州人,又要出发了。
一口鲜吃光光,谁能比过温州人?
除了生猛一面,精打细算,无所不吃就是温州“搞钱”精神在吃海鲜上的极致体现。
除了远海捕捞和养殖水产,还有许多“小海鲜”,是踩着礁石、扒着藤壶,一点点从浪里抠出来,堪称温州版赶海。从前,温州人把靠海吃海、以渔为生称作“讨海”,而今天,讨海更像是沿海生活的一抹情调。血蛤、辣螺、藤壶、沙蒜(海葵)……抠来的小海鲜,做法五花八门。
面对长在潮间带垂直岩壁的佛手螺,外形狰狞,一簇簇镶在岩缝里,酷似外星生物,渔民绑绳垂吊采来,汆烫后掰壳蘸芥末,海味冲鼻,嫩肉像果冻。来自深海章鱼的小吸盘形如“克苏鲁”,温州人拿来以葱油调味,还起了个灵动可爱的名字,海灵菇。
学名疣荔枝螺的辣螺,壳小肉紧,自带麻辣口感,采螺人蹲在潮沟边,用铁钩翻拨礁石,钩尖一挑就是一个。回家清水静养吐沙,下锅快炒,鲜辣开胃。人人喊打的寄生藤壶,也有吃法。团簇在船底、桥墩、礁顶的藤壶,用凿子一下一下撬来,下锅干煸,出锅撒椒盐,壳脆肉嫩。
在温州人眼里,海鲜几乎没有“下脚料”一说,每一次海洋劳作都不可错付,每一缕鲜味都值得细细打量。
青蟹,也就是蝤蛑,在温州话里被叫做“蝤蠓”(jiú měng),是温州人最引以为傲的海鲜。以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的灵昆岛所产为最佳。此蟹上桌,蒸汽未散,温州人不忙动筷,先把蟹翻过来,看肚脐分公母,公钳壮,腿肉绵密,母黄清甜,吃法稍有不同。
真正的仪式从蟹钳开始,掰开蟹钳,露出雪白柱肉,蟹壳裂而不碎,再把最细的那条小腿折断,尖端口子恰好成小勺,沿着钳壳内壁轻轻一转,连最后一缕筋膜也刮得干干净净。剩下几条腿,腿尖轻咬破皮,唇舌并用,一吸一嗦,腿肉滑入口中。最后掀开蟹盖,用筷子尖蘸一点酱油醋,轻点蟹黄表面,增加咸鲜口味。
吃得如此精细的还有温州“鱼生”,其实是一种用酒糟和盐腌渍的细长条的小鱼,原材料为小带鱼“白带”和带鱼幼苗,犹如柳丝一般细长。城里说“白鱣
(shàn)生”,城关说“白带生”,到了苍南、平阳的闽南语里又成了“带柳丝”,一条不过筷子长的小鱼,被方言切成三种叫法,恰如温州人把小鱼做成“鱼生”,稍长些的晒成“鱼干”,连鱼尾等小肉也要熬“鱼露”,丝毫不浪费。
腥黏的墨鱼内囊,包含雄墨鱼的精巢与雌墨鱼的卵巢和缠卵腺,温州人小心翼翼地将三样合拢,筷子轻戳,加少许盐、番薯粉、姜汁,拍成掌心大的小饼,热油一滑,就是人人爱吃的墨鱼饼。除了鲜香,还有墨鱼内脏的滑腻口感。鮸鱼更是温州人最质朴、最广泛的海鲜情结,家烧、清蒸、敲鱼汤无所不吃,成就了一日三餐的鲜。
在这样的“算计”下,温州人对海鲜的追求,绝不会被时令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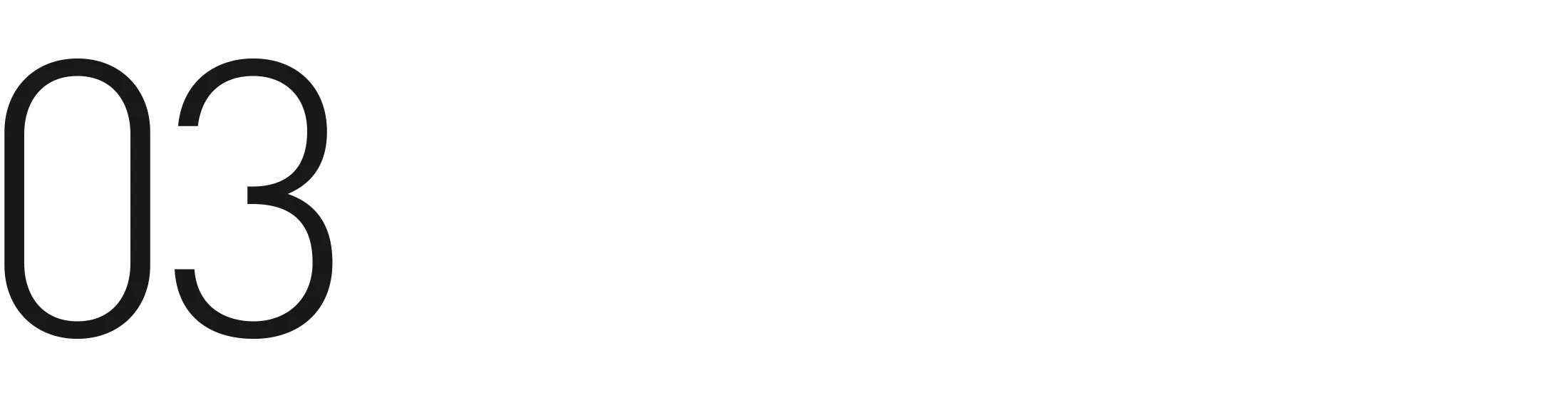
吃“淡”点的温州海鲜
一点也不平淡!
浙江吃海鲜以精致著称,温州人又把这份精致,融入精巧的技法和“淡而不薄”的风味特色中。
地处瓯江入海之处的瓯越,温州菜得名瓯菜。潮汐日夜吞吐,海鲜是不变的灵魂。用淡,就是不借重味、不抢本味,不薄,则是把海味的层次、香气、回甘,排布圆满。
比如瓯菜几乎不用白糖提鲜,而靠贝类、甲壳类体内甘氨酸推高鲜味。清蒸蝤蛑揭盖那一口,咸鲜收尾带微甜,让人回味。与这种味蕾哲学相对应的,就是烹调中的“二轻一重”:轻油、轻芡、重刀工。
炒蛏子只勾几滴熟猪油,油温刚起烟就下料,吃的是海水原鲜,这是轻油。轻芡则是尽量不让芡汁喧宾夺主,最好地提现食材的清晰轮廓、原汁原味,比如爆墨鱼花,要一眼能看出刀纹。
瓯菜刀工,以“敲”和“锲”为特色。新鲜鱼肉拍上生粉,一锤一锤敲成几近透光的薄片,薄得能透出盘底花纹,却又韧得夹不起、夹不断。鱼丝、火腿丝、香菇丝在滚水里一焯即起,三重层层递进,却互不掩盖,著名的三丝敲鱼,提现“敲”的精髓。锲,是蓑衣花刀的变奏,斜刀切过的海鲜,下锅后受热卷曲成麦穗、凤尾,不仅是颜值即正义,也是以刀改形后对火候、油温的苛刻。
敲,温州人独特的烹饪手法。
图/地道中国味
更妙的是,温州山海相交的环境,为瓯菜的鲜美提供画龙点睛的山野滋味。温州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绵亘有洞宫、括苍、雁荡诸山脉,海拔千米以上高峰17座。座座山峰捧出竹笋、香菇、鸽蛋、走地鸡等物产,与海鲜同烹,出现“蝤蠓炖鸽蛋”“黄鱼配笋干”的山海融合菜,鲜上加鲜。山珍不夺味,只负责把海味的边界再往外推一寸。
往时间深处望去,瓯越人向海而生,两千多年前就学会用潮差晒盐、用季风晒鲞。潮水来去,渔船往返,四季周而复始,“淡而不薄”的味觉共识,争分夺秒的海鲜狂热,精打细算的菜肴做法,一点点形成。
唯快不破、无所不吃、清淡细腻,温州海鲜的三大极致,背后更是这座奋斗之都,勤俭细致、拼搏探索的城市精神。当南来北往的人们,去温州品尝一份海鲜,也是品尝一座城的真正本味。
文 | 阿满
文字编辑 | 苹果
图片编辑 | 王家乐
封图、头图 | 上海去哪吃(meishi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