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3年后,
“建筑界的诺贝尔”再度花落中国。
68岁的刘家琨
也成了继王澍之后,
刘家琨的得奖,已然是姗姗来迟:
“家琨老师早就该得了”,
“偶像加冕!”
“让在行业迷雾中挣扎的建筑师又燃起了热情,
重新描摹了‘建筑学原本的模样’。”
社交媒体上,不少粉丝更是感叹:
“这是一场与浮夸建筑时代的决裂。”
刘家琨做的“浪漫事”,
被委员会的评审辞记下:
“对他而言,
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
城市的印记和社区的遗迹。”
这份印记,在刘家琨的词典里,
西村大院鸟瞰,摄影:陈忱
今年的评委会主席、2016年普利兹克获得者阿拉维纳赞美刘家琨:“在这个容易形成无穷无尽乏味边缘的世界中,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建筑方法。”
国际媒体不吝惜对刘家琨的赞赏:
“他是一位歌颂普通民众生活的建筑师。”
这位50后的成都建筑师,
刘家琨还曾听到年轻人用“我就在这个烂尾楼这儿”的言语,

西村大院临街街道,摄影:存在建筑
但渐渐地,这里成为成都西边的市民最爱待着的公共场所,竹下火锅、屋顶跑道、广场舞胜地、创意市集……
男女老少都能在这找到乐趣,
刘家琨造房子,
擅长把各地的文化习俗和人们的需求
无缝融入建筑中。
造出的建筑虽然常常外观看上去“粗糙”,
却总能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后,
和自然生长在一起,
并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西村大院里的周末市集

西村大院里的棒球训练课
值此大奖公布之际,
一条回顾5年前与刘家琨的对谈。
2020年秋天,
我们和他一起,
在成都新工作室的后院打篮球,
听他和画家老友何多苓聊艺术。
更在他设计的西村大院里,
刘家琨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但大概因为祖籍河北,自带一股在四川人身上不易寻着的酷倔劲,不常笑的脸孔大多时候严肃、冷峻。有人用“雄健”形容刘家琨的建筑,初见刘家琨,发现这两个字放在他身上也极合适。但开口攀谈,他便流出成都人的随和,聊起天夹杂冷笑话,用他自己的原话,就是“闷骚”。

第一个拍摄日,刘家琨带我们去看蓝顶艺术区里两栋施工中的工作室,这里未来将是家琨建筑事务所办展览、做活动的地方。收尾阶段,他一定要自己去现场跟工人商量诸多细节。工作完毕,他从车后备箱摸出一颗篮球,吆喝一条的摄影师们陪他玩上几局,一边上篮,一边玩笑般和年轻人们嚷嚷:“我受过伤,你们不能撞我!”刘家琨想着未来能多来这儿办公,老友何多苓的美术馆紧挨在隔壁。他在后院里规划了菜地、种了树、建了篮球场,把工作室二层朝向最好的地方,装了长窗、留作咖啡厅。1999年,在还没什么“独立建筑师”概念的年代,刘家琨自立门户开了事务所。事务所在成都玉林一栋再普通不过的商住楼,进小区要让门卫室打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事务所在商住楼的六层,入口的门上挂着刘家琨淘来的铃铛,大伙儿进进出出,清扬的铃铛声也跟着响。刘家琨的房间在跃层二楼的一个角落,桌上、墙上都是他建筑项目的手绘图纸,但书桌前后的书架上,一眼望去,文学作品比建筑书籍多不少。门常开着,事务所里的三只中华田园猫自在地溜达进来,蹦上书桌、向窗户外张望上一阵儿。

成都蓝顶艺术区,一条拍摄何多苓(左)与刘家琨
临近饭点,浓郁的火锅味从街道的餐馆飘进小区。作为成都人,火锅是刘家琨的爱。疫情期间,困于隔离,刘家琨只得自己在家动手下厨。情况转好后外出的第一餐,便是找了家位于屋顶、相对开敞的火锅餐厅,给何多苓等老友们庆生。对于盆地、四川人和火锅,刘家琨有一套自己的火锅哲学:“成都平原周围有高山围绕,本地人在盆地里的生活被环绕、被包围,就有个盆地意识。火锅也是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容器,里边什么都能装,也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成都西边的青羊区,刘家琨造了一个巨型“火锅”,占地约70亩的西村大院。
带我们去西村大院里闲逛,刘家琨一路开着手机相机,记录疫情之后成都人迅速恢复起的各种“竹下生活”:长条形院子里热闹的周末集市,入口门廊前休息平台上蹦跶的小姑娘,以大院空心砖墙为背景自拍的年轻人,中央球场上打棒球的小朋友……
西村大院是个城市综合体,除了没有住宅,几乎没有想不到的功能。70多亩的地四面环街,房子绕着街道修建,环形一圈,各类商铺入驻。

还有大大小小、种满竹子的院子、廊道,供人跳广场舞、打麻将、吃火锅……

从地面升起又环绕屋顶一圈的跑道总长有1.6km,定期会举办主题性的迷你马拉松。曾经一晚上屋顶涌入9000多个市民来散步、跑步,管理方很紧张,怕出安全事故,平日里就把屋顶的跑道给锁了,有活动时再开放。刘家琨拍摄的方型火锅
因为这样,刘家琨常说西村大院就是个“可以什么都往里扔”的火锅,不过不是圆锅,是方锅,带格子的那种。他专门拍过一张方锅的照片,和西村大院的俯视图凑在一块儿,说方格子就是大院里的小院子。

西村大院的周边有十几个住宅区,可原先这块地上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几个网球场和一个游泳馆。占地都很大,运营成本都很高,却只服务于少数人。委托刘家琨来设计西村大院的是杜坚,他是刘家琨相熟20多年的好友,也是个有情怀有理想的企业家。作为西村的总策划和业主,杜坚希望,落成的建筑不仅能体现成都平原的地方精神,也能体现当代的都市生活。委托之前,他把刘家琨写的小说、建筑杂文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最终确认自己的人选只能是刘家琨。这个决定证明了杜坚的建筑眼光和城市理想。刘家琨、文德斯与杜坚在西村大院的屋顶跑道
韩国济州岛的建筑师们在慈竹院吃火锅
2016年西村大院落成,开始投入使用,至今四年多。成都文化圈在大院里办活动、外地外国的朋友来参观,都让刘家琨一年里得往这里跑上好多次:
德国导演文德斯夫妇来溜过弯,韩国济州岛来的建筑师们在大院的竹林下面吃过火锅,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在这里喝过茶。

西村大院里种了将近30种竹子:慈竹、粉单竹、斑竹、紫竹…… “满足成都人幸福的指标:竹下生活,” 刘家琨说。
设计之初刘家琨对大院里的活动场景并不做预先设定,只是根据大约会聚集、活动的人数,框定出尺寸不一、形状不同的场地,做上些高低不同的混凝土长凳、吧台、台阶,至于在其中怎么活动、怎么用,自由度全交给市民。
相比于具体的设计,他更在乎这些公共空间是不是真的能被用起来:
“它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有一个广场、有一片树林但不让人在那活动,那也不叫公共空间,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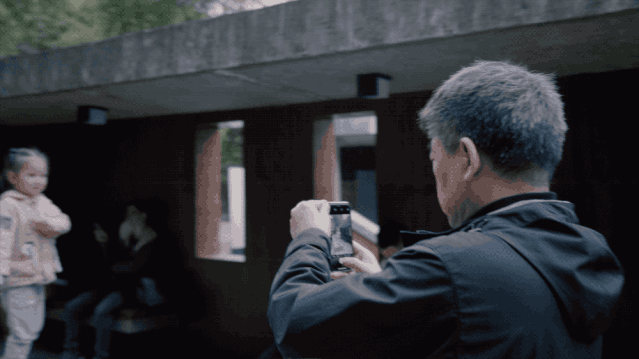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在许多大型公共建筑的实践中都引起过讨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de meuron)在设计鸟巢前到北京考察,他们看到天坛东门游廊里自发聚在一起唱歌的北京市民,因此在鸟巢底层设计了围绕建筑的空廊,希望即使没有比赛,也能让市民们去休憩、游乐、唱歌……现实中环廊设计了出来,但进鸟巢收取的门票阻挡了市民前往活动的脚步。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构想国家大剧院时,希望冬季的水池吸引孩子们去上面滑冰,冰刀划出的弧线成为地下通廊上方不断变幻的抽象图案。但最终实现的水池,却引进了保证冬天水面永不结冰的水循环系统,防止上人。

以西村大院为原型制作的装置”人山人海“
这其实都是刘家琨口中的权利问题。而他自己敏锐的“公民建筑意识”的形成,与早年在西藏做建筑的一段经历有关。
1984年,在成都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刘家琨,被选中去西藏设计群众艺术馆。在那里,牧人们围着火堆唱歌跳舞、骑马扛枪的画面,不仅触动了他,也让他警醒:自己带去的设计不过是自作聪明,牧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我设计了一个物体,建筑首先是要和人有密切的关系。”

带着这样的想法设计房子、造房子,刘家琨收获了许多非建筑圈的真爱粉。与一条在西村大院里拍摄不到十分钟,他就被粉丝认出,要了签名和合照。画家老友方力钧评价说,“我接触的很多建筑师,其实都是人类的敌人。好多建筑师都在做一个壳,刘家琨在做一个整体,他考虑的事情是人的整个感受。”

西村大院的沿街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