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女一号宁可不演。”
2019年2月,咏梅凭借电影《地久天长》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成为中国内地首位柏林影后

《出走的决心》上映一周后,在豆瓣上获得8.6的高分看到很多我妈妈的影子,让我掉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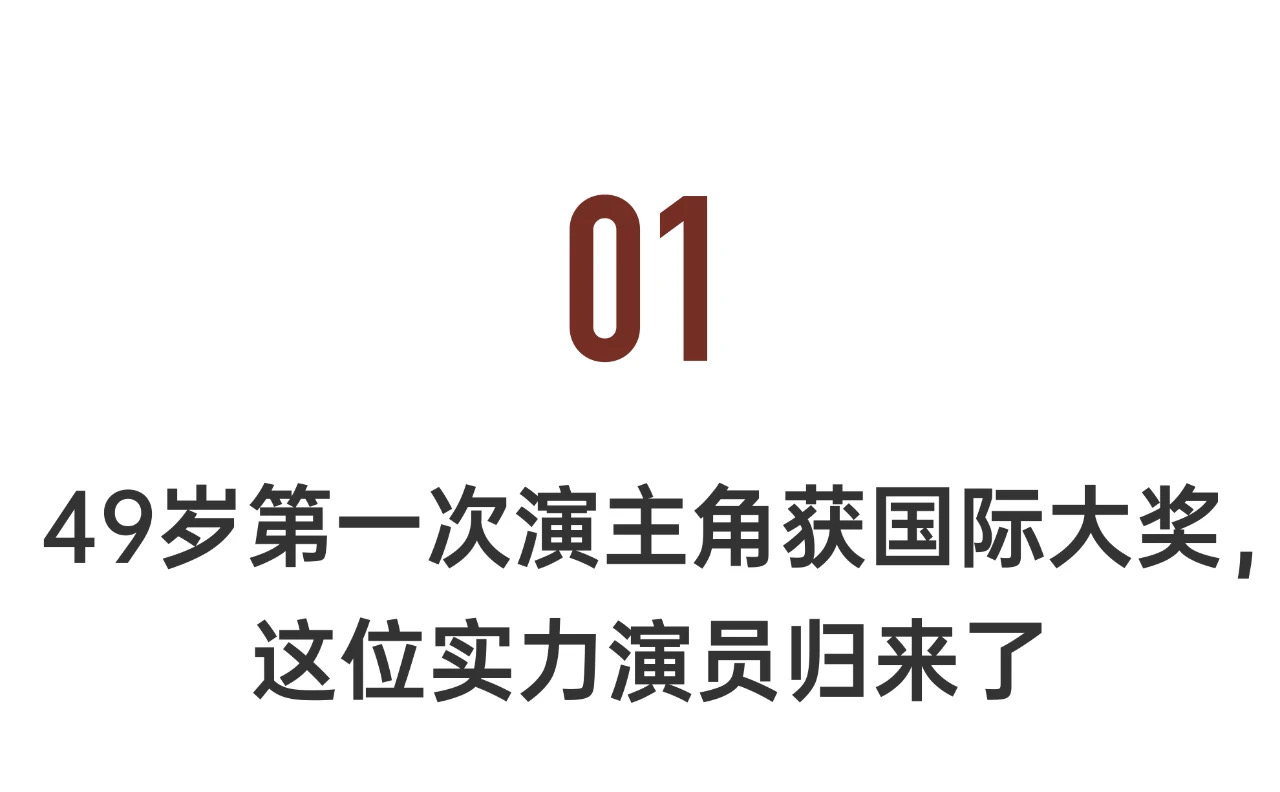

拿到柏林电影节影后的这5年里,咏梅一如既往地低产。她不上综艺,不演真人秀,真正担任主角的长片只有一部,就是前不久上映的《出走的决心》。
其他的时间里,她就在自己喜欢的电影里客串,虽然只有几个镜头,她都会认认真真地琢磨角色,小到台词的每一口换气、每一根面部肌肉的控制。
以前找到她的剧本是一年一部,现在是一年两到三部,现实是无奈的:“留给我们这个年龄段女演员的剧本,没有想的那么多。”
其实,也有不少所谓的“大制作”找到她的经纪人,但都被拦截了。对方常说,“这种国民度的项目,你们都不接”,随后面露惋惜,“多少人都排队等着”。咏梅接戏的原则很朴素,也很恒定:“故事要打动人心”。如果是个好故事,女二号也接,如果是浮夸的、流量导向的片子,女一号宁可不要。一个故事是不是动人,直觉和身体都会告诉她,多年前,拿到《地久天长》剧本的时候,她用了一个下午读完,眼泪都要流干了。
直到2022年,让她再次感觉到心灵共振的角色来了。咏梅在《人物》公众号上读到了苏敏阿姨自驾游的故事,几乎是同一时间,导演尹丽川也被这个故事击中。
“我们同时被震撼到了,一个50多岁的阿姨能有这个勇气冲破对她的限制。”一个困于母职的女人,用自己打工赚的钱买了辆面包车,义无反顾地离开酗酒家暴的丈夫、无爱的婚姻,在路上活出自己第二次的人生。电影《出走的决心》中,咏梅饰演的“李红”,大半生被困于家庭的桎梏中在一个全女团队的努力下,这部关于“现代版娜拉”的电影落地了。咏梅饰演的李红,原型来自苏敏,不一太样的是,这部电影讲的是“出走前夕”的故事,一个女性,她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要从家中出逃?
影片里,我们看到一个令人窒息的丈夫,对妻子颐指气使、打压她、贬低她,视她为自己的免费保姆;一个刚刚成为母亲的女儿,出于传统惯性将育儿劳动转嫁给母亲;一对重男轻女的父母,剥夺她高考的资格,一辈子指挥她的人生。
“在你身边的千千万万的像她一样的命运的女性,你看的太多了”,在角色李红身上,咏梅看到了部分的自己,也看到了母亲。
1970年,咏梅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平日里,母亲总是更偏袒哥哥,而她很早就要担负起更多的家务。父母离异后,咏梅和哥哥跟随母亲生活,整个家都是由母亲操劳。“她的婚姻给她带来了很多磨难,因为爸爸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妈妈并没有”,两人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的悬殊,把母亲置于婚姻的阴影里。
父亲是精神性的,热爱哲学和艺术,是电力工程师。每次见面前,咏梅经常很发愁,父亲都讲哲学的东西,又要听不懂了。但她心中的另一个世界也来源于此:“慢慢地你会觉得什么东西好像被点燃了,我会与众不同,我心里是有另外一个疆域的。”
母亲是普通工人,受教育水平不高,性格刚强,控制欲强,“像我们的上一辈人,都在传统的、被驯化的一种模式里面”。青年时代,咏梅和母亲之间产生过长时期的对抗,“她说什么我都是反着来的”,母亲不允许她穿喇叭裤,理由是女孩子不应该太招摇,她就偏偏穿去上学。直到人生中年,咏梅才开始理解母亲的局限。那个曾经在父亲面前“黯淡”、“世俗”的母亲,本身也是一个分身乏术的独抚妈妈,只能终日从工厂车间辗转到家庭内部,把生命囿于两个狭小的端点里。
母亲的心里其实装着一个更大的世界,她爱旅行,梦想是“环游地球”。1992年,咏梅大学毕业后,想要南下去深圳工作,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觉得那个地方很可怕,物欲横流”,母亲却是坚定的支持者,“你有本事你就出去,证明给我看看。”
咏梅的倔犟也来源此,她一辈子都在自证,“证明你是可以独立的,是不输给男孩子的,在社会上是有价值的。”


因为气质内敛温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咏梅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剧里出演符合传统期待的“好女人”,她是好妻子、好妈妈,也是好女儿。
2004年的热播剧《中国式离婚》中,咏梅扮演的角色肖莉,是改革开放后初代独立女性的代表,遭到丈夫背叛后,她主动离婚,独自带着孩子打理好生活,“活得体面”、“没有怨气”;紧接着在电视剧《孝子》里,咏梅演了孝顺善良的“媳妇”谢言,一个被称为“完美女人”的角色,每当丈夫工作至深夜回到家里,她准备好丰盛的晚餐,热情迎接;在电影《地久天长》里,她扮演的失独母亲王丽云,同样是一个善良、隐忍的女人,失去生育能力后,对丈夫心怀愧疚。在2004年的热播剧《中国式离婚》中,咏梅扮演剧中的女二号“肖莉”电影《地久天长》中,咏梅扮演失独母亲王丽云,也是一位善良、隐忍的妻子2020年,拿到银熊奖后的第二年,50岁的咏梅等来了全新的女性脚本,一个愤怒的、抗争的、想要复仇的全职母亲。这也是她和尹丽川导演的第一次合作。
当时,尹丽川请她出演女性主义剧集《听见她说》中的一个短片《重塑》。13分钟的片子,贯穿着她掷地有声的独白,遭遇丈夫出轨后,她拿起拳击手套,重重地打在沙袋上:“这次不要通情达理。我受够了。”为什么选咏梅?尹丽川导演敏锐地捕捉到咏梅身上的一种“汹涌”,是她平静面孔下被遮蔽的部分,“一种压抑下想要抗争和跳出来的那种汹涌”。
这是咏梅身上少有人了解的部分,一股决绝的、在无声之处抗争的力量。大多数情况下,她随遇而安,生命里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东西,但在原则上她旗帜鲜明:“只要选择了不做,无论是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去做。”
咏梅的个性不喜欢热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怎么审时度势,怎么周旋于小圈子、服膺于看不见的规则,她对此感到疲惫,“经常会说一些不恰当的话”,也因为这样,她一直跟演艺圈保持了一种疏离的关系。

在影视圈,咏梅不接电话是人尽皆知的。2004年,《中国式离婚》开播后,收视率一度飙升至20%。走在街上,咏梅开始被人认出,有人喊她在剧中角色的名字“肖莉”,她不得不戴上墨镜、帽子,像个明星那样把自己包裹起来。
“好像自己已经很了不得了,跟朋友的相处,有点高高在上了,会忽略别人的感受”,电话、饭局也朝她涌来,她敏感地察觉到这种生活背后的代价。
不久后,她关机了,从此再也不接电话。近20年过去,她只用短信、微信回复工作,“真正的好的、我想要的,它一定会来找到我的。”如今,咏梅的电话,基本上只给外卖、快递员敞开。

另一种汹涌来自于她骨子里对“打破常规”的渴望。年轻的时候,她开越野车,喜欢骑马,享受风驰电掣自由的感觉,“很喜欢去撒个野,是那样的”。童年时代,“我好奇心重,把家里的钟表拆了,自己拿弦去做古筝,然后尝试着把各种菜混在一起,看它有什么味道”,“很小的时候哪怕跟爸妈撒谎什么的,就为了让自己的主权在我的手里。”
这些年,咏梅开始研读女性主义书籍,认真回顾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她时常想起,母亲也有疯的一面。母亲爱骑马,荡秋千,能把身体荡到和地面平行,70岁的时候,她还要求咏梅带她去坐海盗船。她不断确信,自己身上那部分“野孩子”的基因继承自妈妈。
和母亲很像,咏梅的个性也曾激烈过。平时话不多,一旦爆发,就在沉默中炸出一片火花。不久前,发小跟她聊起童年往事,“咏梅,你小的时候脾气可不好了,北京有一个话叫‘短捻的炮仗,一点就炸了’,你就属于那样的。”
她曾经给《人物》讲述过一个故事,读大学的时候,她和室友因为挡床铺的帘子到底拉向哪边起了争执,一气之下,她把帘子剪成了两半,室友被吓了一跳。如今咏梅已经不愿再提起这个故事,“我怕她看到了好伤心”。咏梅参演黑豹乐队的MV《Don't Break My Heart》她后来追溯,曾经极端化的情绪源于成长里爱与沟通的缺失。小时候,咏梅总被家里人评价“不像个蒙古族女孩”,蒙古族姑娘应该能歌善舞,她却总是怯场的,回避的。
这种表现经常被误认成一种“内敛”,咏梅后来明白:“其实是自卑,因为觉得不如哥哥,你处处都会帮妈妈,她还老去指责你什么的,不被关照就会自卑。”
自卑和狂傲曾在她的身体里此消彼长。刚入行的时候,咏梅有过争强好胜的阶段,“非女一号不演”,“明明制片人也说了我演女一号是合适的,但为什么就没有选我”,愤恨和嫉妒积压在她心里,日常生活都无法顺利展开。
她也看到这个世界里那些不公平的东西,诸如圈子里的论资排辈,人际关系中的虚与委蛇,面对这些,她的内心波澜骤起,不能平息。
她现在回想:“这些东西都让人变得很丑,人很容易这样会被欲望这种东西俘虏。”


欲望和情绪有时就像一匹野马,如何驾驭它,而不是被它驾驭,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
20多岁在北京的时候,蒙古族姑娘咏梅第一次真正地开始学习马术。骑马是因为丈夫栾树,当时栾树已经离开黑豹乐队,用全部积蓄在北京西郊建立了一个马场。
很长一段时间里,栾树经常入不敷出,两个人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过着世外桃源的日子。就像蒙古族民歌里唱的那样悠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2021年,咏梅和丈夫栾树共同演唱《一江水两只鹅》。咏梅说:“每一个人最终是孤独的,但是人的生存、生命还是离不开情感的,那么为什么不在一个好的关系里?”被激荡的情绪左右的时候,咏梅就从栾树身上观察“练习平静”的方法。她多次提起丈夫栾树对她的影响,“他的性格是很温厚的,我急的时候他觉得不急,因为他是有很多爱的那种人。”
阅读也是她归于平和的方式。大学毕业后,咏梅曾在深圳感受过欲望对人的那种隐形的控制。90年代,深圳可以接收到香港的电视台,各种娱乐化的综艺在内地是看不到的,“很吸引,每天好像只有电视了”。
“后来有一天,我觉得我不能把这么好的时光全放到这个上。我试试关电视,开始读书。”几次之后,咏梅发现放弃电视没有那么困难,她从三毛的书开始看起,她看到了一种更富冒险精神的生活。她后来意识到,关掉电视其实就是修行的第一步。“从一点一滴开始,你看中的是什么,你要去取舍。”在当下的短视频时代,咏梅很少沉溺手机,翻开书,她的心就沉下来,这背后是日复一日不厌其烦的训练。
另一件常被咏梅提起的小事,是“一条裙子的诱惑”。当时,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消费主义比内地更早盛行,下班以后,咏梅经常会去逛百货公司,一条美丽的裙子,是她一个月工资的两倍。入睡前,咏梅闭上眼镜,脑子里想的都是镜子里穿着裙子的自己。
“那个时候是挣扎的,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条裙子?”有一些看得见的“捷径”在向她敞开怀抱。毕业以后,她时常被提醒,美丽给人带来的权力。找工作,她总是比别人更容易就被录用,进到公司里,她很容易受到男性的青睐,有各种方便,也会有一些有钱、有权的男性来靠近她,甚至包括已经进入婚姻的富商。讲到这段经历,咏梅平静的声音有了微小的起伏,“后来觉得好可怕”,“但其实骨子里还是有倔强的那一部分,再加上爸爸的影响,他从小就灌输我女性的独立意识”。父亲一辈子过得拮据,改革开放以后他拒绝赚不该赚的钱,“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就OK了。”两年后,咏梅从深圳回到北京,从许戈辉工作室的主持人做起,一步一步亲手搭建自己的生活。
年龄渐长,美丽成了她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拍杂志、广告,她要求摄影师不要把她的皱纹都P掉,她的手机里也没有美颜相机,经纪人说:“估计她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在她微博分享的照片中,她的头发经常随意地扎起,露出额头,素面朝天。
在演艺圈,咏梅很少感觉“身不由己”。演员常常被认为是一份被动的职业,她却认为,自己一直是有选择权的,不迎合也是她选择的方式之一。
2006年前后,她发现影视行业的规则开始被商业化彻底改写,“变成快餐了,没有给你创作的时间。”咏梅记得有一部剧,她去跟导演讲那场戏的处理方法,对方说,你不要跟我讲戏。“最夸张的时候,一天要拍几十页,只要你把这个调度走完了,一场戏就结束了。”这种流水线的工作模式让她觉得无意义,“所以我其实很淡,有好的我就接,没有好的,我就算了。”2014年,演完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后,咏梅再度“消失”,因为父亲和母亲的相继离世,她用了4年的时间闭关,读大量的哲学、宗教、心理学,深入地思考生与死的议题。
在瞬息万变的影视行业,暂停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太多演员在离开演艺圈数年后,发现潮水的方向改变,自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位置。
但对咏梅来说,不经审视的欲望才是更危险的。“用自由换取(名利)的话,我觉得有点太奢侈了。你要争取让自己更有自由的这种生活方式,到此时此刻,我没有停止过。”

如今,54岁的咏梅,每天做饭、阅读、散步,认真生活。春天的时候,她静待春暖花开;秋天,等待果实的坠落。
不拍戏的日子里,她规律地去上瑜伽课,只是为了减少打扰,她不再去人多的大班课。她坚持天天做饭,西红柿炒鸡蛋做了半辈子,还是她的最爱,简单、美味、营养充足。做饭完全可以交给家里的阿姨完成,她却执拗地坚守厨房,“做饭是家庭氛围,那一刻两个人是在一起可以说话的。”
家务也要关照,下水道堵了、电灯泡坏了、灶台脏了、地板上又落了灰尘,都由她一一处理。其他时间,则尽可能关照自己。
每天下午是她固定的阅读时间,2-3个小时是一定得保证的。看书是从青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精神世界同样需要饱腹。

2019年起,咏梅和某知名图书品牌发起了一档阅读计划——咏读计划。5年间,她分享了50多本书,书单都是她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一定是要自己读过的,没有鸡汤,没有成功学,只有严肃阅读,从诗歌、文学到艺术史、社会学。
最近,她准备开始分享理想国出品的M系列,大部头,厚的单册多达五六百页。读书海报上印着那句“平静又沸腾的阅读世界”。
在被互联网技术全方位包围的当下,咏梅重视日常生活里“身体性”的经验,比如她给家中阿姨的留言,尽量都用手写,她相信这种细微的情感传递是微信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年轻的时候,她曾跟随潮流用电脑给父亲敲下了一封打印信,没想到,父亲严厉地回了她,“这个字是没有情感的”。

30多岁,她曾经在一档明星访谈中透露:“我的个性是不太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我会觉得,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是跟所有人是融在一起的,(这样)你不会觉得不自由。”
二十年过去,她仍旧没有让渡出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权利,仍旧是一个人群背后的好的观察者。走在街上,她为躺在路边树荫下小憩的女性外卖员而驻足停留,感受普通人在活着这件事里要付出的努力、隐忍,以及承受的琐碎。
对日常生活的执着,对人的悲悯,给了她好好演戏的养料。咏梅让很多人看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强烈的主角意识,也可以捍卫住自己的天地,就像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来自于《卜算子·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她在丛中笑。”每个年龄段都带给咏梅不一样的体验,年龄越长,她越懂得放下焦虑:“你自己快乐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为什么要让它占据你的那么多的生命和时间”50岁以后,时间前所未有地带给了咏梅满足与自由,她比以往都更加从容。面对媒体的喧嚣,她已经知道如何去接住它。
“通过学习来建立你心里的精神世界的更大的一种辽阔,所谓的困难,恐惧,你都会有方法和渠道去解决它,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