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国高考人数1342万,
再创历史新高,
或将成为史上最“卷”一届高考。
过去几个月,一条对谈了3位学者、教育家,
涉及当下最热门的教育话题:
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有解吗?
从“小镇做题家”到“常春藤精英”,
阶层差距如何通过教育传递?

▲
陈美龄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三个儿子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如今各有所成
教育学家陈美龄,
曾是与邓丽君、山口百惠齐名的传奇歌星,
也是一边带娃、一边攻下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学霸妈妈”。
她的三个儿子都考进了斯坦福大学。
她聊到当下父母们的教育焦虑:
“我更希望家长不要那么紧张。
时代真的很快,可能很快AI就什么都帮我们做了……

▲
谢爱磊希望为更多的农村学生做一些事情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谢爱磊,
从2013年起追踪了2000名“小镇做题家”,
发现他们往往会自我低估、自我设限,
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才能拿到普通的剧本。
他们很难凭借学历实现阶层跨越,
只能用“做题”的思维,

▲
姜以琳现任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2023年因《学神》一书成为皮埃尔·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的首位非美国籍获奖者
台湾学者姜以琳,
则用7年时间聚焦了富裕家庭的“名校精英”,
她指出:“阶层复制就像打牌一样,
精英学生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天生拿了多么好的一副牌,
同时也不让那些拿到差牌的人意识到,
责编:陈子文

一条
https://dldir1v6.qq.com/weixin/c ... 11533a600.png");">
就这么过了两年多,我写完了论文。通过的时候,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我真的成了博士。


“美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的通过。曾经,有在公司里面设立托儿所的例子应该是5间左右,现在是5000间;那个时候女性希望去工作,一定要问她的丈夫的意见,现在不用。但还远没有到理想的状态,还是存在收益收入不平等、家庭育儿责任分配不平等等问题,性别处境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从偶像成了博士,身边的人看我的眼光开始不同。他们开始相信我,也尊重我的意见。我可以做很多文化人的工作,也可以帮其他的女性更加有信心地回学校继续学习,我觉得是很安慰的。陈美龄很喜欢孩子,作为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协会的大使,曾经多次远赴非洲探望当地的孩子我觉得教育是教小朋友去梦想。首先给他们看看世界是很广阔的,你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你要去寻找你最喜欢做的事。等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工具,教他们要有勇气去踏出第一步。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失败,失败的时候我们教孩子要坚强,站起来继续去做。要是很幸运地成功了,要谦虚、要分享。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医生,做律师,让他们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这就是我的教育的理想。我大儿子三岁的时候和我说,他将来想做厨师,于是他很小的时候我就教他做料理。九岁的时候他突然说他不想做厨师了,我还有点失落。不过也有好处,他现在做菜也很好吃。还是这个孩子,在斯坦福大学读的是工程师的专业,但快毕业的时候突然跟我说,想要放弃一切去当一个救护人员,他希望可以救人的性命。救护人员要读两年才能考牌照,而且薪水不高、很辛苦、也没有很多发展空间。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善良,真好。我马上说,好,那妈妈再供你读两年,你想要帮助别人,我为你骄傲。很多家长会咨询我,问得最多的还是小孩子不肯好好做作业、成绩难以提高等等问题。我是有很多小方法可以让小孩子读书不那么辛苦,但我更希望家长不要那么紧张。时代真的很快,可能很快AI就什么都帮我们做了,分数可能完全没有用了。怎么样才能超过AI?AI是大数据的,以前人家想过的事它才会知道,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小孩子超过AI,就要培养小孩面向未来,想到以前人家没想过的事情。培养小孩有“人性”,这是最重要的。要哭、要做错事、要后悔、要开心、要爱人、要恨人,这都是人。我们现在的教育好像训练我们的小孩子做机器,但我们不要小孩子做机器,要让小孩子做一个很生动的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不喜欢上班,他们觉得我这么辛苦,难道就是为了公司吗?他们想休息一下,这是一个新的趋势。我觉得爸爸妈妈最重要的就是理解。不需要非得告诉ta要走什么路,让ta自己慢慢去想一下,可以的。刚才也说过,这个社会转变得很快,而且现在我们的人生是100年,让年轻人偷懒两三年没问题,让他们寻找一下,迷茫一下,也是可以的。可能等他们思考过之后,他们发出来的力量更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包容,然后接受ta,告诉ta,你还是有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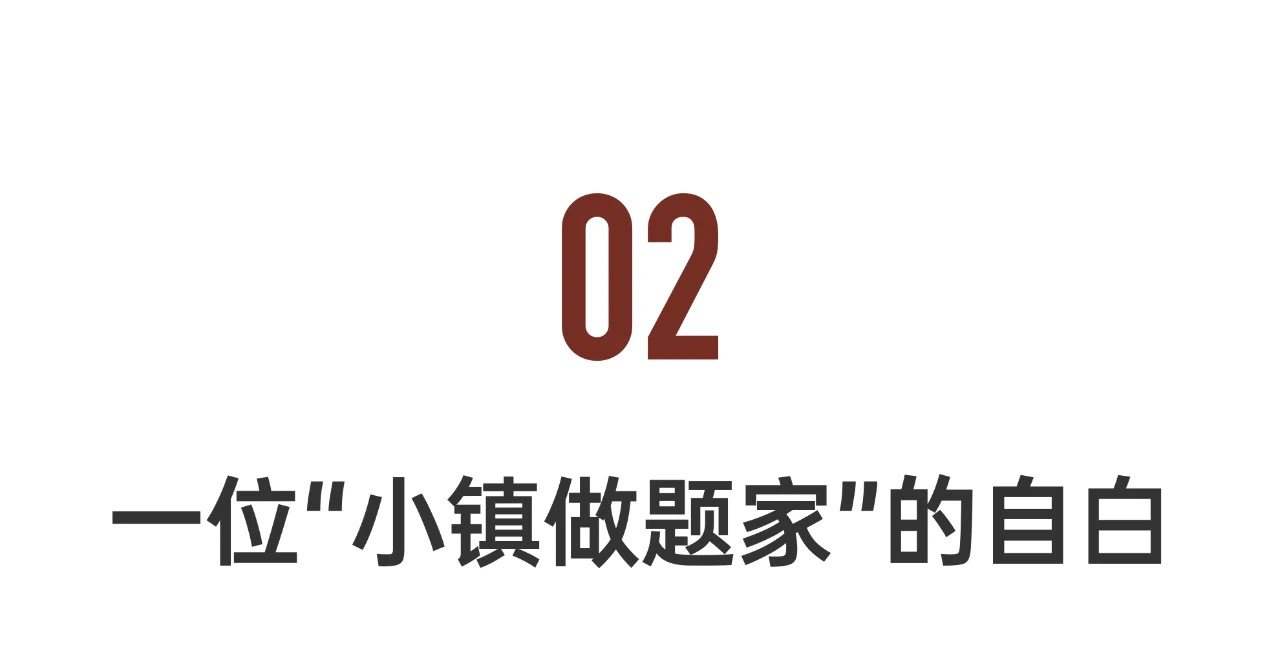
2020年的时候,“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在线上火起来了。有三条标准:1、出身农村或者小镇;2、擅长做题,通过高考,进入一流大学;3、缺乏视野和资源。每一条都特别的客观,好像是摁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一样。包括出现了一些污名化的现象,说他们“视野狭隘”、“综合素质不高”、“没出过什么远门”、“格局小”、“只会做题”等等。但不是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所谓“小镇做题家”。我在安徽农村长大的,那时候还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
小学是在村里上的,条件很艰苦,一下大雨,老师就不让我们上学,怕建筑塌了。也没有课桌,只有桌面,底下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普通话,都用方言带我们读课文。从小学到初中,我从来没有讲过普通话。高中到了市里面,大家都讲普通话,我一下傻眼了。因为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不敢讲,我的同学很多人觉得我是哑巴。
我高考考得很好,是学校的文科第一名,但是填志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扰。我们小村子里面就没有谁上过特别好的大学,最好的是安徽大学。想着综合类大学学费比较高,师范类学校可能会有学费补贴,所以我最后就填了华东师大的英语专业。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北大是可以上的,比复旦的分数线也高了二三十分。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老家给孩子们补课的时候,我更加深入地意识到,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够、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我想把这些困扰表达清楚。2013年,我在4个985学校,每个学校找500个学生,分别在他们大一结束、大二结束和毕业半年后的三个阶段,先进行问卷调查,紧接着做访谈。我其实一直不太愿意把我研究的学生群体叫做“小镇做题家”。我最初的研究想法很简单,就是精英高校里面的农村籍(包括农村和乡镇)学生。我跟学生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他们说,“这个类型说的好像就是我”,“我觉得好无力、好悲哀”。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要给人力量的,而不是把人框在一个架构里面,让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从而失去了向前的动力。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一些共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高中生活就是“培养做题机器人”。早上6:30起床早读,上午四五节课,下午四五节课,中间吃饭吃个5分钟,晚上10:00回宿舍以后还得学习。很多同学都因此出现了健康问题,甚至延续到大学以后。这种高度竞争性的教育模式,让他们对于自己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完全没有想法。到了大学以后,面对突然的空闲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我的一位受访者叫作小毅,他回忆说,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图书馆。每次经过游泳中心、学生活动中心,都没有推进门进去看一看。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说,“当初应当推开门进去看看的,也许这四年会过得不太一样。”
纪录片《出路》拍摄了不同阶层孩子的命运
左:来自甘肃马百娟在做完农活后读书
右:北京女孩袁晗寒辍学后在父母资助下,在游历欧洲
很多人会讲,农村的孩子很“自卑”,这么说好像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而忽视了背后的社会原因,其实这就是一种“谴责受害者”。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自我低估”,这和两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认知是有关系的。社会流动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生活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不那么值得肯定。那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童年其实也挺美好的,下雨天在稻田里面玩,会放鞭炮,会恶作剧什么的。
但是一到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当中,得到肯定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会才艺,会跳舞、会唱歌,会弹钢琴。农村孩子不擅长这些,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社会能力不如别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做一些探索的时候,就会发怵。我们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不像父辈那一代,有个大学文凭可能意味着很多。尤其是现在,你还要做很多的事情,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积累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资本……这些用刷题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处于竞争的劣势了。但是不是年轻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思考,他真的就不会赋予自己生活意义?我想可能低估了我们年轻人。我访谈的所有学生,其实每个人都会反思,都尝试去改变。当他们在用“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自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做反击了。
现在我是教育科学学院的,我的学生将来大部分是会做老师的。我会尽量培养他们的社会学思维,让学生看到社会阶层方面的教育不平等。同一个群体内部,有些人能上大学,有些人不能上大学,就是努力不够或者智商不够。这是“贤能主义”与“优绩主义”给我们的故事版本。我想驳斥这个版本。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农村来的孩子不太善于向上社交,这样会错过很多机会。我就带着他们跟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一个个吃饭,院长、副院长、系主任还有教授都吃过了。我特别鼓励他们出去,在周边旅游,我还会送一些票给学生,让他们去听听音乐会,看看展。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将来就是你们要教的那些孩子的眼睛。
中国人还是比较信奉教育改变命运的。但是假如我们的教育只剩下标准答案和高分数,只剩下优胜劣汰和成王败寇,那么它就注定只能制造“小镇做题家”、“大厂做题家”,而不能使我们的学生看见更加丰富的选择,拥有更加丰满的人生。在我看来,教育不是让他们看到另外一种生活高大上的地方,而是重新去肯定自己原来生活的一些价值。这个可能是教育更加终极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久地解决一些内心的困扰。

一条
https://dldir1v6.qq.com/weixin/c ... 11533a600.png");">
从2012年到2019年,我花7年的时间追踪了28位“精英学生”。他们就读于北京市排名前5的两所中学,并且都来自于富裕阶层。
他们的家庭收入是全中国城镇的前10%,中位数是前10%的至少两倍以上。父母们不乏清华北大的校友,还有留学生、博士。
调研中,我发现,越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越容易对人群进行细分。
在我所调研的两所中学里,可能有1/4的学生都能上清华北大,在这群人数很narrow(窄化)又非常优秀的学生中,学霸和学渣已经不足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们有更细分的四级地位体系——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最高高在上的就是学神,看起来没在念书但就是成绩很优秀;学霸成绩和学神差不多,但每天都在努力,临考前要开夜车;学渣就是成绩不怎么好,也看起来没在读书的;学弱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虽然很努力地学习,但成绩还是不太好。这里引入了一个“可感知的努力程度”(perceived diligence),俗称松弛感。“学神们”热衷表现自己的松弛,来稳固自己金字塔尖的地位。尤其是上了大学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和那些出身小镇、整天学习的“做题家”们划清界限,把后者排出自己的圈子。我调研的父母里,他们习惯性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其实,他们付出的可太多了,从心理咨询到课业辅导,再到孩子的生活起居,规划孩子每天的时间安排,精细到每5分钟、每10分钟。
精英父母往往是很擅于谋略的。他们看得到10步以外的距离,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步到位,怎么做最有效率;他们知道怎么做能让小孩容易接受,也最皆大欢喜;他们懂得在社交关系里应对进退,能够榨取到别人不想告诉你的独家信息。
28位学生里,参加高考的有17人,其中11位都通过自主招生以及其他政策获得了加分。其中包含一些非常隐秘的加分方法,比如奥数冬令营。当时,有一位名叫浴朗的女生意外在奥赛中发挥失常,失去清华的保送资格。她的妈妈很快跟学校的奥数老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后打探得知,如果送女儿参加北大举办的一个奥数冬令营,就有机会获得60分的高考加分。后来,浴朗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这位母亲有很强的危机管理意识,她知道老师身上有隐藏版的讯息,懂得如何靠关系网去获取这些内部消息。精英父母给孩子的经济支持也是让他们成功的关键。有一个学生因为SAT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一年之内往返新加坡5次,其中包括机票、酒店、报名费,就是为了能让孩子能在分数上更高一点。
精英群体中,常常会看到一种“我配得”的心态,就是“我够好”、“我值得”,这和东亚语境下,人们普遍的“不配得感”形成了反差。他们在成长过程之中遇到什么需求,只要表达了,就会有人来帮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心态。精英复制就像打牌,少数玩家拿到一手好牌,大部人拿到的则是普通的牌。拿到好牌的人擅长使用各种策略,拿到烂牌的人却常常无计可施。
精英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靠实力得来的,而且喜欢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天分”。天分这两个字非常地模糊,它把家庭背景、学习习惯等后天的因素,也全都浓缩其中。这种天赋说,合理化了他们从家庭传承来的优势、抹平了不同人之间的资源差异,让一切的分化看上去合情合理。精英“天经地义”的态度也是全社会默许的结果。这些年,媒体上经常会渲染一些超级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爱凌,近期大火的“天才少女”郭文景,媒体报道他们的“努力”与“天资”,但翻看他们的出身和履历,其实对大众来说并没什么借鉴意义。我在《学神》里说精英们其实是现在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蛮重要的推力之一,这群学生他们本身的存在,以及他们被教育出来合理化自己优势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在造成不平等了。所以停止“天赋能力说”,意识到精英复制背后的机制、方法,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