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时大家听评书、看电视剧,故事中似乎动辄便是“正德游龙戏凤”“乾隆六下江南”“咸丰圆明园四春”……
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都心知肚明,其中的“正德““乾隆“”咸丰”可不是皇上的名字,而是年号。

只要提到年号,在人们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就会涌出许多与历史相关的故事:说起“靖康”,人们就会想到北宋末年,皇帝被俘奇耻大辱的亡国痛史;讲到“开元”,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号就宛如一种历史的标签戳,给每段历史都打上了标记,其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清代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里说,年号“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不愧是“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虽然年号被誉为“千古不易之良法”,但它肯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事实上,和世界上大多数古代文明一样,在年号出现之前,中国人也是用最简便直观的方式,也就是用当政君主在位的年数来纪年。只是,这种纪年方式在统一的情况下还比较好说,一旦疆域内出现长期共存的多个政权,就很容易产生混乱。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这个时候还有周天子在,但每个诸侯国内部都是关起门来称孤道寡,用自己君主的传承脉络来记载事件,自说自话谁也不搭理谁。但这实际上非常麻烦——拿孔老夫子编撰的《春秋》来说,全书从头到尾是以鲁国十二代君主系年。如果只是研究鲁国史这倒也勉强足够,可是倘若某个学者想要跨越国别,用《春秋》去对照各种史料看能不能研究出点春秋“大历史”,那他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掉到坑里了——换算来、换算去。这一来一去,其中错谬在所难免。后世学者治史集讼纷纷,其中这种系年法带来的负面效应,实在难辞其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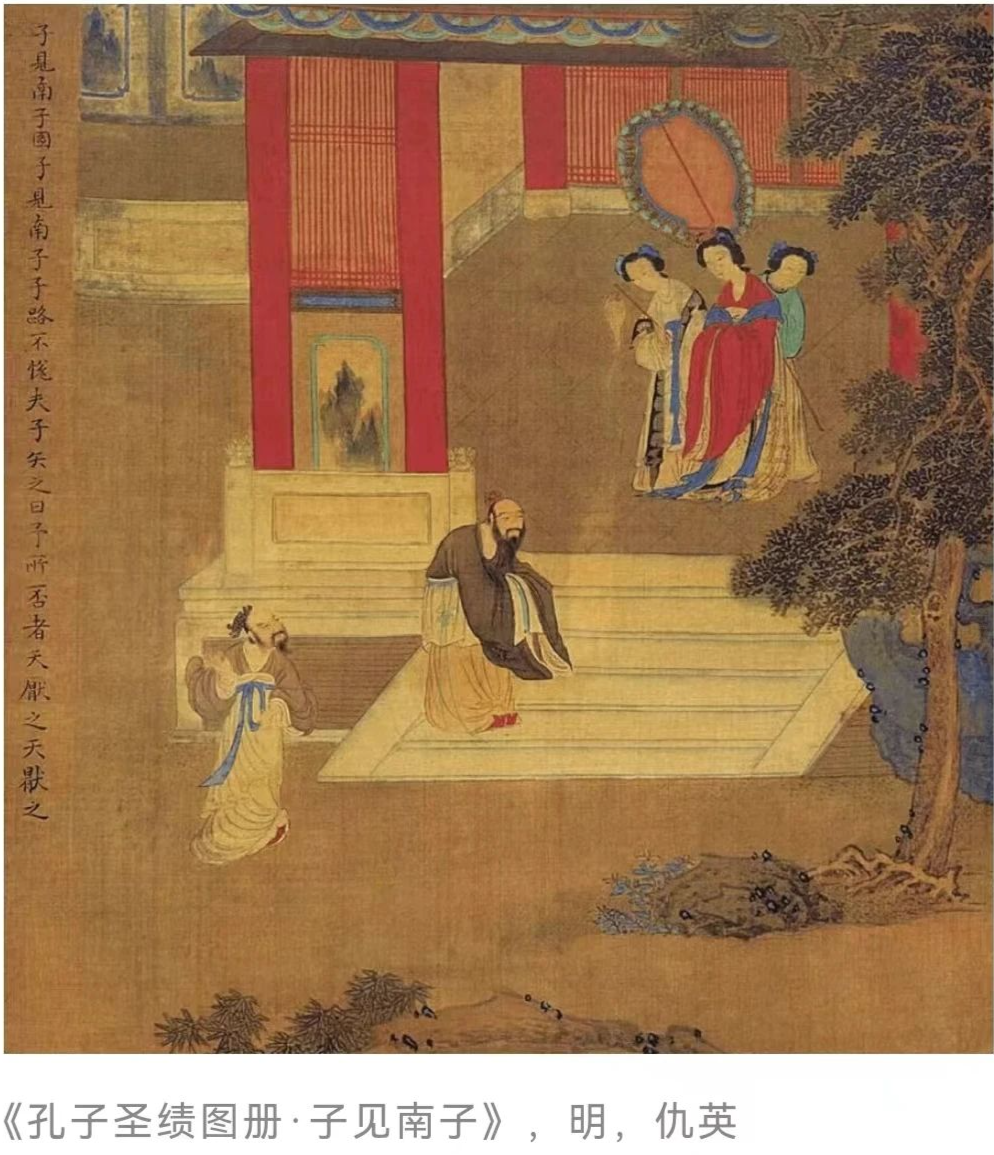
在分裂时代,这种系年会导致换算问题,那么到了大统一王朝,除了皇帝之外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统统都是某皇帝多少年,这总该没有问题了吧?
理论上如此,但实践中还是会出问题。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他们可以说汉文帝多少年、汉景帝多少年,但对处于这些皇帝统治下的时人来说,他们是不能这么称呼的,且不说他们不知皇帝死后谥号,就算是不上谥号的秦朝,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直呼“始皇帝”“二世皇帝”。因此,他们对于年代的概念完全仅局限于“今多少年”。比如写于秦始皇三十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只要提到秦始皇就是“今元年”,而稍晚一些时候,写于西汉早期的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甚至更偷懒,把吕后在位二年颁布的律令直接写作“二年律令”。
这种永远活在当下的记载方式,对书写者来说固然是方便省事,但对于后来查阅档案的人就不是那么友好了。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凑合着用。此时的君主也几乎没有改元的例子,都是一世一元,从继位开始一口气用到君主过世。就连创下扫平六国伟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也不例外,从始皇元年到三十七年,中间也没有搞出什么花样——大概因为这位始皇帝是讲究实际的法家,完全没有想到统治的纪元年份也可以搞出许多新奇说法来。所以只有到了儒家逐渐抬头的西汉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不少专家做好诸多开拓性的创新后,才能出现“改元”这种既有技术又有故事的操作。
所谓“改元”,顾名思义就是中止正在行用王年数,改用另外一个新元年,过去统统归零,年份从头算起。在汉文帝以前漫长历史中,此事只在战国发生过两起,分别是秦惠文王和魏惠王(也就是孟老夫子老在自己书里开涮的梁惠王),魏惠王改元详情不见史载,而秦惠文王是将通用的十四年更为元年。不过,这两人都有很正当的理由,他们是由侯称王,所以将以前侯年改为王年,以示自己和国家已经焕然一新。
改元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西汉文帝十六年。这年赵国术士新垣平让人拿着玉杯献宝,自己装模作样占卜一番,然后告诉文帝刘桓说:“阙下有宝玉气来者。”皇帝派人去看,果然发现有人献玉杯,上面刻着“人主延寿”字样。没过多久,这个新垣平又忽悠皇帝说:“臣候日再中。”也就是说他要给汉文帝表演一场大型魔术,一天之内让太阳两次经过最高点。根据史书记载,这场魔术很成功,“居倾之,日却复中。”龙颜大悦的刘桓觉得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吉兆,太阳能经过中天两次,那么自己统治也可从头再来,于是下诏将明年十七年改为元年,还特地下诏让天下每村每户可以吃酒宴会,而这次改元也是正史中公认的首次改元案例。

地球不可能停止自转,太阳也不可能一日之内重回中天,所以新垣平肯定是在弄虚作假,最大可能就是买通了观察天文的官员。事实上,这位神神叨叨的魔术师后来就是因为被人揭穿老底而遭到“诛夷”。不过,新垣平个人生死并不妨碍“改元”这桩大事进入政治生活,虽然作为皇帝,汉文帝刘恒已经升无可升,但他还是领会了“改元”这一操作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改元”归零,具有祈求“与民更始”“延年之祚”的神圣意义,这种操作不仅是在祈求帝王本人万寿无疆、生命长驻,更重要的是寄托了延续国祚、除旧布新的重大意义。其中的政治含义,在后来西汉所颁布相关诏书中将写得清清楚楚:“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武帝元封改元诏),又或者是“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哀帝太初元将改元诏)。其中说得很明白,就是过去事情一风吹了,现在皇帝开恩,重新开启统治的新纪元,他的统治自然也就会长久地延续下去了。
正是文帝时起,改元就逐渐成了统治者的惯例。不过在文、景及汉武帝初期,改元还没和年号扯上关系。史书上对此时标记的“中元”“后元”,只是后人为了区别的方便称呼而已,时人则不会说什么“中元某年”“后元某年”,只是将前后两次都称为“今上某年”而已。实际上,当汉武帝刘彻继位时,改元已经成为朝廷一种日常操作。加上继位,他一共改元十一次,前七次六年一改,从太初开始四年一改。这几乎成了制度,在他之后的西汉各帝也大都是六年或四年一改。
如此频繁地改元,自然很容易在记录上发生混乱,作为一名英主,刘彻自然要对此采取措施——让年号和改元相结合,每次改元都冠上一个美好的名字,看上去就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之道。因此,改元与年号的历史性结合,在“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手中完成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之事了。就连后世不少学者也认为年号和改元合流,就是因为刘彻改元太多,“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曹魏王朗言)
此话不无道理,汉武帝共用了十一个年号,大多数年号的取名过程都是一场大型拍马屁现场,让人解释得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比如第四个年号“元狩”,起因是刘彻某冬天猎到一只异兽,“一角而五蹄”,觉得稀奇的他只是想让群臣认一下到底是啥东西,结果一个叫终军的近侍(谒者给事中)就开始借题发挥: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啥,但想来是因为皇帝陛下伟大,所以就像昔日白鱼主动跳到周武王船里一样,神奇的异兽也自动出现了!(“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于勒成,专神明之敬⋯⋯而异兽来获,宜哉!”)总之结论就是,这是上天给皇帝您的嘉奖,您不妨因此改元,取个好听的名字来纪念(“苴白茅于江淮,发嘉号于营丘,以应缉熙,使著事者有纪焉。”)。汉武帝看了之后,“甚异之,由是改元元狩”。接下来的“元鼎”则更是一场刻意表演。齐国方士公孙卿听说有人在汾阴后土祠非常巧合地发现了一尊古鼎,觉得自己也有机可乘,就编造了所谓“朔日冬至”的良辰吉日,证明汉武帝统治下天人感应,祥瑞双至。他先是想通过一名叫作所忠的侍从献书,结果就连这个“幸臣”所忠看了之后也觉得马屁拍得太过了,就回绝说宝鼎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你还想咋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但事实证明所忠完全不懂武帝的心思,公孙卿另找“嬖人奏之”,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悦,“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后来宣布此次改元为“元鼎”。不得不说,刘彻的这个制度创新收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正是从他统治时期开始,年号和改元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纪念意义,成了封建王朝中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事。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0年5月上,原标题为《改元与年号,汉武帝的政治大发明》,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