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山西的一个乡间无赖薛良不断控告自己的债主张寅,指称张寅的真实身份是弥勒教首领、朝廷在逃通缉犯李福达,由此引发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这桩史称“李福达之狱”的大案,自案发到最终结案,前后历时三年,巡按御史、刑部尚书、未来的内阁首辅乃至于皇帝都下场角力,案情发生了两次反转。甚至在结案多年之后,再度翻案,余波难息。很多人将其视作正义与奸佞的斗争。可是,当我们深入案件内部,却发现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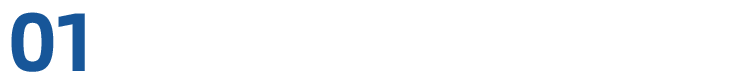
事情的开端极为平常,源于民间常见的经济纠纷。
原告名叫薛良,家住山西徐沟县同戈镇旁的白树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赌棍。早年与人通奸,因害怕泄露,逼得女子自缢身亡,被判处杖一百、徒三年,发配到同戈驿服役。薛良自然不可能老老实实呆在那里,很快逃役回来。被告名叫张寅,山西五台县人,是一个精明的“成功人士”。他往来两京、河南、苏杭、徐州等地做买卖,还在省城太原置办了八间门面房。在古代,大商人多半同时也是大地主。正德年间,张寅在同戈镇置买了房屋土地,此外在五台、太谷等县也有田地。有钱之后,自然要当官,恰好明朝允许买官,也就是“捐纳”。正德十六年(1521),张寅捐纳了一个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位,他的长子张大仁也纳银在北京充吏。无赖和商人,都属于流动的不安分的人,很容易就产生交集。当时,张寅在太谷、徐沟二县放贷。薛良就是他的客户之一,陆续向张寅借了15两银子,但一直拖欠未还。张寅多次向他逼讨债务,可能使了一些手段,于是双方结下了仇怨。嘉靖三年(1524)八月,薛良向山西巡抚毕昭举报:张寅其实是一个在逃的通缉犯——李五。李五何许人也?李五也叫李午,早年在陕西洛川县行医,暗地里宣传弥勒佛教,煽动信徒造反。正德七年(1512),洛川县发生叛乱,然而李五早已经不知所踪。这个消息,薛良声称是同里魏槐亲口告诉他的。事关谋反之事,巡抚毕昭当然不敢怠慢,立马下令拘捕案犯并进行审问。当时,张寅及其长子在北京,所以官府抓了张寅次子、三子及其亲眷。嘉靖四年(1525)二月,薛良上报称张寅手指生龙虎形,左肋有朱砂字样。五月初,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太原投案,称薛良是挟仇诬告。七月,薛良收罗到新的“罪证”,又上交了一份讼状。讼状中说:张寅原是崞县左厢都李福达,弘治二年(1489)参与造反,被发配充军。后来逃回,投认在五台县张子名户内入籍。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薛良的两次举报,信息都不够准确,比如他把张寅说成了张英,把李福达写成了李伏答,把张子名写成了张子贵。这说明,他的消息大都是听来的。不过,一个清晰的犯罪链条已经呈现:崞县人李福达,弘治二年谋反,被发配充军;逃回后躲住在陕西一带,以李五为名传教惑众,引起了洛川县的叛乱;后又脱逃,改名张寅,并冒入五台县张子名户籍。按明制,负责此案的是山西按察司。由于案情复杂,牵扯的人物、地点众多,加上调查能力实在低下,山西按察司的进展十分缓慢。五台县证实张寅确实有该县户籍。徐沟县证实薛良确实与张寅有仇。验看张寅的身体,也没有发现龙虎形和朱砂字样。陕西方面说当年与李五有关的造反者都病故了,无人可以证明张寅是不是李五。几个证人也推翻了之前的言论。魏槐说他只是和乡亲们聊到了李五煽动一事,从来没有与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五。戚广说,张寅是太原左卫指挥,从来没有聚众叛乱。嘉靖五年(1526)二月,山西按察司作出了初审判决:薛良乃是诬告陷害。审判结果上报巡抚,复审之后得出的结论一致。薛良将以诬告谋反罪被放逐到口外(长城以北)。至此,大幕已经拉开,原告被告两方对垒,一干证人悉数登场。然而他们并非主角,只是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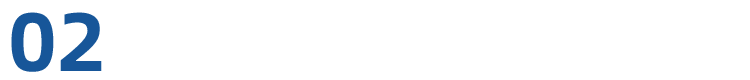
嘉靖五年(1526)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马录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请托信,里面写着“张寅是我旧识,被人诬告,不过因疾其富,乞矜宥”等话语。为官十八载,想必马录经历过无数的贿赂、求情和威胁,但是这一次他不得不谨慎对待。因为写这封信的人乃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武定侯郭勋。郭勋是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之后,承袭先祖武定侯之爵位。嘉靖帝即位之初,朝廷发生了“大礼议”事件。以杨廷和为首的文臣群体,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郭勋则果断支持皇帝,因而备受恩宠。
郭勋介入此案是一个意外。原来,张寅在京期间,四处攀附权贵,结交上了郭勋。其长子张大仁在京工作,应该一直与郭勋有来往。五月,张大仁不知案件已经定性,害怕自家有牢狱之灾,便找上郭勋,求其帮忙打点一番。这才有了郭勋请托一事。马录看完信后,立马翻开卷宗查看张寅一案,随后陷入了沉思。郭勋是什么人?一个得势的武人,仗着皇帝喜欢,处处和文官作对,多行不法之事。现在他写信请托,不正符合奸佞之人的行事风格吗?如果案件没有猫腻,他为何要替人求情呢?此案必有蹊跷之处。马录弹劾郭勋的奏章一公布,就激起了追求“正义”的浪潮。兵科给事中刘琦批评郭勋“求讨书信者,即是知情;党类受嘱者,意图贿赂”,甚至还分析了一番:“妖贼名李午,盖午,四正之时,正阳之位也。改张寅,盖岁首建寅,人生于寅之意也。”户科给事中郑一鹏称:“访得张寅情罪深重,乃知勋之罪有不止于专横者。勋明知张寅系谋反杀人首恶,自宜觉发,为国讨贼,乃与之往来交结。”御史潘壮上疏:“张寅,天下皆知其为李午;李午,天下皆知其为谋反人也。乞将张寅置之重典,郭勋解其兵柄。”在案件未查明之前,这些人已经认定张寅就是李午,就是李福达。弹劾郭勋者,包括马录在内,要么是都察院的御史,要么是六科给事中,他们都属于一个群体——言官。明代的言官十分厉害。他们的人数为历朝之最,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品级低,没有患得患失之念,不怕得罪人;但是权力重,二三品大员见了他们也得规规矩矩。朱元璋如此设计,是为了把一群有胆气、又熟读圣贤书的人变为“天子之耳目”,查不法,查贪官,查奸佞,使得江山永固。然而,士大夫有独立的意识,有“从道不从君”的追求。言官终究无法完全成为皇权的工具,在必要时刻,他们化身为“公理”的守护者,向皇帝宠信的奸佞宣战。马录的果决也赢得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赞美。吏部侍郎孟春称赞道:“昨劾郭勋,殊快人心,彼虽喋喋,愈见其非。”大理寺丞汪渊说:“昨见章奏,攻发巨奸,人心甚快,非有大风裁者致是。”工部侍郎闵楷说:“今睹发奸一疏,风裁百倍,中外咸服其公,奸雄已落其胆矣。”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马录更加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他要做的就是排除一切奸佞势力的干扰,走到自己早已认定的“真相”面前,揭开它的面纱。如果他失败了,所有这些追求正义的人不就会变成一个笑话吗?官府发现了许多新的人证。比如定襄县的韩良相,他在北京时认识了李俊、李二和李三,这三个人曾秘密地对他说:“我们是李福温之子,如今上官的张寅,的名李福达,是俺五叔。你们不信。取起帽看他是秃子。”韩良相立马查看,果然是秃子。陕西方面也解来15个见过李五的人,官府让张寅和一众皂隶站在一起,结果这些人一下就把张寅认出,扯住他说:“这是李五。”不过,案件依然存在许多疑点。比如,张寅当时已经66岁,可是依据记录李福达户籍的黄册,张寅应该才51岁。崞县县民杜文住说李福达娶了自己的姐姐杜氏,可是张寅的妻子明明姓林,而黄册里李福达的妻子却姓张。当然,这些疑点对于已经先入为主的马录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很快,他公布了再审意见:张寅、李五、李福达是同一个人,依律处以凌迟。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就仅仅只一个清官明断的故事。这不是马录作为言官的追求:如果正义仅仅止于一两个人的清白,却放任天下的浑浊,那么,这样的正义要来何用。因此,他们要将“正义”的火焰燃向朝堂,烧尽一切奸佞。
▲海瑞虽不是言官,但其他们的精神气质十分相似。图源:影视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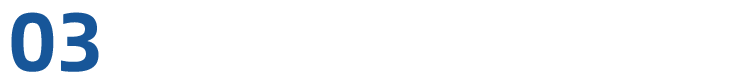
自他即位之后,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群体就一直提醒他要守规矩。天子之尊,如何能受人掣肘呢?幸好嘉靖帝对于权力的使用颇具天赋,他用左顺门的鲜血教育了这群士大夫,什么是为臣之道——君是主,臣是仆,该闭嘴时就闭嘴。“大礼议”一事后,嘉靖帝对文官极不信任,于是大力提拔身份尊贵的郭勋,用来平衡朝堂势力。自那以后,郭勋便常常受到言官的弹劾,罪名包括侵占军田、给亲戚走后门、剥削士兵等等。但在皇帝眼里,郭勋始终是个好同志。马录弹劾郭勋的时候,皇帝说这案子交给巡抚好好办,丝毫不提郭勋。张寅案再审结果出来之后,皇帝认可了马录的判案,但对郭勋只是口头指责了一下,明显不愿深究。言官对皇帝的偏袒十分不满,“正义”的追击随之爆发。众言官纷纷上疏弹劾郭勋,声势比以往更为浩大,其中有两份奏疏还是20多位官员联名的。他们的意思很明显:郭勋交通反贼,罪无可赦,不要再包庇。这时,皇帝的心腹张璁和桂萼说了这么一番话:“诸臣内外交结,借端陷勋,将渐及诸议礼者。”嘉靖皇帝想起了令他头疼的“大礼议”,想起了文官的集体哭谏,心里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置郭勋于死地,难道真的是为了正义?他们是冲皇帝来的,他们想用一种名为“公理”的力量,驯服皇权。想到这里,嘉靖对于李福达一案恐怕就已经有了翻案的念头。皇帝立即令锦衣卫前去山西接管此案,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及锦衣卫进行会审。此案会审共进行了六次,前五次均由刑部尚书颜颐寿主持,参与审判的官员不断增多,各个单位都有,遍及九卿、五府、科道,看起来十分公正。然而,主审官员不得不经受来自四方的压力,挣扎于皇权与舆论的夹缝之间。第一次会审有点敷衍了事,仅仅只是重复了双方的证词,没有发现新证据,维持了原判。嘉靖皇帝敦促会审官员“勿得徇情回护”。第二次会审,一个重要证人翻供了,李福达妻弟杜文住本来称张寅是李福达,在这次会审时,杜文住却说:“我是崞县人,与李福达无亲。我姐夫也叫做李福达,矮矮些儿,脸上有麻巴。”颜颐寿不敢也不想给出明确结论,只能列举供词,模糊处理。嘉靖皇帝一看,再次斥责主审官员徇私,甚至表示要亲自审讯犯人,经大学士杨一清等劝说,才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皇帝下令,必须要交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第三次会审,颜颐寿再次发现原告的证词存在疑点,但是指证张寅是李福达的证据链依然完整。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赞同原判。嘉靖皇帝再次告诫:“不许仍前回护。”皇帝一次又一次驳回官员的审判结果,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要翻案。颜颐寿事实上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继续维持原判,必然得罪皇帝;但如果改判,又如何推翻前面的证词,而且一旦改判,之前参与此案的官员都要遭殃。他能做的,就是寻求一个中庸的方案:一方面,仍然认定张寅就是李五和李福达;另一方面,承认无法证实张寅参与谋反。此外,颜颐寿上了一篇悲壮的奏疏,详细地记录了从马录审案到第四次会审的全过程。如果此案诬告,那么就代表整个文官系统都腐烂了,这是不可能的。皇帝已经听不进去了,直接斥责审案官员“朋谋捏诬,泛言奏饰”,命他们“戴罪办事,待再问明白,一总发落”。第五次会审,官员们要是还看不清形势,就堪称愚蠢了。有些证人“适时”地翻供了。马录主动承认失职。审案人员推翻了之前的结论,认定薛良诬告好人。事情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但是真相已经面目全非。假如张寅真的是李福达,因为年代久远,出现矛盾的证词极为正常;假如张寅不是李福达,任何一个疑点被忽视都有可能导致冤案的发生。从案件本身出发,张寅、李五、李福达三个身份,却是同一个人,证据链虽然完整,但并不通顺。而且证人的证词是否能作为核心证据有待商榷,证词是否忠实地记录下来也无法确定。当然,大人物们并不在意这些,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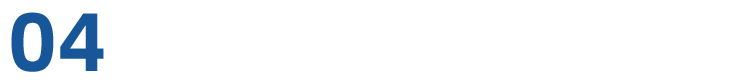
皇帝下旨全面更换主审官员,由礼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署掌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署掌大理寺印信。这三人从大礼议时就支持皇帝,是嘉靖最信任的人。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将不听话的朝臣定罪。一夜之间,仿佛命运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原来坐在审判席上的官员,尽皆沦为阶下囚。主要证人全部翻案了。马录家中搜出了不少书信,那些赞美他敢于“锄奸”的文字,被当成了官员勾结的证据。追求正义的言官们,被打成了挟私报复的小人。随后,皇帝指令桂萼等审理此案时“用刑推究”。这些人得到了尚方宝剑,自然不会心软。据说,颜颐寿素来看不起张璁、桂萼,他们便借此报仇,上了夹手指的酷刑,还笑着说:“汝今日服未?”颜颐寿忍受不了痛苦,不断磕头,说:“爷饶我!”当时,京师有一个《十可笑》的歌谣,其一就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书叫。”可见,审判之中不乏诱供、逼供、屈打成招的行为。不然也无法解释,所有被审官员全部认罪,所有重要证人全部翻供。很快,皇帝要的真相就呈了上来:薛良诬告张寅,秋后处斩;马录、颜颐寿等审案官员犯故意“入人死罪”,徒四年;众言官犯诬告之罪,徒四年。嘉靖看见审判结果,十分兴奋。这里面有不少人曾在“大礼议”中上疏批评皇帝,甚至还有人参与了左顺门的哭谏。如此一来,朝堂应该能清静不少。但他有一处不满意,对马录的处罚太轻。在他看来,这场文官集团挑衅皇权的战争中,马录是那个吹响冲锋号的人,必须严惩。正如当初那个顽固不化的杨廷和一样。皇帝想以“奸党”的罪名判马录死罪。桂萼等讨论后认为,处斩太重,原来的判决又太轻,干脆将其贬至烟瘴之地,永远充军,遇大赦也不宽宥。他们向皇帝解释说,要是置马录于死地,只是惩罚他一个人;永远充军,则祸及子孙。这样,马录看似活着,实则比死还难受。但皇帝仍不甘心,非要杀了马录,以解心头之恨。大学士杨一清劝谏道:“录无当死之罪,律无可拟之条。若法外用刑,人无所措手足矣。”皇帝这才勉强接受,下旨说:“马录情犯深重,你每既这等说,发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事后,嘉靖皇帝十分高兴,特意嘉奖了张璁、桂萼等人,夸他们“尽忠以事君”。皇权即是公理,只有忠诚才能行善道,否则就是徇私枉法。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个道理,嘉靖皇帝将张寅案相关档案编成《钦明大狱录》一书,刊行于天下。无论此案是不是冤案,嘉靖皇帝的作为都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一道旨意决定一场司法的现象,在明朝后期还见得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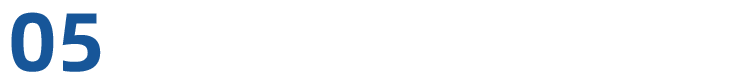
隆庆二年(1568)九月,右佥都御史庞尚鹏上了一道奏疏,重提李福达一案。据他说,他在山西见到了一名罪犯,名叫李同,传习白莲教,蛊惑人心,甚至引起四川一地的叛乱。李同自诉是李五的孙子,其供奉的祖师名叫李大仁、李大义,家庭情况竟然与张寅一家相同。这说明,张寅真的是反贼。庞尚鹏早年在读《钦明大狱录》的时候,就非常困惑,为什么一个案子前后判决竟然如此迥异?他遍访士大夫,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信《钦明大狱录》。人们口耳相传的是另一个故事:言官忠于职守,却被奸人打压。在皇权的压制下,无人敢公开反驳。但,皇帝只有一张嘴,而公理在每个人心里,“真相”终有重现天日的一刻。如今,迟到的“正义”终究还是到来了。庞尚鹏在奏疏中赞扬那些获罪的官员:“天地有正气,宇宙有正人,故天网地维,万古不坠。”庞尚鹏敢如此高调,也是因为时代变了。嘉靖皇帝死后,首辅徐阶大力革除旧弊,大礼议以来被打压的群臣都得到了翻身的机会。直到隆庆五年(1571)高拱为内阁首辅,这场平反运动才被叫停。
在庞尚鹏的奏疏里,出现了许多事实性错误,比如张寅明明是投案自首,他却写成马录抓捕了张寅,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读过《钦明大狱录》。而且,仅仅凭借一人之口供,根本无法确定张寅就是李五。李同是何时被捕的?审讯是何时进行的?真实的口供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再说了,张寅家境殷实,已经成功洗白了,为何还要继续从事反叛活动?这明显不合情理。当然,细枝末节并不重要,人们有时候只需要一个故事。此后,在明人的史书笔记里,几乎清一色都是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为那些受冤的官员抱不平。不少人找到一些未被埋没的“真相”。比如万历士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载:“(张寅)二子纳粟入国学,而大礼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勋。”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完全是后人想象的产物,却被当成了正确的“记忆”。只有少数人认为张寅非李福达。最有名的自然是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里面评价张璁时说道:“及奉诏鞫勘大狱,独违众议,脱张寅之死,而先后问官得罪者亡虑数十人,以是缙绅之士嫉之如雠。然其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终岁而一时风纪肃清,积弊顿改。”张居正赞扬张璁的做法引来了许多士人的不满。沈德符直接破口大骂:“大狱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灭以泯其迹,恣横至此,他日其后惨祸,谓非自取不可!”
沈德符是一个典型的追求“公理”的士大夫。他视皇帝为最高统治者,但维护的却是一种体制化的皇权,换句话说,守规矩的皇帝。这个规矩我们可以称之为“道”,而“道”为士大夫所掌握。实际上,就是要求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沈德符曾评价二张“皆绝世异才,然永嘉(张璁)险,江陵(张居正)暴,皆困于自用”。他明白,张居正和张璁是一类人。他们身怀大才,有志革新,于是奋不顾身追求权柄,最后难免走向刚愎自用。他们或媚事皇帝,或专权自用,在事实上都形成一种“独”的政治风气。而这种风气违背了共治天下的原则。马录未必真的想要忽视真相,沈德符未必真的想要篡改记忆,他们只是认为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当同道之人越来越多,他们自然坚信,这条路是正义的。然而,在不断强化的皇权面前,士大夫们虽有抗争表现,但更多的是忠顺、沉默、党争乃至摇尾乞怜。最后,在明朝这个庞然大物倒塌之时,士大夫群体发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声音。后世说这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很明显,并不是。君与相的传统格局,发展到了巅峰,就是这个样子:极端的皇权,以及畸形但蓬勃发展的士大夫群体。但是,正如李福达一案告诉我们的道理:细枝末节并不重要,一个完整的故事才重要。这是虚伪的、悲哀的理想主义者留给这个世界最有用的东西。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文献: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明]张璁等:《钦明大狱录》,《四库未收书辑刊》一辑第十五册,北京出版社,2001
胡吉勋:《明嘉靖李福达狱及相关历史评价考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2007
高寿仙:《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史学月刊》,2020年第8期
- END -
作者丨秦时避世人
编辑丨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