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称自己是“防疫钉子户”,在中国疫情全面解封后整一年,依然虔心恪守着全方位的防疫措施:
每天佩戴N95口罩或防毒面具;
坚持测抗原,几乎不聚餐、不堂食;
每天清洗当天衣物,或用紫外线灯消杀;
还有人在进门处搭起隔离棚,进行“半污染区”管理。
在孤独防疫的2023年,他们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有人和朋友从争吵到断交,有人终日蛰伏人群中,时时有如“惊弓之鸟”,更有甚者,离群索居,成了“当代隐士”。
事到如今,他们为何执着防疫?那就要进入他们各自的故事里——

何飞的防毒面具,从去年12月一直戴到今年夏天。那是一款售价超过1000元的头戴式防毒面具,类似一个低配版的钢铁侠头盔——它自带扬声器振膜,不需要扯着嗓子说话。直到天气热得不行,他才勉强换成“轻便”的N95口罩。
这一年来,何飞几乎戴过市面上所有主流品牌的口罩,像个“口罩专家”。他还用雾化糖精钠的方法,为小脸的母亲测试了15款口罩和2种防护面具的气密性,终于找到她的真命口罩。
他并不限制自己出行,不过但凡踏出家门,他绝不摘口罩,哪怕周围空无一人——为此,他以卓绝的意志杜绝非必要的饮食喝水——摘口罩要消毒,麻烦。
回到家,他立即执行严格的消毒SOP流程:开门,进入玄关“半污染区”。以酒精消毒双手、头发和口罩边缘。再消毒随身物品,清洗衣物,洗澡。
在那套约90平米的房子里,4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不间断工作。有的空气净化器品牌会在宣传中加上“工业级”,何飞就拥有这样的一台。如果可以,他也许想把自家空气净化到医院手术的无菌级。
武汉疫情爆发时,何飞在陕西念高三,得了普通肺炎。高烧13天,能用的药都用了一遍。同学在家上网课、备考,他整日吃药、打吊针。睡眠被发热拆成碎片,情绪像黑笔在纸上乱作一团,快两个月才恢复健康。
半年后,他复查拍肺部CT,医生看完交待他,你少抽点烟吧。可他从不抽烟。
“在病床上那样的时间,你活着和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说。
疾病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失去,失去身体的完整性和对生活的掌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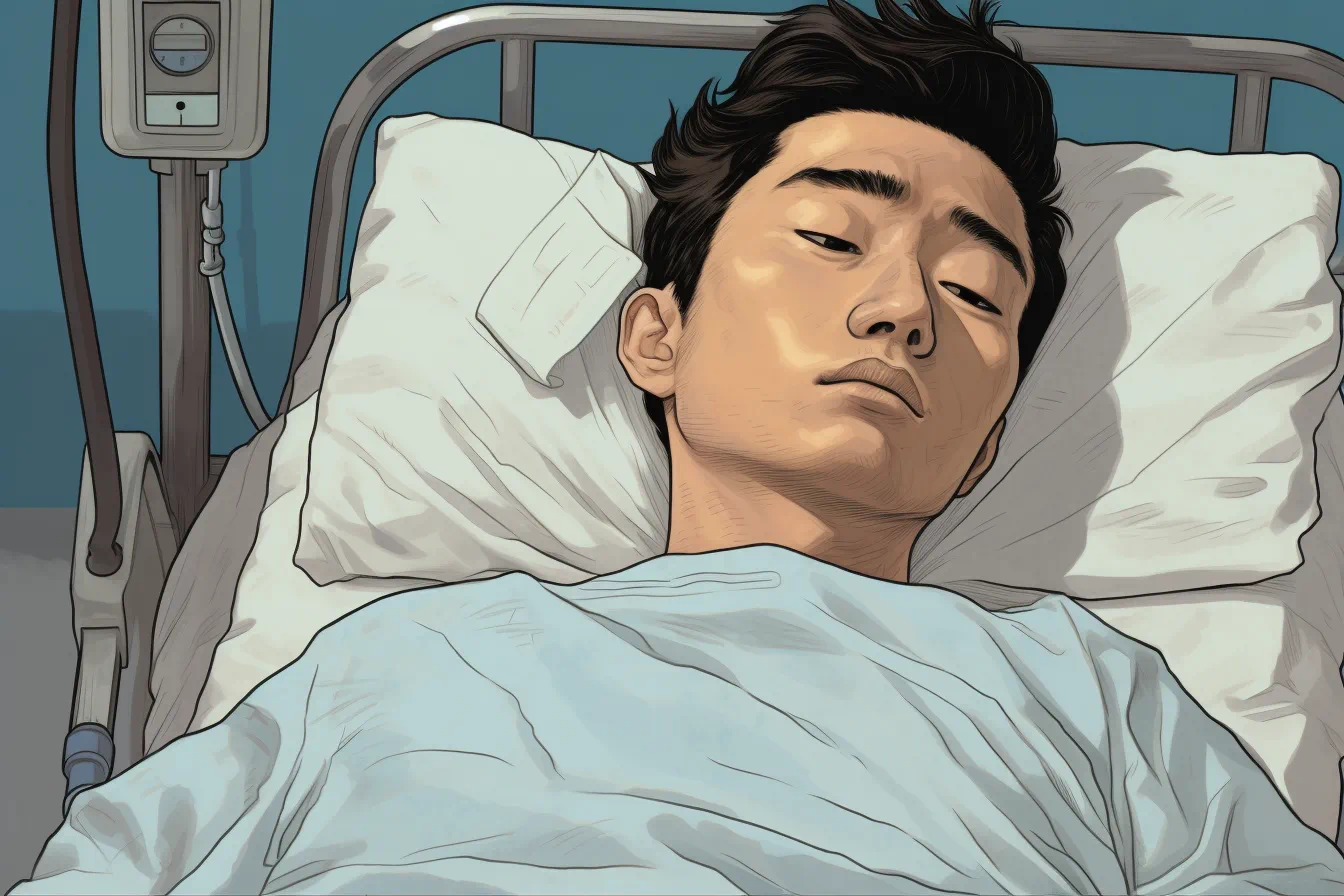
何飞再也不想生病了。这是他成为防疫钉子户的核心内驱:“我只想健健康康的。”
他囤了300多个新冠抗原,今年2月起,他每天起床睁眼,先测一遍。他的防护细致到了指甲缝——指甲剪得“很秃”,绝不藏污纳垢。
在硬核防疫的路上,何飞并不孤单。他加了足足11个“防疫钉子户”微信群。第一个群是去年12月建的,直到现在还有近300人。
他们在群里探讨防疫方法和物资。比如,除了酒精,群友们还会如化学巫师一般推荐各类消毒液——次氯酸、次氯酸钠、二氧化氯以及双链季铵盐等等。

何飞的群友蓝鲸,一位B站视频博主,也在家建了“半污染区”。这个北京小伙精准地指出,超市购物小票、塑料袋、雨伞等物品,也应正确处理或消毒。
过去三年间,蓝鲸收藏了264条防疫相关的视频。他发来其中一条,是另一个“山外有山”的钉子户,在玄关处,用白色塑料水管和三通转接口建了一个立方体,蒙上防尘隔离膜,内置脏衣篓,再配上空气净化器和紫外线灯——“有点像电影《生化危机》”。

群里还有个理工科女博士叫高高,每搬一次家,就自费为房东改造一次房屋:在中央空调出风口加静电过滤棉,换更严密的地漏和带U型弯的下水管道,并确保存水弯高低差5公分。
她自制过一台CR Box,一种四面搭载过滤网和顶部风扇的空气净化装置。这是两位美国环境工程专家发明的促进空气流通、净化的设备。购置元件她只花了200多元,低本高效。
外出时,高高会佩戴一种“神器”:一种能测量周边二氧化碳和pm2.5浓度的传感器。钉子户调侃它叫“电子罗盘”,可预测附近空气质量的“吉凶”。
至于终极防线——口罩,高高用的是“移动肺保”。这种口罩自带送风机,一根软管从口罩里伸出,连接着充电宝大小的净化器。为此,邻居小孩友好地称她,“外星人”。

去年12月底,众人皆阳时,高高也中招了。她的恢复期很漫长,2月连着3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一个晚上,她认真地准备次日会议的PPT。第二天上午,正拖地呢,接到电话:“师姐,你怎么还不来开会?”
——她全然忘了。
“整个人’傻’了。”高高说,她的记忆力、反应力出现了明显的退化。

像是潜到海下的一瞬间,安静得令人发指。她老公贴心地安慰:“欢迎来到普通人的世界。”
高高的人生是以“神童”叙事开始的。她复述了一件母亲总在复述的往事:在她两岁尚不识字时,有天倒拿一本书,几乎一字不差地念出来了——不是念,而是大人前两天给她读过那个故事,她记住了。
如果这个证据过于遥远,这位理工科博士还有一个“密不外传”的思维训练法:心算两位数乘以两位数。过去,她总是算得又快又准,可年初那几个月,她“完全算不出来”,或者,“我刚随口出的是哪个数来着?”
——若有幸参观部分钉子户的房间,会看到他们的桌子上摆着红红绿绿的保健品罐子,那里有复合维生素、辅酶q10和葡萄糖酸锌等。在他们描述中,这通常和免疫力的巩固紧密相关。
在将近4个月的调养后,一个普通的春日,高高闲来无事,随口算了一道乘法题。和计算器上的答案一对,全世界都明媚了。

前后反差扑面而来,高高夯实了防疫决心:“我要是再阳了,我这个博士就不用读了。” 在那以后,她的自我防护和社交隔离成为巨大的生活惯性,持续至今。她的态度很强硬:人不能等危险来了,才吆喝“安全第一”。
为此,第一次和博士生导师见面时,她大方表达:我会一直佩戴口罩。理由是,自己一阳的恢复期很长,不良反应比旁人强烈得多。
导师就此和她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老师和同学,秉持着“不理解,却尊重”的态度,接纳了这个“外星人”。
高高感到幸运。毕竟,她的一个钉子户群友抱怨过,领导让他“明天不要戴口罩来了”。还有的群友,虽拥有顶配的“面罩”,可日常通勤,只敢戴上平平无奇的N95。

刘小寒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KN95佩戴者——戴的还是国产杂牌。她小心翼翼拿医用胶带为口罩封了边,以使它完美贴紧皮肤。
她真心佩服那些无惧他人眼光的钉子户,勇于“焊”口罩在脸上。而她只在一百多人的大课时才戴KN95,其余时间则换成更为普通的外科口罩。
刘小寒在南方读大学,医药专业,月生活费1200元,有时接传单和家教补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是一个“半躺的钉子户”。
“半躺”的原因之一,是指她欲防还休,隔离并不彻底。经济条件不到别人一半,上不了好装备,勇气也只有别人的一半。
不同于高高式的“丑话说在前头”,刘小寒的防疫是“静水流深”的那种。
每次,她步入寝室大厅,会像电子扫描仪一样,先勘察周围有没有身体不适的人,然后,憋气,73步,58秒,钻进位于一楼的宿舍。就像一只人群里的“惊弓之鸟”。
她建了三四个小号,潜伏到大学城邻校的微信群里,打听“最近感冒的多吗”;
又在本校的“表白墙”匿名“开炮”:“生病了就别来自习室,不戴口罩你还咳嗽。”
“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挺好笑的。”刘小寒说道。她选了周六晚9点,在校园空无一人的小湖边接受电话采访。
她是一个关注健康的医学生。食品配料表上,但凡出现长长的添加剂名称,一概不吃。这位20岁出头的姑娘,幸运地从未经历过生离死别——“所以,就会更害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她也是凤凰网采访的7位防疫钉子户里,仅有的二阳者。这是她自视“半躺”的原因之二。她用“打击”这个词汇形容当时的感受。
那是今年5月又一波新冠来袭时,她班里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第二天,刘小寒找了个蹩脚的理由——最近压力大——搬出了宿舍。
刘小寒坦白,她是为了防疫才搬出来的。她和一位考研的学姐合租,住进两室一厅,每人月租500元。
他人即地狱,烦恼就此开始了:她想劝学姐注意防护,又担心人家就此拒绝合租,只好弱弱旁敲侧击,“学姐戴好口罩”,“学姐多注意身体”。还特意提过一嘴,如果你感冒、发烧一定告诉我。
前半个月,二人平安无事。某天,学姐有事返校,刘小寒递给她两个KN95口罩和两个薄薄的外科口罩,学姐只接过了后者。
刘小寒说她瞬间内心“警铃大作”,又只好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几天后的下午,她瞥见学姐在吃布洛芬。接着刘小寒测了抗原,她也阳了。
刘小寒当即质问,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病情?学姐的表情混进了一点“鄙夷”,说:“你不要太大惊小怪了。”
剩下的半个月,刘小寒在出租屋颓着,等待康复。她无法接受自己严防死守还是二阳的事实。
那首先是一种挫败感——“我为防疫投入了将近1000元”,就像是一个奋斗三年的学习标兵,高考那天睡过头了。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我向她表明了态度以后,她依然向我隐瞒”。
租约到期后,刘小寒搬回宿舍,删掉了学姐微信。

无论出于何种动力成为高处不胜寒的防疫钉子户,但人,终究是社会的人。
刘小寒常感到割裂,以前她喜欢KTV、酒吧、演唱会,如今的爱好主要是钓鱼。她自嘲变得“清心寡欲”。
和许多大学生一样,她渴望融入群体。她研究过重返宿舍几种隔离方案的可行性:
比如戴口罩睡觉。确实有校园钉子户这么做,暂不论其安全性,仅是操作起来就有极大风险——早晨起床口罩多是歪的,毫无用处。

另一种方法是建一座正压床——类似医用层流床,用塑料膜包裹整个床铺,再外置一个空气净化器,但这样麻烦且显眼。
碍于室友的姐妹情面,回到宿舍后,“半躺”的刘小寒不再采取任何防护。
而那些100%满格的钉子户们,从不吝啬拒绝。像高高就几乎推掉了95%的聚餐邀请。她亲自认证的“待客之所”,是一家带包厢的火锅店。少有的会餐里,她提前10分钟到,拎一台便携式空气净化器,将6人规格包厢的空气“翻新”一遍。
何飞也是如此。难得的老同学相见,他戴口罩,只聊天,不吃饭,多少像个异类。他经常善意提醒身边人注意防护,偶尔得到回怼:你又想封在宿舍里吗?
——疫情伊始,何飞正值高三,高考为此延期一个月。接下来大学生涯的前两年,不是停留在网课上,就是圈在校园里。
何飞自然理解那种渴望享受青春的心情。只是——他顿了顿,说:“没有人希望得病。但是在如何不得病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视频博主蓝鲸的答案则呈现了某种公共道德观。他认为,佩戴口罩,“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事情”,是选择一种更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与此同时,他希望淡化这种责任心的负累感——“防护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并不会有多不方便”。
唯有一次,何飞和身边人达成了高度共识。那是今年11月初,他和几位钉子户群友线下会面。餐前,他们重拾了疫情时代特有的“仪式”:
每个人测了一遍抗原,自证安全。

年轻母亲朱仪敏也难得出席了那次聚餐。从5月起,她几乎谢绝了所有聚餐和婚礼邀约,也再没去过电影院。
“我不是不想见,而是我愿意见安全的人。”朱仪敏说话时,总有种斩钉截铁的气质。
春天,朱仪敏一家去家族聚会,全染了流感。当她安抚怀里发烫的婴儿时,恨不得让整个地球跟着降温。她建议先生,下次家庭见面,先做抗原、戴口罩。
“那还是不要去见了,”朱先生对她说,“做这些措施,只会让家里的叽叽歪歪更多。”
朱仪敏有点无奈:“我不知道为什么戴口罩变成了这么棘手的事情。”
朱仪敏是辞掉互联网大厂工作后,全职带娃的。去年底,他们全家就阳过一次。儿子当时4个月,拉肚子、咳嗽,半夜高烧,最高时接近40℃。同样发烧的朱仪敏费了千辛万苦,从朋友那儿获得一瓶婴儿退烧药。
正是儿子哭闹又说不出难受时,朱仪敏坚定了做钉子户的决心——“这么小的孩子,他这样的痛苦谁来替他承担?”
在病毒肆虐的季节,她把一位宝妈的责任心发挥到极致:
她和先生亲自动手,为婴儿车安装了一台车载空气净化器;

她放弃社区医院免费的体检项目,转而去1800元3次儿童体检的私立诊所——那里的每间诊室都有一台空气净化器。
他们一家目前是租房,房子格局也是挑选再三:最适合防疫的独栋太贵,综合下来,她定下一个物业优秀的大平层,位于二层,方便走楼梯,还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在主卧,便于居家隔离。
——这个精心考量没有浪费,今年5月,朱仪敏请了一位育儿嫂。一上岗,阿姨先在主卧隔离,朱仪敏送饭菜到门口,监督测抗原。第三天,阿姨真的阳了。
但她先生的想法是——“病毒没那么可怕”,“我们感染的概率很小”,“同事朋友没有一个人这么做”。沟通的过程长久又耗人,在此只好概括为:争吵,争吵,讲理,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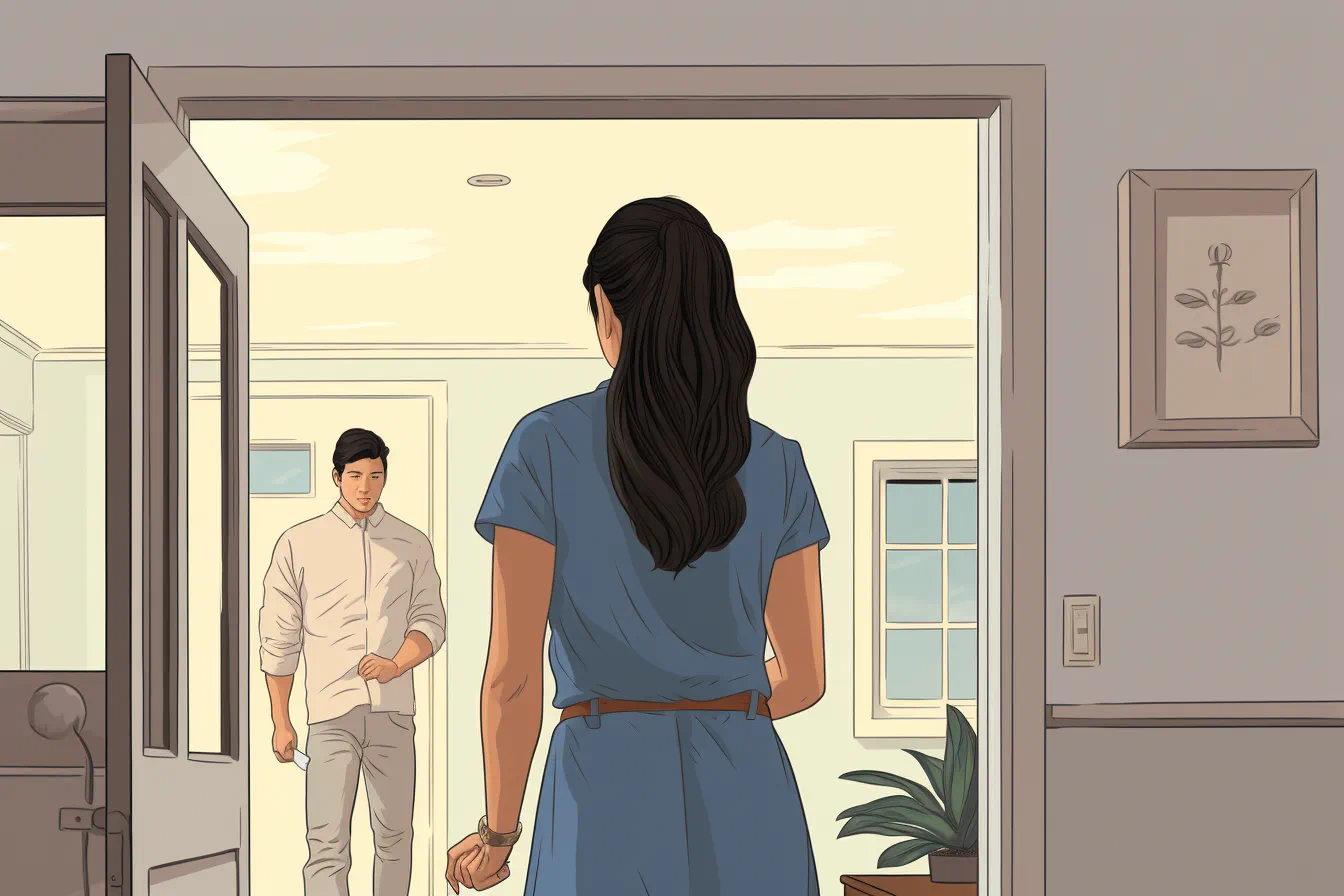
虽说朱先生没有100分地明白朱太太,好在,这对夫妻达成了平衡——她不限制他投身公共生活,条件是戴口罩,必要时去其他住所隔离。日子久了,她敏锐地觉察到,先生也自然地实践着钉子户的防疫理念。“我很感激了,他是我见过这种情况的家庭里,非常配合的了,都在互相理解。”
“在防疫群体里,非常多的家庭是一个想‘防’,一个不想‘防’。有的人都快要离婚了。”朱仪敏总结道,防疫手段没什么难的,“最难的是人心,是求同存异”。

尽管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可寻求共识,总是艰难。
刘小寒另辟蹊径。她深谙说服父母戴口罩的方法,不是晓之以理,而是适宜地“制造紧张”。于是时常反向科普,发去一堆充满惊叹号的文章如:《戴口罩!已叠加感染!》。
何飞的父亲是90年代的大学生,他不明白儿子的“执着”。暑假在家,何父外出工作不戴口罩,何飞躲进房间,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档。他故意买很多抗原,告诉勤俭的母亲:再不测就过期了。

河北人吴伯娴4岁的儿子至今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靠的是全家人的集体自觉。
去年12月起,她公婆带着孩子,像守卫城堡一样捍卫家中。孩子3个月没出门。
那段日子,吴伯娴和丈夫白天上班,下班后把菜放到家门口,再去别的住所过夜。地漏是封着的,马桶是盖着的,窗户只在清晨5、6点——别人家还没有醒的时候开一会儿。
今年9月,吴伯娴送儿子进了一所私立幼儿园。因为疫情,儿子愣是迟了一年才入学。
“该防还是得防,该过正常的生活还是得过。”吴伯娴好像想通了,语气里又满是无奈。
促使这位钉子户送儿子入“虎穴”的根本原因是,这孩子太孤单了。之前,每天下午5点,她儿子在楼下,乖乖地等着别的小朋友放学,一起玩耍一会儿。要是哪天人家孩子没来,小男孩一定很沮丧:“妈妈,今天真糟糕啊。”
这位小朋友天性乖巧,在电梯里遇到陌生长辈打招呼,不敢对视。虽说有性格成分,但吴伯娴心里清楚,这孩子缺少同龄人社交。她咬咬牙,“毕竟生活除了病毒,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然而,入园两个月,他已经高烧三次。过去的频率是一年一次。

吴伯娴不是没想过,给班里捐两台空气净化器。但上课要换教室,而园里的新风系统也只在空气糟透的时候才启动。
10月份她参加全园的亲子活动,目力所及,只有他们一家人戴口罩。
她询问老师,班里有没有发烧的孩子,老师会说,没有。可传来的视频里,入冬后上课的孩子日渐减少——据国家卫健委消息,近期呼吸道疾病已经进入高发期。此外,多地相继发文,要求教师、学生不带病上班、上课。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戴上了口罩。
上幼儿园、当钉子户,像是二选一的人生难题。这位坚持佩戴N95,被同事说“好久没见过你的面容”的母亲感觉这道题很残酷。
回到年初躲在家的三个月。有天,吴伯娴的儿子坐在飘窗往楼下看,忽然说:“妈妈,那个人不戴口罩,他肯定阳过了。”
自这孩子懂事起,口罩就像一件衣服,穿在脸上。他和他的同龄人,在一场盛大的全球性瘟疫中开始了漫长人生。许多事情,家长也没有刻意教过,却自然地生长出来——比如,他今年第一次出远门,一下车,就捂住了口鼻。
在他小小的身体记忆中,疫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他所看到的世界变成了二元对立:阴和阳,洁净和危险,戴口罩和不戴口罩的。他不曾呼吸过那个笼罩着昂扬、乐观气息的疫情前的空气。

刘小寒偶然想起在KTV唱J-pop的时刻,诚实地说,“自己是孤独的那一类”;
高高倒是通透,“又不得病,又可以继续上班上学”,挺好;
“我也想回到之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我没有办法,”何飞说,“错的是病毒。”
11月初,幼儿园陆续有孩子生病,吴伯娴的儿子又没躲过去,咳嗽、呕吐、高烧。
她终于憋不住了,一口气跟老师请了四个月的假——春节后再见吧。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