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之后,他遭遇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到北京领奖。他给当记者的弟弟王天乐打电话说,去北京的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自己的获奖作品送人,钱仍然不够,希望弟弟再帮他想一下办法。临近领奖日期,王天乐终于借到了钱,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王天乐愤愤地对路遥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回了一句“×他妈的文学”,头也不回进了火车站。这是路遥生前名声如日中天的时期,但他留给亲朋的印象,依旧是一生穷和一身病。一年多后,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去世,年仅42岁。但在他有限的苦难的生命里,却因为创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小说,而成为亿万青年的“人生导师”。阿里巴巴创始人不止一次说过:“是路遥的作品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100位改革先锋获得国家表彰致敬,路遥名列其中,是仅有的两名上榜的作家之一。▲路遥(1949.12.2-1992.11.17)。图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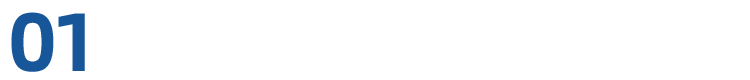
路遥生于1949年底,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原名王卫国,带有浓浓的时代色彩。他出生在陕北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家里十来口人,只有一条被子。好友贾平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陕北高寒贫瘠,使他有着不堪的童年和少年。我去过他的故居,看着那低矮阴暗几乎要崩坍的窑洞,使我悲切难受,回望几十年后村前屋后仍是光秃秃的山坡,使我能想象当年这里人的生活。”7岁的时候,这个贫困重压下的家庭,把路遥过继给伯父。当时,路遥的亲生父亲带着他,一路讨饭,从老家榆林的清涧县乡下,乞讨到延安的延川县,走了上百公里路。一路上,父亲始终没有告诉他真相,只是说带他到伯父家去玩两天。某天清晨,父亲唤醒儿子,跟他说要去赶集。敏感的路遥知道父亲要悄悄溜走,于是躲在一棵老树背后,看着父亲踏着晨雾,溜出村子,上了公路,眼泪唰唰流下来。伯父家同样一贫如洗。上小学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走到别人面前。有同学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因为贫穷,伯父不让路遥读中学,只想把他当劳动力。路遥偷偷跑去参加考试,竟然考上当地最好的中学——延川中学。开学时,路遥把砍柴刀往山沟里一扔,一个人跑到县城上学了。随后三年,无法自带干粮的他,硬是凭借同学们的接济,把中学读了下来。穷困,在他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段早年经历,也决定了他后来小说中主人公的出身,无一不是带着命定的苦难。有研究者认为,路遥一生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转换为非农身份,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里奋斗。日后脱离农村户口的路遥,成为城市人。他爱喝咖啡,爱抽好烟,但即便成名了,成为大作家,日子还是一片潦倒。1984年,作家张贤亮认识当时红遍文坛的路遥,去他家里坐过。张贤亮的印象,路遥的家简单得近乎简陋,感觉蒙着一层乌蒙蒙的气息。出来后,他对同行的人说:“你们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那个年代,穷苦出身的文学青年都想靠一支笔改变身份,改变命运。而屡获全国文学大奖的路遥,最终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农民”。成名后的路遥说,写小说并不比种地的农民高贵,“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他有句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践行到底。他的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大概为他带来3万元稿费。但这3万元在这部书出版前已经预支得差不多了:家里的开支,供养养父母、亲父母,自己用于抽烟……1989年,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电视改编权给了中央电视台。剧组专门到西安跟他见面,递给他一个信封,说是著作权报酬。难怪路遥常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不仅拖垮身体,而且难以为继。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张晓光求助。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
路遥黯然伸出五个手指:“5000吧!这是我第一次卖自己的名字给别人……”那是路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卖自己的名字。因为文章刚发表,他就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爬起来。路遥死后,留下1万多元的债务。他的弟弟王天乐说,路遥就是个“悲剧人物”。▲路遥烟瘾很大,他说是为了激发灵感。图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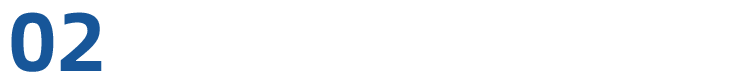
一辈子与穷困的斗争,并未让路遥在物质生活上有多大的改善。因为绝大多数时候,他的拼命,压根不是为了钱。1973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陕西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1978年到1980年,陕西籍作家莫伸、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都已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想而知,好强的路遥那时候没获奖心里有多憋屈。”《路遥传》作者厚夫曾说道。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路遥一直有一股不甘人后、只争第一的干劲。此时,路遥完成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投稿却连连遭遇退稿。绝望之余,他甚至要把这稿子烧了。烧掉之前,他最后一次把稿子寄出去,寄给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学杂志《当代》。如果再退回来一定烧掉,彻底忘掉这件事。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主编的秦兆阳,看到《惊心动魄的一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篇小说不仅没被烧掉,还在1980年秋季发表了,获奖了,连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当代》年度文学荣誉奖。路遥成了陕西第一个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作家,同时跻身全国知名作家行列。这对路遥的影响很大。他曾说过:“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有了这次成功与肯定,他才有勇气投入另一篇影响全国的小说《人生》的创作。1981年夏天,路遥背起简单行囊,在甘泉县招待所住下,开始21个昼夜的疯狂写作。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
就是这样一种在别人看来苦哈哈的状态,路遥却甘之如饴。他始终认为,写作《人生》的21天,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1982年,13万字的《人生》公开发表。这部描写农村知青在改革时期命运的小说,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主人公高加林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经典的形象之一。小说发表后,路遥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无数读者来信,许多人向他请教人生问题。路遥的朋友陈幼民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广播里播放小说《人生》,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一段完了,旅客们还不尽兴,有看过小说的,向别人介绍情节的发展,更多的,是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进行讨论。陈忠实说他读了《人生》之后,一下子从自信中跌入了自卑,“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很多作家,在一炮而红之后,毕生躺在上面收割荣誉和地位。如果是现在,他们还要收割流量和现金。但对路遥来说,越是成功,他越不肯轻饶自己,“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在后来的回忆中,路遥说,“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他的目标,是创作出“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他渴望去挑战这份“本属巨人完成的工作”。他说: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 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忘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1985年,路遥(右二)与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籍作家合影。图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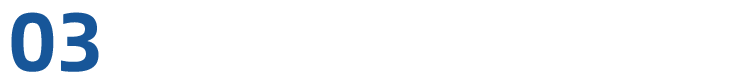
32岁的路遥依然坚信,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在苦难中铆劲,其实不算太难,因为你别无出路。但在成功中抽身,远离闪光灯,远离鲜花和红地毯,很难很难,因为你面临诱惑。他的设定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最初还分别给这三部曲取名为《黄土》《黑金》《大城市》。他决定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1975年初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奋斗、情感与梦想。光准备工作就耗费了3年时间。3年间,他潜心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他还专门找来十年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省报、地区报的合订本,逐月逐日仔细翻阅,甚至磨破了手指,只能用手掌翻动纸张。然后,就是体验生活。为了书中人物写作的真实性,他到铜川鸭口煤矿、陈家山煤矿,和矿工同吃同住,一遍一遍地下井,而且要下到很深、很潮湿的地方去体验生活。准备工作做完,真正的小说一字未写,人已经折腾得半死不活。路遥的小说经常获奖,很多人会以为他过的是一种潇洒的写作生活。只有他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片巨大的沼泽,他要一个人跋涉而过,想想都不寒而栗。一些作家自带天才或鬼才基因,即便如此,创作对他们来说,也是脱一层皮或两层皮的问题。而路遥资质平平,全靠努力和勤奋获得极高的文学成就,他的写作,直接就是脱三五层皮,甚至要命的问题。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但接下来的遭遇,几乎比艰难的写作本身更致命。蛰伏几年后,路遥发现中国文坛的风向变了。整个中国,哪怕是偏远山区的文学青年,都热衷于西方各种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被评论界贴上“陈旧”的标签。因此,哪怕是早已名满天下的路遥,拿出他最有分量的作品,仍旧接连遭到了两家出版单位的无情退稿。最后,才由远在广州的《花城》杂志刊发。《平凡的世界》一开场就奠定了悲剧性的命运基调。很多评论家对路遥说,《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贾平凹回忆,《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路遥对他说:“狗×的,都不懂文学!”有段时间,路遥郁闷到顶点,经常对弟弟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大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声大哭。柳青,陕西人,现实主义巨著《创业史》作者,1978年病逝。路遥受柳青影响巨大,终生奉其为文学教父。▲路遥在柳青墓前。图源:网络
路遥后来不无伤感地谈到,面对文学思潮冲击时,内心那种孤军奋战的悲凉: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责难,我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
最终,他“战胜自己”,决定不为一时的文学思潮所动,坚持用“老气过时”的创作手法,继续书写《平凡的世界》第二、第三部。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1987年夏天,《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时,路遥开始大口吐血。他的弟弟王天乐后来说:“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十分可怕。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苦行僧式的写作方式,让路遥的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被扯断。他自己描述说: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着了。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他才三七八岁,正当生命的“中午”,但他不止一次想到了生命的终点。他隐瞒病情,和时间赛跑,赶在1988年初夏,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也就是全书的写作。为全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后,他把手中的圆珠笔掷出窗外。几年来,第一次认真在镜子看了看自己,皱纹交错,两鬓苍白,憔悴不堪。在那一刻,他记起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平凡的世界》后来被拍成电视剧。图源:影视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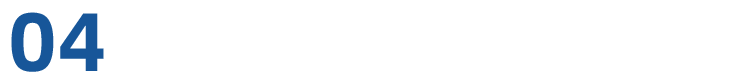
路遥明白自己在疾病、死亡与完成《平凡的世界》之间,他选择了什么。但是,作品完成之后,它的命运走向,他无法控制。意料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二、第三部的发表不容乐观。其中,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第三部也只是在更为边缘的文学杂志上刊发。完成《平凡的世界》后,路遥给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的蔡葵写信,再次表明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与此同时,这部在评论界饱受冷遇的作品,在流行传播领域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88年3月27日起,《平凡的世界》全书还未写完之时,这部书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126天的播出。小说一下子征服了听众,直接受众达3亿人之多,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听众来信居19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贾平凹说,《平凡的世界》是他用生命写成的,“用生命写作”这句话,路遥是最配得上的。随后,《平凡的世界》不仅三部都出版了,还改编成了电视剧。“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路遥向贾平凹说。“他们”指的是那些被文学思潮牵着鼻子走的作家、编辑和评论家。这无疑是路遥一生中最解气的时刻,但他同时也陷入了穷与病的深渊。“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他留下的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长期以来都是为数不多的畅销书和常销书,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亿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无数成功人士都说自己受过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的影响与鼓舞。一些评论家调整了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另一些评论家固执己见。当初瞧不上路遥的那些个作家、编辑和评论家如今在哪里,而《平凡的世界》已成永恒流动的“江河”。如他所说,生命从苦难开始,只有在苦难中诞生灵魂的歌声。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文献:
路遥:《路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陈泽顺:《路遥的生平与创作》,《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陈幼民:《忆路遥》,《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