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房君睿,是一个普通上海青年,
他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复,
但大专毕业,
找不到相关工作,
30多岁了,没有稳定的工作,
也没有女朋友,
和父母挤在市中心30平米左右的老公房,
有时候连起床的动力都没有。
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导演秦潇越原本设想,
但房君睿却说:
“你永远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故事。”
断断续续拍摄近5年,
秦潇越也陷入了对自己的质疑。
她慢慢发现,
这不仅仅是“个人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让更多人看到了理想的背面。
工作难找,房价太高,婚恋困难……
年轻人的失落与无奈,
在这部片子里一一展现。
自述:秦潇越
编辑:张雅兰
责编:倪楚娇


我是带着“拍摄一个励志故事”的想法去到房君睿家里的。他是我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的观众,放映结束后他过来跟我谈理想。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复。那时候是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很火,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个想要在上海修文物的青年,他可能碰到了哪些困难。

家里空间很小,处处塞满了房君睿买来的书
第一次去他家里,我就印象深刻。他的原话是,我们家虽然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在上海市中心,在静安寺那边有一套房子。房子是狭长的,非常昏暗。目光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橱柜里……一摞一摞地放着,基本都是精装书或者外版书,其中有宗教、历史、哲学、艺术……像他爸爸说的,“都比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厉害了”,家里甚至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这样一个精神世界,落脚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反差。

工作中的房君睿
大专时,因为兴趣选择了文物修复专业。毕业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需要高学历,有强大资金支持才能做的行业。他爸爸为了支持他,帮他付了高昂的学费,给他报了一个关于文物修复的大师班,他断断续续上着,也持续在修一只碗,但一直没修好。为了有事干,房君睿尝试过很多工作,在派出所做特保、做房产登记、技术工人等等,很多工作没有通过试用期,我拍摄的时候他正在医院做保安。他还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结婚生子,过普通人的生活。找一个相貌端正,不太在意钱的女孩,但是苦于收入和房子的问题,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房君睿把恋爱和婚姻当成一种“救赎”, 但她妈妈告诉他,这世上是没有救世主的。他还稍微有点口吃,说话紧张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有种想说说不出的感觉。不过他也很聪明,思辨能力很强。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有很强的内在张力。

房君睿常常没有起床的动力,躺在床上发呆
我当时拍到的很多画面都是静态的,小小的地球仪放在窗台上,房君睿在午睡,他爸爸就看着无声的电视,里面放着国际新闻。然后窗帘是那种透光的,光从外面射进来,照在很昏暗的屋子里面。他们家那只猫,像是一只上帝之眼,注视着屋子里面正在发生的争执。每一次房君睿心里有委屈的时候,只有猫在他手边蹭着他,或者走到他的脚周边,这些小细节我觉得会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准确来讲,片子都不算是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没有我们传统印象中那么多起承转合,就是在呈现人处于困境的一种状态。
某种程度来说,房君睿的困境既来源于他的内心,也来源于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和认知差异。基本上每天都有快递上门,是他买的书,我们也拍到过好几次。他爸爸不理解,家里空间本来就不大,书占据了太多空间。房君睿也觉得委屈,他觉得自己没有无所事事,他在看书,在研究历史。父亲只觉得他不务正业,吃饭的问题还没解决,还要搞研究,这些就是空谈。我就在争吵的现场,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真的会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

房君睿母亲负责照料一家三口的日常起居
房君睿的父亲在家里,经常用指责和负面的语气和他说话。但是在外面,有人说他儿子“心态不好是因为没有受过挫折”,他又会站出来维护儿子,说现在工作找不到就是受挫。他妈妈很维护儿子,每次他父亲指责房君睿,妈妈就会立刻过来说:“你不要再说他了,这么多年了,说了也没用。”房君睿想要做出改变,辞掉了保安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这个年纪做保安,没有哪个女孩子能看得上他。所以想去做空气检测,这是个新行业。他妈妈就会担心:“空气检测是不是要一直站着,会很辛苦。”他爸爸就说:“你这人好奇怪,一边担心他吃不了苦,现在又怕他吃苦。”但这份工作,对方可能嫌他动作慢,他就又被辞退了。

房君睿父亲经常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国际新闻
他爸爸一直很喜欢画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办法做相关的工作,而是在澡堂当服务员。后来改革开放,人才流动了,他才去了医院里做美工,就是出黑板报,也是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一直等到40岁分配到了房子,他才开始考虑结婚生子。房君睿爸爸的观念就是,没有条件,没有房子的话,还谈什么朋友?结什么婚?但房君睿觉得,有房子住,可以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实现的基本需求。“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结婚吗?”所以他对现实有很多抱怨和不满,不像父母那一代可以坦然地接受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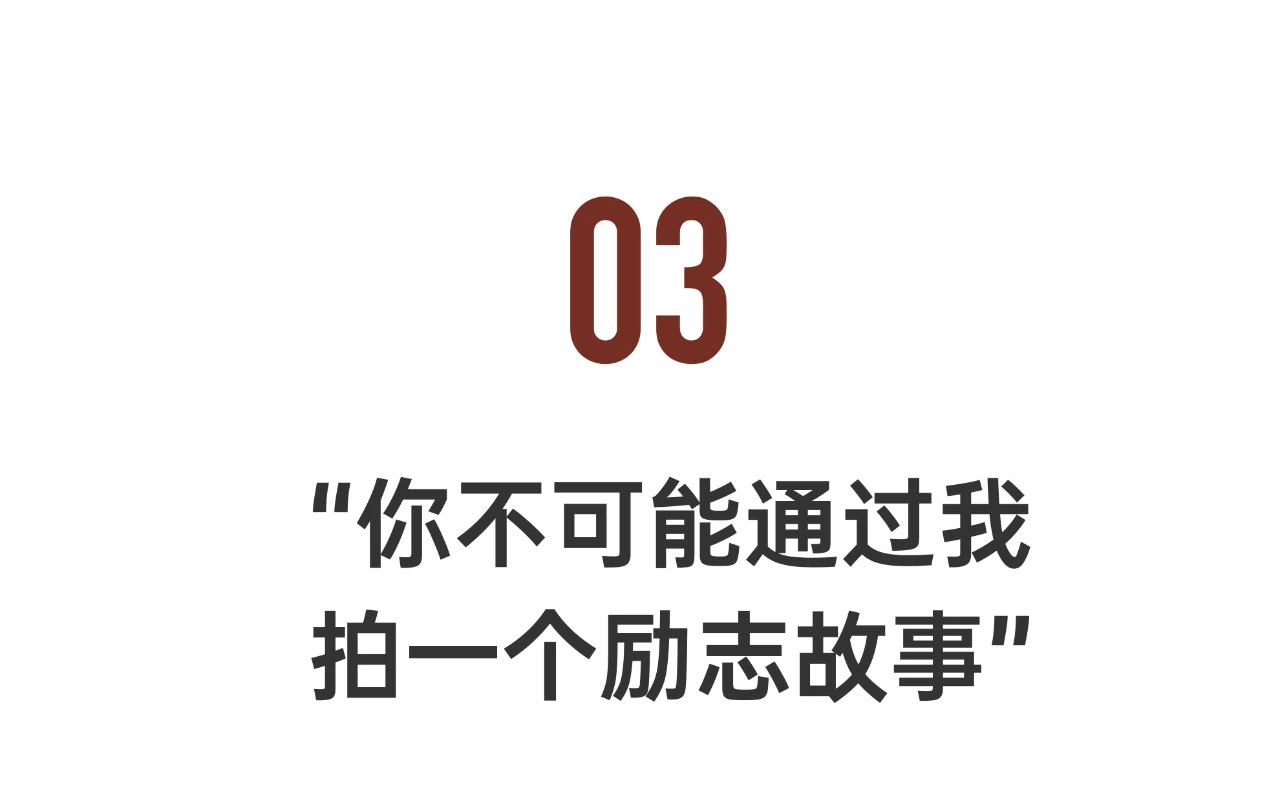
▲
房君睿有一个叫杨光的朋友,也经常上门来找他。因为房君睿很喜欢研究宗教和历史,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为了让房君睿走出来,杨光就鼓励他办一个自己的展览,可以讲一讲宗教的历史。通过这件事来建立信心。
但是房君睿根本没有经验,他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事实上,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策划一个展览。所以写文章、找场地,做策划的时候会拖延。其实就是担心自己做不好,怕自己努力了也没有结果。
确实,当时去看展的人也非常少。其实大家都很善良,希望能给房君睿一点积极鼓励。最后那个展览变成了一个大家分享明信片的活动,草草了事,好像也就是满足了一下大家帮助他的心愿。▲
导演秦潇越正在拍摄中(右一)
在拍摄半年之后,我也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因为当时看到的一切和我心里想拍的完全不一样。
前半年,拍到的几乎都是父子间的争吵,摄影机的介入,让他们俩有了更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个人物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没有突破。我也不知道还能拍什么。
房君睿上的“大师班”里,有一只碗要修。他爸爸有一次说,你要是真的热爱这件事,你早就把碗修好了。
我觉得这个碗就是他埋在心底的那个理想的外化,他不去修碗,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算碗修好了又怎么样呢,就真的能够找到和文物修复相关的工作吗?▲
后来我就跟房君睿说,要不等到下次他把碗修好了再来拍他。他立刻察觉到了我的意图,回我说:“你永远都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故事的。”
我当时被震慑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结结巴巴地说: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拍一个励志故事。只是觉得,即便是一个陌生人,也都是希望你的生活往好的方向发展。
作为导演,会经常有个“上帝视角”,好像对故事的走向有一个判断,到最后你发现,这些是根本不受你控制的。
我的情绪,也受到了拍摄的影响。最差的时候,晚上也会做噩梦,梦到房君睿轻生。
做后期的时候,反复看的也是家庭矛盾、争吵的画面。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拍这么一个片子。那段时间,我和父母也起了些矛盾,我妈妈说,你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变成房君睿的。▲
我是从2012年12月21日,所谓的“世界末日”这天开始拍片子的。
“年轻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期待”,这个主题我很喜欢。于是当时我一个人坐火车环游中国,记录了沿途陌生人的生活理想,制成了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人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最后发现,一个个体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个人,也在于家庭,也在于社会。
房君睿根本就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大部分人都不是。所以人们才常常期待一个大英雄。▲
但就此放弃,仿佛是在打自己的脸,我就继续拍,一下拍了近5年。
后来我在想,他至少可以被外界看到。当一个人深陷痛苦,你就不要再去试图找到某种正能量。展现痛苦,就是在给他一个拥抱。
在First电影节映后交流,很多人觉得房君睿能够在镜头前展示自己,是很勇敢的。其实每个人眼中的房君睿可能都不一样。

▲
今年7月的First电影节,秦潇越在电影映后和观众交流
这部片子还有一个特点,像宏大的城市变迁这样的话题,都是通过非常日常的对话和家庭内部的争执表现出来了。
房君睿的父母双方,他们的祖辈刚来上海的时候,也是很普通的。房君睿爸爸的祖辈是从苏北过来的,妈妈那边是广东过来的。
房君睿爸爸的四祖父年轻时一直跟外国人做生意,家里条件很好。房君睿爸爸的爷爷,那个时候购置了很多黄包车,按现在来说,就是开了一个出租车公司,所以都过得不错。
然后日本人攻打到了上海,整个时局都不好了,慢慢地,他们整个家族就彻底没落了。
后来,有很多新鲜的血液注入了进来,新上海人成了中流砥柱。
拍摄到后期的时候,两个老人考虑到房君睿以后可能要结婚的问题,他们又在上海嘉定买了一套经适房,房子坐落在城市边缘的地带。有种他们要被这个城市抛弃了一样的感觉。
▲
我在想,假如我和房君睿是同样的出生背景,家庭环境,这样成长起来,那我可能就是一个房君睿。
世界就是“所有我的合集”,全世界这么多人会不会都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不同可能。人都是差不多的,我们都没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或者轻易地做出某一种评价。
我前两天看到豆瓣上有一个观众写的评论,他说这可能不是那种大家期待的励志故事,但他看完之后,觉得要更加尊重时间的流逝,重视每一刻的意义,更好地成为自己。我看了之后好感动,觉得被理解了。
因为这个片子刚刚拿了First的最佳纪录片奖,可能有更多的人会看到他,甚至“房君睿”可能会变成一个标签化的认知。我还没有跟他接触,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消化得怎么样。
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准确总结出房君睿的困境形成原因,或许这不仅关于人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关于“人要如何存在”的哲学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