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真,接下来要聊的第一本书《莫扎特的女人们》实在算不得很新;11年前的出版物,放在这个喜新厌旧的时代,基本可以看做是古籍。那一年是沃尔夫冈·阿马杜斯·莫扎特的250年诞辰纪念,应景的出版物不计其数,可至今还能看的就有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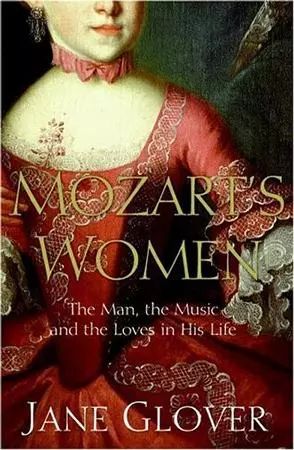
首先,由女性视角切入经典话题,这一点至今没有过时。作者的叙事技巧加上专业成就,也保证读者能从书中获益。至少不像我们这边一些知识贩子,专拿情怀、艺术感觉这类屁话蒙事儿。最近看见北京一个素有雅誉的作家,大谈瓜涅利提琴音色如何含蓄,斯特拉迪瓦利如何浮嚣。好吧。不过就笔者听说,昔年帕格尼尼常用的随身家伙就是一把瓜涅利,单凭“大炮”(Il Cannone)的绰号,您就知道音质绝非内敛一路。真想问问这类乐评人,小提琴的四根弦是哪些音,钢琴上的哪个键是中央C。
“莫扎特的女人”这个题目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所指非和他睡过的女人。作者的用意是,通过回顾不同的女人的影响,检讨音乐家的人生和写作。所以有个副标题:“他的家庭、朋友和音乐”。所以,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关于成长,以及与成长相关的语境。在莫扎特的母语当中,成长(Buildung)这个词还有塑造、教育的这层意思。
想起这本书,是因为不久前一天晚上,老爹心血来潮,拖笔者陪着看一部80年代老片,叫《上帝的宠儿》(Amadeus)。这个充满poetic license的音乐传记片,讲的是莫扎特的音乐家同行萨利耶里出于职业嫉妒,将天才传主设计设计害死。故事源出自普希金的诗剧,后来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谱成歌剧。浪漫派人物常有的文艺男心态,就是平庸之辈总要害朕。


《上帝的宠儿》剧照
做为音乐家,萨利耶里的成就自不能和莫扎特相提并论,可也到不了天壤之别那个程度。那个时代名家辈出,凯鲁比尼、霍夫迈斯特、克莱门蒂、科隆默,你能数出一个野战排,历史记忆的配额留给谁,删除谁,并非没有偶然因素,而公众又都喜欢三大、十佳之类的排名游戏。所以不仅是活人,死人也一样要靠运气来混。伟大的老巴赫就是一例。其实萨老师是个热心肠,不但利用职权人脉帮过莫扎特,还因为后者早逝,继续提携故人的儿子。称他为乐坛伯乐也不为过,贝多芬、舒伯特都曾受教于他。
影片中重彩深描的部分,是莫扎特的肛门期人格,并暗示其形成,或因乃父的长期干预。这是一个非常“中欧”的话题,很容易让观众联想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有卡夫卡那种俄狄浦斯式的乖张想象。考虑到导演福尔曼的捷克原籍,这样的处理倒也不难理解。
严父之外还有慈母,这是多数研究者着墨较少的一个话题。《莫扎特的女人们》的贡献,或许就在于提供了一个来自女性的叙事角度。作者珍妮·格罗弗是英国指挥家,她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合作的《魔笛》很有影响(虽说由《狮子王》闻名的茱莉·西摩尔的舞台导演,略嫌喧宾夺主),因而在分析莫扎特的歌剧人物方面,尤其另具心得。
做为莫扎特一生最后完成的大型作品,书中对此于该剧着墨甚多。其中的诸多史实掌故,爱好古典音乐的读者并不陌生,然而作者格罗弗的剧场经历,让她在选角方面别有洞见。在《魔笛》大获成功的首演中,女一号夜女王由约瑟珐·韦伯担纲。这个技术上极为吃重的角色,很可能就是为她量身定制。此前不久的《点金石》一剧未设花腔女高音角色,就因为她在休产假。而夜女王一角也将由她在维也纳舞台上垄断十年之久。
约瑟珐是韦伯家的老大。因为生长于音乐之家,她们一家四个姐妹全部接受过声乐训练。其中她和老二艾洛霞后来成了歌场名旦。这个家族最有名的人物是她们的堂弟,《自由射手》的作者卡尔·玛利亚·冯·韦伯。莫扎特第一次结识这家人,是1777年在曼海姆。那年他21岁,刚刚辞掉萨尔茨堡的工作,跑出来另谋机会。
这一家的二女儿艾洛霞,一位极具天赋的女高音,让他堕入情网,并一度成了他的缪斯。然而俩人有缘无分,分别几个月后,他们曾在慕尼黑重逢,但已如同路人。最后嫁给他为妻的,是老三康丝丹瑟。这不是莫扎特第一次跨国远游。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只有母亲随行,而他那位一向监控甚严的父亲,因为请不下假,只好老实呆在萨尔茨堡,在大主教府里当差。一同留在家里的,还有姐姐南内尔。
此行的终点是巴黎。然而那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并没有他的位置。他曾在一封家信中说,凡尔赛有可能雇佣他做管风琴师,但他没有兴趣。这种带有自我推销性质的出行成本高昂,如果不能达成目的,最后收获的就是债务。雪上加霜的是,母亲此时突然病倒,最后客死异乡(葬于大市场附近的圣厄丝塔什教堂,与路易十四的财务大臣科尔贝、音乐家拉莫等大人物为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落单。
莫扎特的母亲是个从小吃过苦的人,后来嫁给萨尔茨堡这样一座富裕城市的宫廷音乐家,算是不错的婚事。她性格乐观,喜欢各种平民阶级的无厘头笑料,这一点和她功利心极强的丈夫恰成反比。父母双方,一边代来严苛的专业训练和进取心,另一方则以慈爱和幽默加以中和。装逼、逗逼两相对冲,真气逆行,但也成就了他的绝世之作——《魔笛》正是这种丰富性的标本——就像海洋深处的寒、暖流交汇之处,往往孕育出最为丰饶的生态。
这些我们已知的内容,《莫扎特的女人们》是以那个行将离世的母亲的视角,来呈现的。她和丈夫列奥波德有过七个孩子,但只有我们熟知的一儿一女存活到成年。他们都是音乐神童。神童(Wunderkind)是个德语词,十八世纪开始流行,折射出启蒙主义对于人,以及人的潜力的想象。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也是文化教育惠及平民阶级的产物。
身为两个神童的父亲,列奥波德·莫扎特自会善加利用这一天赐资源。一次次合家远行,就是两个孩子的推销活动。在旁观者眼里,他们和杂耍卖艺的没什么区别,除了目标受众不是社会大众,而是宫廷里的贵族。这个萨尔茨堡大主教府的乐师,能被恩准请下这么多长假(最长一次旅行长达三年),也是甲方认为自己治下出了这等奇才,拉到各地嘚瑟一下,不失为一种公关宣传——为了本地、本座,还有主的荣光。
莫家的旅行路线就像曾经流行的西欧几国游,主要的停留地点都是维也纳、乌特莱赫特、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米兰、罗马、威尼斯,这些财力足以赞助音乐生活的中心城市。当时非但没有ICE、TGV、Frecciarosso等各国高铁,就连冒黑烟的蒸汽机车还没出现呢。坐着马车在土路上颠簸,疲劳病痛如影随形,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照料他们的重责,自然落在母亲肩上。
比起一般贫苦人家,维持这样一份生活,已算是大幸。操劳辛苦的同时,也能带来收获。总算识文断字的人,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本身,也是极好的。何况还能接触到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小莫扎特六岁那年,在维也纳受到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召见,表演盲奏——在用布遮住键盘的羽管键琴上弹奏。在场的皇亲显贵,还有同龄的玛丽亚·安东内塔公主,就是后来路易十六的断头王后玛丽·安东瓦奈特(嫁到法国,名字就得按法语拼读)。


音乐家《Mozart!》剧照
这其中的原委,无非就是她的老公和孩子有一种本事,知道怎么弄出听着舒坦的声音来。这也是一份娇贵的财富,需要强有力者的庇护。而寻找庇护本身,又要经过颠沛流离的一番折腾,听着非常讽刺。其高昂成本的回报,也就是爵爷们的一点打赏。
在肉食者眼里,这些表演相当于茶歇饭后看耍猴,图个乐儿,关于莫氏姐弟少报的年龄,他们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至于谋求职位,那是没戏。当时哪个大国不在打仗?谁家宫廷的纸醉金迷,不靠债务铺垫?在凡尔赛,莫家恭候多日,终于获准觐见路易十五,却遭到国王宠姬蓬巴杜夫人的冷遇。这只寻常巷陌飞出的凤凰,面对同样想登高枝儿的同类,眼光立刻开了刃似的。
然而各路真假神童的爹妈们,哪一个不是打破脑袋往窄门里面挤?这一点不论古今中外。曾在施坦威钢琴厂赞助的活动上,听见该公司一位高管讲,中国有六百万学童在上钢琴课。这个市场确实诱人,可对于那些小孩,已然繁重的课业之外,每天还要练琴不少于两小时,而且六百万人当中,未来就业涉及音乐的——演奏、创作、教育、学术研究、评论全算上——乐观估计也到不了六千吧。
拜托别提修养那俩字。所谓修养,往往就是挑剔,势利,眼高手低,口袋里没俩蹦子儿,还老觉着高人一等。拙见以为小孩成长先要内外兼修,一能打斗,二会打扮。再就是数学、母语、国际通用语,三类基本语言。至于才艺,您觉着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能降低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可替代性?为人父母者,先得把养儿育女看成自我再造,包括要求自己的信息和流行观点,更多来自《经济学人》,而不是《罗辑思维》。
笔者早年学琴,是因为那会儿的大学全都关了门,要想逃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命运,就得考个文工团什么的,才能留在城里。除了个人资质,机会因素,还免不了要走后门。好在后来保送到体校,不用再受那份洋罪,除了偶尔给文艺女孩弹弹伴奏,最后礼也崩了,乐也坏了。琴者,禁也?别逗我咳嗽。琴者,淫也!省下陪姑娘们鬼混的功夫,编程都学会了。
莫扎特这种出身平民的神童,一旦变声并长出胡子,就要龟缩回到草根阶级所属的角落,一切按既定规则处置。他们见识过一个浮华世界,却又无缘融入,偶尔也会蹬鼻子上脸,不把自己当外人看。他们知道在一个宗法社会里,混不成人上人就根本不是人。世间总有天赋异禀,野心勃勃的第三等级子弟,不论伏尔泰、卢梭还是莫扎特,对这套游戏规则提出或是激烈或是温和的异议。
然而对于每个人,柴米油盐的破日子还得接着过。莫扎特最后娶到韦伯家的三小姐为妻。这位新太太显然不是家政方面的好手,但用格罗弗的话说,“她可以满足作曲家多方面的身体需要”。婚事肯定不算体面,韦、莫两家闹得鸡飞狗跳,丈母娘那边要报警拿人,老列奥波德·莫扎特也是终生为此不快。
上一辈人老脑筋,觉着儿子得谋一个体制内的位子,去贵族家当差,虽然老莫扎特自己,当年也曾离家出走,从奥格斯堡跑到萨尔茨堡,最后混到教堂音乐副总监的位置。那个年代,从海顿兄弟到巴赫的几个音乐家儿子,包括老莫本人,一个成功音乐教育家,哪个不是穿了多年外省宫廷的号衣?
他的天才儿子是这一行业最早的现代人。他的世界是都市,那里正在出现新型公共空间,各种思潮在那里交汇辩诘,催生出新的变异体。也是在这个音乐的首都,他沦为一个自由职业者,靠写作,教学养家糊口。这个广大的市场同时赋予他某些自由,允许他超越贵族恩主们的过时口味,发展新的表达方式。
在维也纳还有他的两位妻姐,以及阿德莲娜·菲拉雷塞·德尔·贝内、安娜·哥特里布、卡特里娜·卡瓦利埃莉、南希·斯托雷斯,这些才艺高超的女歌者。她们不仅是《唐璜》、《后宫诱逃》、《女人皆如此》、《费加罗婚礼》、《魔笛》,这些歌剧女主角的最初阐释者,也是莫扎特理解女性,并塑造这些角色的现实参照。
不论多少坎坷,莫扎特终究能搏出位。而他的童年搭档,同样有神童之誉的姐姐南内尔,却只好留在萨尔茨堡陪伴鳏居的老父,直到三十多岁,才嫁给一个带着五个孩子的丧妻公务员。她也目睹过美泉宫、凡尔赛的排场,但此时,当弟弟在帝都声誉日隆,一切都像与她无干。为了这个弟弟,父亲不但牺牲了她,甚至牺牲了自己。
老莫扎特流行至今的作品,只剩下那首《玩具交响曲》。那是他所属的时代的典型产物,贯穿始终的嬉游气息(divertimento),比起小莫扎特辉煌昂亢,辟示未来的《朱庇特》,不过是贵族庭园游艺的背景音响。文化思想上不能与时俱进,对儿子的说服力便丧失大半。而那个时代专有的戏虐(Scherzo)精神,却将被儿子发扬光大,并以狂欢方式变本加厉。
不管怎样吐槽萨尔茨堡闭塞的外省气,莫扎特终其一生,始终都是这座山城不肖的儿子。有些烙印来自童年记忆,永远无法重新格式化。这里有一座冥泉宫(Schloss Hellbrunn),是莫扎特幼年时最爱跟父亲去玩的地方。这里最出名的是一套水戏装置(Wasserspiele):一个喷泉阵组,只要启动消息,水柱就会喷洒到猝不及防的来宾身上。还有一座设计成剧场样式的超级水力八音盒,和整整一群发条驱动的百工偶人,就像巴洛克时代的环球影城。

这种恶作剧的文化习性,肯定在莫扎特性格深处留下了烙印,而且是以更为粗俗的方式,在他的生活乃至作品中流露。他喜欢涉及到性或排泄的笑话,尤其擅长抖机灵的双关语。早年他沿意大利西海岸旅行,因为卫生环境欠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便在家信中把眼前的地中海糟改成了Merdeterraneo。从字面讲,就是“屎地”。
前面已经说过,这本书的作者以古典音乐指挥为主业,对十八世纪的歌剧更有特殊研究。而歌剧这种人物、剧情、对白一应俱全的表现方式,又给莫扎特这种经常没正型的性格,提供了更大的展示舞台。这个早慧天才从12岁起,就开始在这一综合性体裁中初试啼声。那出名叫《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的说唱喜剧(Singspiel),讲一对牧羊人、牧羊女,做为欢喜冤家调情,误解,插科打诨,最后欢喜大团圆。
这本不是能够升堂入室的东西。但是一,低俗意味着上升空间;二,但凡雅事皆有俗源。剩下的,就是放到一边先酝酿着。盛年的莫扎特写过不少意大利式歌剧,特别是他和来自威尼斯的剧作家达·庞蒂合作期间,完成了《女人皆如此》、《唐璜》、《费加罗婚礼》,这三部名剧。
等他完成毕生剧场实践的收官之作《魔笛》,简浅轻薄的说唱已经升华出崇高的宗教感,从而完成一个循环。只有在捕鸟人帕帕盖诺和帕帕盖娜这一对活宝身上,还有巴斯蒂安和巴斯蒂娜的影子,不时出没作祟。他们身上反映出一种不为宫廷剧院所容的颠覆性,因而只有维也纳这样的都城,才有不再敬畏权威的犬儒人群,成为他的受众。
帕帕盖诺也是莫扎特所有歌剧当中,自传性最强的一个人物。除乐天、嬉闹的个性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像莫扎特一样爱鸟。西雅图有个博物类作家莲达·琳·霍普特,对音乐也是内行。她新出版的新书《莫扎特的欧椋鸟》,除讨论美国的自然生态问题外,也谈到莫扎特和鸟的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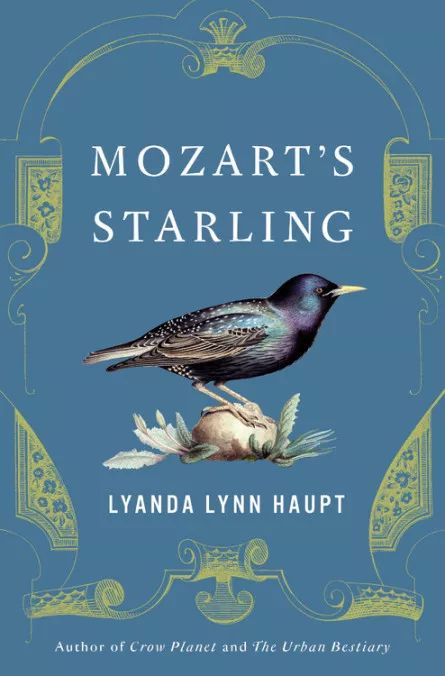
那是1874年5月,莫扎特在账本上记下一笔开销。那天他偶然走过维也纳一家宠物店,听见笼中一只椋鸟唱出一个他熟悉的曲调。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就是他本人新写的。那是他的《G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开头部分。此时距离新作首演尚有时日,可其中一个动机却被这小东西公然外传,对于保密工作相当不利。他当即付钱,连笼子带鸟一起买回家。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版本,说正是这只欧椋鸟,给了莫扎特写作的灵感。
如果此说属实,那就意味着作曲家进行过一次跨物种的采风活动。至于那段旋律的来历,则很可能是某一首失传的民歌,被那只小鸟从哪里听到,后来又唱了出来。莫扎特在笔记本上就此写下一句:“Das war schoen!”(这太棒了)这种鸣禽被林奈以自己的双名法命名为Sturnus vulgaris——一是指普通常见,二是展翅的样子像星星——有很强的模仿能力。笔者住处附近就曾有过这种鸟。有段时间它们喜欢超低空追踪流浪猫,没过多久,半空里就听见“喵喵”地叫。
莫扎特记录的鸟鸣如谱所示,与我们熟悉的乐队引奏,区别先是第二小节最后的延长音,然后是下一小节中的那个sol高了半度。此外就是再巧舌如簧的鸟,也唱不出的装饰音。

下面是我们平时听到的旋律: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17 in G Major, KV 453: III. Allegretto Finale [Presto]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Edwin Fischer -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17 in G Major, Piano Concerto No. 20 in D Minor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17 in G Major, KV 453: III. Allegretto Finale [Presto]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Edwin Fischer -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17 in G Major, Piano Concerto No. 20 in D Minor
那只鸟一共养了三年。就在维也纳老城的大教堂胡同(Domgasse),那处莫扎特故居。鸟死的时候,主人还筹办了一次隆重的葬礼,不少人赶来参加。一首悼亡诗里说;“这儿安眠这一个小傻瓜/ 短短的一生,也有过好时光……”没过多久,老莫扎特列奥波德去世,沃尔夫冈并没去萨尔茨堡奔丧。这期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无法详细知道。
说起维也纳的鸟,想起有一年笔者去该城郊区参观卡尔·马克思大院(Karl-Marx-Hof),然后走到卡伦山下的格林钦。一道溪流从村中蜿蜒而过。日色向晚,花树下的黄昏浓郁得让你睁不开眼睛,惬意的倦怠随风挥发,林中一片鸟声对位押韵,提示你侧耳细听。椋鸟、杜鹃和夜莺昼夜换班的时刻,枝叶间的对鸣似乎早曾耳闻,然后另存在记忆深处某个文件夹。那是贝多芬在《牧歌交响曲》的“溪边景色”一章,记录过的声音。
由此走向村子深处,眼前一条小路,一块朴素的标牌上写着Eroicagasse(英雄小道)。此处必与那位音乐巨人有关,至少《英雄交响曲》写作于此。复行百余米,居然看到一座贝多芬胸像立于道旁。再向前,就是他曾借宿过的,作家葛里尔帕策旧居。果然鸟不欺人。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