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闫红
▍一
小学六年级上学期,我忽然患上了头疼病,我爸带我遍访小城名医,还去拍了脑电图心电图,都没有找出问题。
我做过针灸,喝过苦得叩问灵魂的中药,收效甚微,我爸为此苦恼不已,也有点怀疑我是在装病。
但是班主任为我作证。她跟我爸说,这孩子最近是挺不精神的,那么大的眼睛,现在都睁不开了。我爸提起医生建议我休学,她坚定地说,休学吧,不然,一个好好的孩子给毁了。
我这才知道,我在这个老师眼中,居然也是个“好好的孩子”,而且她也担心我给“毁了”。
她曾无数次地让我请家长,叫我妈把我带回家,后来跟同学解释说,她没有把我开除,是因为我妈差点给她下跪。如今我已经不知道她怎么就这么容不下我,我虽然糊涂、拖拉,经常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成绩也不好,但天生胆小,也不至于恶贯满盈啊。那种被厌恶感,是我人际关系里最初的阴影。
在她希望我离开时,我终于成了一个“好好的孩子”。我爸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那点纠结,被她的“良言”打散,寒假开始之前,我爸带我去办了休学手续。
那个寒假我的日子有点难过,我爸虽然从善如流,内心也不是不疑惑和失落的,我妈干脆认定我是装病。说实话,我当时确实经常头疼,但没到需要休学的程度,对于各方面的怀疑,我也有点心虚。

就在这时,我姥姥从乡下来了,来过年,元宵节后回去。
我是我姥姥带大的,对于和我姥姥共同生活的时光存有美好回忆,就要跟她去乡下。我妈原本不同意,架不住我的眼泪汪汪,和我姥姥的施压,只好答应了。
临走那天,我妈送我们到汽车站,在寒风里替我翻了一下滑雪袄的领子,笑着说,怎么像个没娘的小孩一样。
那是件红色的滑雪袄,我上一年级时,我妈托厂里的上海人带来的,当时长及膝盖,现在袖子都短了,一大截手腕露在外面,从我妈的眼光看过去,难免有着凄凉的观感。
但我是快乐的,被西北风吹得不住吸溜鼻子,也不妨碍我的快乐。
▍二
我跟着我姥姥,坐汽车到县城,滞留了数日。我姥姥还要办点事,托一个表姨把我带到她乡下弟弟家,在我姥姥回来之前,那表姨都陪我住在那里。
那是1987年,我所在的地区百分之七十的乡村都没有通电,但这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少困扰,相反,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煤油灯的气味,以及它摇曳出的气氛。

我姥姥有三个弟弟,表姨是中间那个弟弟所出,另外两个弟弟因为成分高,成了老光棍。
现在一说起老光棍这个词,总隐隐怀有暧昧的恶意,但我两个舅姥爷都是本分厚道的庄稼人,在村里人缘极好,加上家里没有精打细算的主妇,天一擦黑,他们家就成了村里人的活动中心。
来得早的,先据要路津,斜躺在那张破而大的床上,来得晚的,也有同样破的长条板凳可坐。煤油灯的光焰在床头木箱上跳动,舅姥爷免费提供的烟叶,在许多个铜烟锅上忽明忽灭。收音机里播着“全国报纸新闻摘要”或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他们有时候安静地听,有时候会随口聊点什么。
比如庄稼,雨水或是阳光,也谈陈年旧事,村里所有人的历史,都为他人所洞察:
谁曾去过北京,谁的儿子媳妇不孝顺,谁当年曾经与谁缔结婚约,却被不可思议的原因拆散,以及,谁家的女儿去县里看电影,路上被人强暴。施暴者是那一带出了名的痞子,数日后,他暴尸玉米地里,公安来调查,人人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样一桩命案,居然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那女孩的哥哥,后来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
这等大事,被村里人讲得风轻云淡。
白天村人下地,孩子们上学,时间铺展在我面前,任我安排。我将家里带来的书一遍遍地看,那时候书是罕物,大家都习惯将一本书一读再读。
如此这般地过了一些天之后,我姥姥回来了,她有把生活瞬间变得喧哗的魔力,带我串门,走亲戚,她与后庄一位长辈交好,过个三五天,我们就去那长辈家走走,有时还会住下来。
那长辈的丈夫是个老师,儿女都一直在读书,是前后庄数得着的体面人。他们对于能说会道的我,激赏有加,而我,也惊喜地在他们家,发现了很多我从未看过的书。
我以前所读有两种,一是少儿读物,如《童话三百篇》、《三百六十五夜》等等,还有一种,是我爸揠苗助长般地硬塞给我的,像《三国演义》之类。前者对于当时的我过于低幼,后者我虽然也煞有介事地读过一部分,一定程度是虚荣心使然,而且只挑出有女性的部分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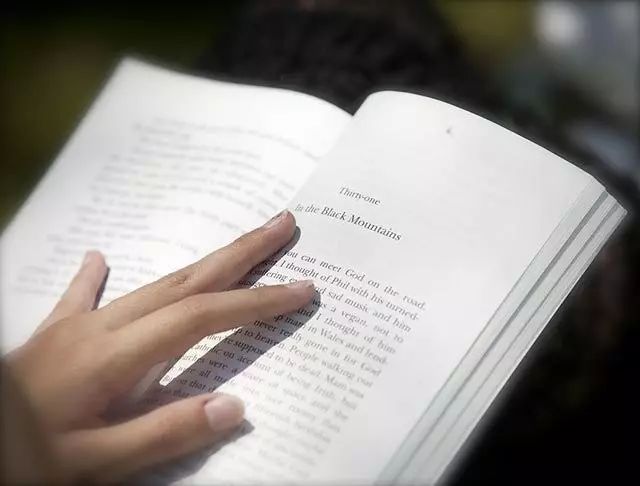
这位长辈家中的藏书则不同,都是些小说,比如戴厚英的《人啊人》,路遥的《人生》,苏叔阳的《故土》,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等等。
我甚至还找到一本琼瑶小说,叫做《剪剪风》,不是书,是手抄本,出自那位长辈在外地读大专的儿子之手。一行行淡蓝的钢笔字,将全文抄在白皮笔记本上,封面上则写着“精神食粮”。
应该说,我当时读到的,都不是一流作品,但它们将生活与阅读打通。在过去,无论是看童话还是看《三国演义》,我的阅读都如隔岸观火,看个热闹,现在,阅读还能提供别处真实存在的生活,让我一边看,一边遥生神往之心。
▍三
我和生活本身之间屏障也被谁突然抽离。在过去,我看似愚钝,却也是时刻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但我收集那些海量信息,似乎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我与生活之间,隔着父母老师,隔着我的“小”,在乡下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动辄遇到生活的真身。
比如在河边,忽见满树桃花,夭夭灼灼,触目惊心。我以前也曾在公园看到过桃花,工作人员将它种在那里,它就该在那里开花,开花于它,也算是事务性工作吧。可是这小河边,这桃花无主,自说自话,忽然胡乱那么一开,就开得如梦似幻,这这,让人到哪儿说理去?
还有下雨。城里也下雨,但跟乡下的雨一比,根本不配叫做雨,没有那么一种劲儿,即使是传说中的三月小雨,在乡下,也有着恐怖的威力。

疾雨如鞭,院子里瞬间积了水,水花互相追打,有作恶的快意。一场大雨能将全村人封锁在家中,即使终于雨停,也不意味着重获自由,你知道什么叫“泥足”吗,鞋子踩在泥地上,被恶作剧般地一再拽下,就算鞋子足够紧,走不上三五步,也会粘上重重的一大坨,拖得你步履蹒跚,咫尺成天涯。
孩子们都不喜欢下雨,但有一次,是需要雨水的时节,它却摆起了架子,久不光临。田野龟裂,禾苗蔫萎,男人端着碗在村中心的饭场上吃饭,“下雨”成了高频词,他们回忆某年某月的干旱,脸上是对现实的忧怖,这情绪传染了孩子,大家都觉得下雨是一件大事了。
我们喜欢生活里有点大事,我们像大人一样谈论并盼望下雨。
最后雨水在某个下午突然落下,雨点如深色花朵,点染在小伙伴们的肩膀上。正在割草的我们,片刻惊疑之后,不约而同地把篮子抛向天空,碎草如礼花,是我们的小仪式。
雨点重重打在肩背上很好,被淋成落汤鸡也很好,我们奔跑着穿越雨幕,在村口,有个女孩碰上了她父亲。那男人面色沉黑,喝道:“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女孩乖乖跟着她父亲回家,这一幕让我沮丧,被盼了这么久的这场雨,不值得为它忘我地快乐一场吗?
我也记得那阳光,在许多个春天的正午,我听见它如蜜蜂般哄哄然闹响;它也有气味,六月里,它将麦子焙香,也被麦香熏染;它还有色泽,有时是蜜色的,在院子里波浪般荡漾,有时又掺进了一点苍灰,在黄昏的旷野上。

后来,我也曾在城市里偶尔与这样的阳光重逢,他乡遇故知般,被唤醒许多过往。
不再相逢的是被流星划过的夜空。入夏之后,村里人都将竹床搬到外面睡,有人经过,就互相招呼。这种开放式的睡觉方式,新奇得让我无法睡着,有许多个夜晚,我大睁着双眼,面对夜空,常常看到流星坠下,不太快,好像坠落得也不很远。我真想撵上去,看看它在地球上的样子。
当然,乡下也并不总像悠缓的田园诗,某些时刻,气氛突然被旋紧,孩子们啪嗒哒的脚步,将诡异的兴奋带进每一家——大人们确认一桩新闻事件发生之前,通常会派孩子去打探消息。
那一次,是一个曾被拐卖在这里的妇女回来了,探望她的两个孩子。
这事听起来不近情理,放在吾乡背景下却不稀奇。女人是从四川偏僻之乡被人“带”来的,那人之前将吾乡描述成了天堂,答应帮她寻个好婆家。到来之后,女人这儿发现比他们家乡也好不了多少,她落脚的这家尤其惨。
一开始她也又哭又闹寻死上吊的,后来,她的“婆婆”说话了,说,闺女,你这都出来了,回去也寻不到好人家了,还不如在俺家住下来。过两年,你生下一两个,我去帮你跟XX说,让他这次好好地帮你找个人家。
女人知道这家为自己花了“巨款”,也只得这样了。她婆婆倒也说得出做得到,这女人生了俩娃之后,她托人给女人找了个开私人诊所的老光棍——此人也是因为家庭成分高沦落成了“剩男”。
女的倒是有点舍不得孩子了,但实在过够了穷日子,一咬牙,跟那男人走了。
这事儿发生在我到来之前的秋天,村里人说起来,就像是说一本书,羡慕者有之,骂这女人心狠者有之,表示理解者有之,夸赞女人之前的“婆家人”仁义者也有之。大半年后,这女人再度出现在村口,满村都是熊熊燃烧的八卦气氛啊,在不通电的年代里,上哪儿能看到这么一场跌宕起伏催人泪下的真人秀?
我也跟了村里的孩子蜂拥至“前婆家”的院门,但见一个高大的女人坐在堂屋里,谈不上好不好看,表情木然,女人们围坐在她旁边。我还没看清楚,有人上前把门一关,啥也看不见了。
▍四
我在乡下过了四个月,我爸妈托人带话了,要我姥姥把我送回去。说是开学在即,需要收收心了。
我回到了城市,情绪饱满地,不知怎的,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日子会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有这种感觉。
新的语文老师对我不错,她很快发现我善于表达,我喜欢描述,尤其长于景色描写,这在小学生里是罕见的。老师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念,有次她帮隔壁班的语文老师代班,还拿到那个班里去念,我在学校里有了点小名气。
老师让我谈谈写作文的经验,我站在课堂上,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说了要多看书之类,但我知道那不是主要原因。
如果我能够穿越回去,我想说,是那段不用上学,也不在父母治下的生活,帮我急促现实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间隔,一种缓冲,我逃出我的无力感,逃出那些也许并无恶意的压迫,缓慢而自觉地,和生活彼此诚挚以待。
我还想说,在乡下的这段并不奇幻的漂流,打通了我和世界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我像是穿越了漫长混沌的甬道,终于找到出口,光线涌进来,周围变得透亮,我看得见也听得清,我很想对人说,我都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而写作,就是想对人说点什么啊。
当那愿望被激活,就像火焰不再熄灭,一直到现在。这些年我遇到许多问题解决许多麻烦,我曾心灰意冷,又总能让自己鼓起勇气。我写了很多字,有的还可以,有的很一般,我逐渐成为资深写作者,依然有着讲述的热望。我真的要庆幸那次的被激活,让我,毫无预兆并歪打正着地,与我最喜欢的这件事相遇,虽然,那场漂流,给我的还有很多。
【作者简介】
闫红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误读红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