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光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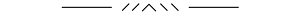
食物中的当代微观小史
文 | 西门媚
第一次吃火锅时,我在火锅边睡着了,而且是趴在桌边上睡的。
不单是我,还有几个高中时的同学,阿华、阿秋、小敏等等。东倒西歪,睡在镶着白磁砖的桌沿上。
那时,火已经熄了,一锅红油正渐渐冷下来。
1988年,火锅进入成都市不久。火锅是从重庆传来的,带着传说。听听那些名字:小天鹅,热盆景。连名字,都有别样风情。
听我妈讲,她年轻的时候,成都也有火锅,跟后来的不同,是那种中间烧着炭火的铜炉。年轻人也喜欢,后来才消失了。
我没问过为什么消失,都知道,经历60、70年代,成都就跟其他城市一样,很多传统餐饮都消失了,直至80年代才慢慢回归。
在凭票供应的年代里,不可能有火锅这样铺张的事物。
成都的餐馆,1988年之前在我心里,大抵只有两样,要么是小吃,要么是炒菜馆。小吃,是我们每日都吃的。从学校对面的酸辣粉、刀削面、麻辣抄手,到学校门口电线杆下的煎苕饼、炸豌豆饼。炒菜馆跟家长才会去,一般重大时刻才去。
但是火锅,听着就觉得神奇,意味着成人世界啊。家长是绝对想不到要带孩子去吃火锅的。
但是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
1988年,我们从那个特殊的计算机班毕业,一如开始所有人预期,同学们压根没有人想去参加高考,而是选择工作。离开学校,去工作,那时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进入成人世界一样诱人。
但同时,每个人心中都怀着强烈的不安。
到了秋天,同学大约有一半的人开始工作了。工作有的是父母想办法安排的,有的去考了工。能从事专业的人不多。有的同学,找个打字的工作,就算是跟专业有关了。在1988年,电脑打字都是一个专业技术活。
我很幸运,进了研究所写电脑程序。周围同事也都是真正做设计的人。像这样的工作,在同龄人中,是罕有的。
但在十八岁的年纪,智力和心理的成熟,并不同步。
我做设计的能力不输于大学毕业的同事,心理上却还是个未成年人。同事们像哥哥一样关照我,我还是喜欢跟同学玩,觉得跟同龄人在一起才放松,想在他们那里找到认可。
从夏天起,同学们经常晚上都会聚在一起。都是八九点以后,骑车出门,一家家地去叫其他人。到每家的楼下,吹一声口哨,楼上应一声,就下来了。
多数是男同学,有时候也有两三个女生。
他们也常拐到研究所来叫我。如果手上的设计做完了,我就跟他们去骑车。
最多的时候,能聚到十几个同学。我们沿一环路骑行。那时一环路还没全部修好,修好的地方自行车道很宽。男生们勾肩搭背地骑车,连成几排。边骑车边大声唱歌。
好像无忧无虑,一首接着一首,争取不重复。什么歌都唱了,当然最喜欢是搞怪一点的歌。那种改编之后,带点儿痞气的歌。最著名的是那首:“跛跛去当红军,红军不要跛跛……”,这是每次要唱的。但男生们最喜欢的是这首:“前面的妹妹听我说,把你的姐姐嫁给我,给你爹说,给你妈说,给你姐姐做工作,那样我就是你呀你的姐夫哥,嘿,划得着!”
但这首歌不是每次都会唱,唱了大家嘻嘻哈哈的,但还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想不起别的歌的时候,停顿的空档,大家随口唱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林,正义的来福林,一定会把害虫,杀死杀死!”
这是小时候就看熟了的电视广告。
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基本不是唱,是喊叫,是一种恶狠狠的感觉。重要的不是农药“来福林”,而是“害虫”。“害虫”才是我们的心声。
一群年轻人,在半夜里,觉得青春躁动,又茫然不知方向,才会喊出“害虫”的心声。

每次都骑到半夜,声音哑了,被街边住户抗议喝斥,大家才纷纷散去。
初冬,我的给飞机厂的程序写好,用户手册也写好,飞机厂也验收通过。我闲了下来。
这天晚上,同学们又拐到研究所来叫我骑车。我跟着他们,一会儿,就绕道进了西南民族学院。阿华的表妹是这里的大一新生。
进民院校门的时候,大家很紧张,却要故做镇定。最近,我知道他们经常巴巴来约表妹和她寝室的同学,想带她们一起骑车。
表妹她们有时会应允,有时推三阻四。
今天,阿秋对阿华的表妹和同学说,今晚可以去他姐的火锅店吃火锅。
这出乎大家的预料。都知道他姐新开了火锅店,但从没邀请过大家去。大家也从没往这个方向去想。
表妹她们也愉快地答应。
但不是马上去,阿秋说,晚一点再去。
大家仍旧像以往一样,沿一环路骑行,骑到西北方向,路断了,又往回骑。唱着歌,东游西荡。磨蹭到十二点过了,准备往火锅店去了,表妹她们忽然说,她们要回去了,明天还要上课。
挽留无效,先送她们回了学校,再骑二十多分钟,到了火锅店。
火锅店已经关门了。阿秋并没有钥匙。他把门锁上一边的搭扣搞了一会儿,就开了门。
火锅店不大。只有五六张台子。台子上贴着白瓷砖。中间是冷了的油锅,暗红色,冻着厚厚的牛油和辣椒。
要不是阿秋能熟练地点火,看他那开门的架势,简直会怀疑,这根本不是他姐的店。
阿秋拿了些菜来,没有荤菜,只有土豆、白菜、豆芽、海带之类。但锅一烧开,土豆煮熟,热烈麻辣的牛油气味扑面而来。大家马上吃得狼吞虎咽。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有香油碟,要加蒜蓉什么的,每人一只碗一双筷就够了。
直到阿秋说,没有菜了。大家才觉得倦意上涌,不知不觉都趴在桌上睡了。
清早,我醒来,看了看还在睡的同学们,没吭声,出门,骑了自行车,汇入了上班的自行车流。我还觉得倦,没睡够。看见那些早上的人,路边卖菜的人,扫地的人,觉得那些人都精精神神,忙忙碌碌,都很有希望的样子,早晨是属于他们的。
自己与早晨无关,一阵晨风吹来,忽然觉得一阵虚空。
我想起小时候,因为看书又多又杂,老是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同学给我取名“博士”。顶着这个“博士”名头长大了,现在连大学都没上过。而研究室里的同事,哪有没念过大学的呢。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博士”,就变成一个笑话了。
骑到半路,我拐了方向,骑回了家,回到家中,对我妈说:“我想考大学了。”
我妈一听这个,马上眉开眼笑,像等了许久。然后我嗫嗫地说:“我不知道怎么跟所长说。”
然后,我妈就带着我去了研究所。她去了所长办公室,我躲在研究室里,没敢去。但正好两隔壁,他们的话,我听得到一些。
我听到所长说:“是不是赚工资少,我会给她涨啊?”
我的工资是比研究室的同事少很多,而且理由就是文凭。我最初是不满,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妈解释,是因为我想念书。
一会儿,我妈就过来,向我转述,说,所长说了,他本来就打算明年送我去念大学的,就学计算机。
那一瞬间,我的确有点动心。但随即想,我已经说了要辞职,就不能变。我跟我妈说:“我想去念文科。”
我妈又去了所长办公室。所长又惋惜又生气,可能还觉得有点好笑,觉得我连辞职都不会。他走到研究室来说:“当我这儿都是幼儿园啊,还要妈妈来说。”
就这样,我红着脸,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辞职,重新回到学习的路上。
好些年后,同学聚会,我跟他们谈论起这次火锅,其他人都不大记得了。但好几个同学,也的确是先后在这一年,忽然“长醒”了,这一年,就像现在常说的“间隔年”,他们选择读书或者进修,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

【作者简介】
西门媚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小说家,独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