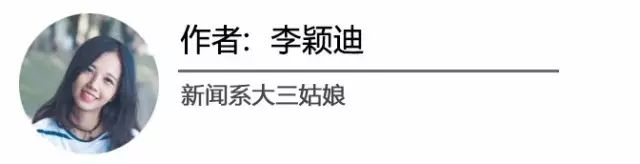《星空》剧照
潜意识里,叶杨并没有把求助父母当做一条有效且可靠的渠道。偶尔父母提出异议,她也不以为意,“你们凭什么以这样的角色出现?凭什么干涉我?”
前言:
潜意识里,我一直觉得留守儿童的故事一定是悲惨的——贫穷剥夺了孩子享受爱的权利,又将他们推向各式各样的深渊。
那么多极端的校园霸凌案件历历在目,以及类似柴静所写的《双城的创伤》里面,五个农村孩子相继自杀,未遂的孩子同样封闭、沉默。最后,柴老师也没能弄清楚孩子们的内心,只说对这个世界平添了几分无解。
但阅览完叶杨的几百条微博,我才明白,“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确实存在的。”正如她朋友所说,“其实她这么多年,只是拿土把心结埋起来了而已,最核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旦有机会,她立马就被打回原形。”
但叶杨说她在有意识地“卸妆”,尤其是日后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时,如何更坦诚地面对自我,“这很困难,但会努力去做。”她说。
在叶杨看来,她和父母中间总是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
5月16日,叶杨转发了一篇有关性侵的文章,下意识地屏蔽了父母。
“更多是为了不让他们担心,但会不会有其他因素在里面?也不好说。”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叶杨还在读小学。一次放学回家,三个小混混隔着五六米对叶杨猥琐地笑,迎面时,其中一个猝不及防地伸手摸了她的下体。叶杨当时愣着站住,混混走了,她才感到愤怒,但是,她最终没有告诉家里人,“怕他们笑话”。
更恶心的一次,发生在初三备考阶段。临近中考,叶杨开始频繁地丢东西,眼镜、笔……起初她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异常。直到有一天,叶杨喝水服药,发现保温杯里被人装了尿液。班主任口头上说要严查,但中考在即,最终没有做什么。
叶杨将目标锁定在一位同班同学身上,在那之前,那位男生总说自己和叶杨关系亲密,捏造绯闻,说他们单独出去逛过街。
原本一直独自回家的叶杨,在周末反常地打电话给父亲,让他来接自己回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对那位同坐校车的“可疑对象”怀有本能的恐惧。但是对父母,她只说是“被男生欺负了”。
潜意识里,叶杨并没有把求助父母当做一条有效且可靠的渠道。
这件事发生后,叶杨发誓,“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校长希望成绩在年级前十的叶杨留在本校,私下里还请她的父母吃了饭,承诺了万元的奖学金。叶杨的父亲很心动,几次劝说,叶杨口头答应着,但最终选择志愿的时候,还是头也没回,填上了东莞最好的一所高中。
如今,叶杨已经习惯先斩后奏,填志愿、谈恋爱、做公益、做实习……偶尔父母提出异议,她也不以为意,“你们凭什么以这样的角色出现?凭什么干涉我?”
● ● ●
二十年前,广东汹涌的经济浪潮吹到了这个家庭,叶杨的父母在东莞开办了一间服装工厂,无暇照顾刚刚断奶的第二个女儿。和90年代成批出现的留守儿童一样,叶杨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距离东莞270公里。
叶杨还曾面临更可怕的命运——“重男轻女”在当地根深蒂固,叶杨的父母渴望有个儿子,他们曾试图把叶杨送给无法生育的朋友,但被老一辈阻止。
最初的十年里,叶杨自由而野蛮地疯长着。这个物质不缺、朋友不缺的女孩儿,唯独缺少父母陪伴,缺少必要的管教。等到稍微有意识时,她发现,只有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周末到朋友家里“野”,叶杨心里隐隐羡慕着,她觉得“有人在真好”。尽管朋友的父母是在吆三喝四地打着麻将,有时还会粗鲁地骂人。
这也让她更加期盼父母一年两次的探望。
有时爷爷奶奶随口说,“今天你爸妈回家”,她就搬来小板凳,坐在门口。爷爷奶奶的家在河源市一个县城的环城马路旁,对面是宽约100米、倾斜30度的斜坡,紧接着一片凹地,没有视线障碍,叶杨能远远看见另一边的高速公路,她总以为父母开车回来会经过那里。
但往往在板凳上坐了一天,太阳从东边落到西边,叶杨也听不到轮胎摩擦马路的声音,只感到时光的无望。
可在父母真正回来时,叶杨只会躲在门角捂着嘴笑,人前她又会刻意地冷淡,表现出不粘人的模样。一个新年过后的夜晚,叶杨的父母都回到了东莞,她躲在被子里咬着枕头哭,实在受不住时,才跑到奶奶床边,钻进被子里,摸奶奶手臂,贴着那份温柔慢慢睡着。第二天奶奶问她怎么偷跑来,叶杨回答说,“我怕鬼”。
因为这一段经历,叶杨说,自己血脉最深处的第一份依恋、恐惧、疼惜、愧疚、爱与痛,都来自爷爷奶奶,而不是父母。
比叶杨年长两岁的姐姐,也在读小学前被送回了河源。父母很快赚到钱,给爷爷奶奶盖起一栋四层洋房,门口立着花坛,内外贴上瓷砖,配有沙发、空调。
叶杨和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但关系不算亲,经常打架,有时也会一起在墙壁上贴周杰伦、S.H.E.的明星海报。
在镇上读小学后,叶杨的姐姐开始接触一些“同样没人管”的小孩,频繁进出网吧、KTV甚至是酒吧,还会在厕所和别的女生打群架,学抽烟,往脸上“浓妆艳抹”。姐妹两也很“财大气粗”——父亲每次离开前,都会留几百元在房间的抽屉里。叶杨跟在姐姐屁股后面,也进那些场所体验了一把。但她在网吧里不过是上QQ,用那种流行的方式与陌生人聊天,“嘿,美女”。
坐在灯红酒绿的小酒吧里,她明显感到不适应,只会在一旁默默喝饮料。
“留守儿童嘛,就是什么都干!”叶杨自嘲地说,随后再次放肆地笑,杏眼弯弯,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和气的神情里带着狡黠。
叶杨五岁时,弟弟也加入了留守大军。此前叶杨一直不知道弟弟的存在,直到奶奶随口提起,她才知道家里又来了一位新成员,而且是男孩。因为接触不多,弟弟在叶杨的童年印象里,几乎处于真空状态。
五年之后,父母不顾长辈的反对,连哄带骗地先把叶杨和姐姐“要”回了东莞,转入了当地一所民办的寄宿学校。但他们每天仍旧在工厂里加班到12点,没日没夜,仿佛是广东那时的常态。“爸妈只是觉得呆在身边好一点,这边教育好一点,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没有时间陪我的。”
叶杨原本学习很不用心,在东莞,对新环境的不信任却刺激着她不断奋起,靠学业出色获取安全感。转学过后的第一次考试,就是班级第一。
与此同时,叶杨的姐姐则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也许我想获得父母关注的方式是用成绩,但我姐就是用‘做妖’。”那段日子里,姐姐只顾着疯狂追星,为“东方神起”(一个已经解散的韩国偶像男团)花光所有零用钱,天天对着电脑,还学会从外网搬运欧巴们的最新动态,成为贴吧和微博中的“小v”。
进入青春期的叶杨,下意识地关上了与姐姐沟通的那扇门。“姐姐雷区很多,一踩她就会炸毛,久而久之就完全不说话了。”尽管同上一所初中,叶杨偶尔还会与弟弟一起乘校车,但从来没与姐姐一起回家过。
● ● ●
周末回到家,父母开始倾泻对姐姐的不满,还拿成绩优异的叶杨与其比较,这反而激化了矛盾。姐姐会当着叶杨的面对父母说:“你们就是偏心!”最激烈的一次,母亲在客厅里指着姐姐骂道:“早知道你这样,一出生我就把你弄死,宁愿生一个叉烧都不生你……”
“现在我如果听到我妈再这样说,我肯定会指出她的不对。”但在当时,姐姐和父母在客厅哭闹,叶杨往往躲在房间,捂着被子继续睡。“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可是我不会想去调和。”
随后的日子里,她也察觉到弟弟沉默下的异常,在叶杨的印象中,弟弟从来没有在家里表露过情绪,“我姐明显是属于叛逆型的,我弟的状态就捉摸不透,他看起来无欲无求无烦恼,谁知道他内心又在想些什么呢?”
上大学后,叶杨有次时隔一学期才回家,坐在客厅的弟弟看见她进门,只“哎”了一声,然后就提着书包匆匆回房。那一刻,叶杨对弟弟的淡漠感到不解,“这么久没见我,发现我突然回来,也不会惊讶一下吗?”
有时弟弟出去玩,叶杨自然地问一下,弟弟反怼回来:“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啊?”
“我父母就是很典型的广东父母吧,只顾赚钱,但他们本身对教育是毫无办法的。也是这种被迫留守和放养,才会让我们三个有这么大的差异吧。”对叶杨来说,姐弟三个就像是豆荚里的三粒豌豆,彼此的关联若有若无。
如今,读高二的弟弟成绩仍旧烂在班级末尾,姐姐更像是浸泡在生活的死水里——经历休学、去韩国、读技校之后,姐姐好像失去了争取的心气,还在家中待业。
姐姐经常在半夜两三点在朋友圈发感叹,比如“感觉自己的人生不会再好,想重新来过”。叶杨有些担忧,私下里揣测姐姐患上了抑郁症,但她没有告知父母,因为觉得“他们也不会理解”。
2016年国庆之夜,父亲和姐姐又开始大吵,听到父亲说出“你滚”,23岁的姐姐没有丝毫犹豫,拖着行李箱跨出家门,随后不接电话不回微信。被父母找到时,姐姐正躲在一家小旅馆里,吃着外卖看韩剧。
在劝说姐姐用“寄养”的名义偷带回一只狗后,叶杨以为它会成为一个转折——为了让这只带有狗瘟的雪纳瑞活下来,姐姐主动地四处打听,买来中药,也在父母嫌弃这只大小便失禁的狗时坚持了下来。但强力续命7个月之后,狗还是走了。
狗去世之后,叶杨看到姐姐发了一条朋友圈,她觉得爸妈会为此开心,不可能有安慰,她开始找姐姐聊天,“人生有时太多无奈,有时候,并不是尽力就能做成什么事,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尽管在这一长串安慰之后,姐姐并没有回她。
她也开始打电话到家里,找弟弟说话,虽然话筒那边的弟弟依然只会说“哦”、“嗯”、“啊”。
叶杨对最初的东莞生活的记忆,既有学业上的得以,也伴随着融入新环境的羞赧、不安和艰难,班里全体女生的排斥尤其是噩梦。
那段时间,有时叶杨仅仅是在课桌上写着作业,女生们都会聚在一团,看着她,故意大声地笑。还有的女生表面上对她很和善,下课时凑过来用手挽着叶杨,却暗暗用指甲狠狠地掐她的胳膊。叶杨不敢动,更谈不上反抗,没人的时候翻开衣袖,只看到深深浅浅的月牙。
绝望让叶杨愈发小心翼翼,她开始刻意讨好主动与她说话的女生,更敏感地观察着周遭环境。也许是为了寻求安全感,六年级的时候,叶杨早恋了——在一辆校车上认识的李清与她表白时,她很快同意。
“你当时对感情有认知吗?”
叶杨点点头,广东口音略微咬字不清,但语速很快。“当然知道,而且后来我总会时不时想起,很多情绪,很多问题,第一口尝试,第一次思考,都是他带来的,真的感激。”
最开始,叶杨十分拧巴,有时李清坐到她身边,她会生硬地说,“你走开”。一次周末回家,李清没在校车上,叶杨又觉得空空落落。同班同学递来手机,叶杨接到了李清的解释电话,但她故作冷漠地回应:“哦,好吧。”
李清问,“你不失望吗?”
叶杨反问,“为什么要失望? ”
“可是我很想你啊”,听到李清说这句话,叶杨心中封存已久的贝壳突然打开了,好像触动了内心最深处的柔软。她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对别人表达感情。”
● ● ●
暑假里,叶杨回到爷爷奶奶家后,每天都会偷偷到一楼拿座机给李清打电话,天南地北地聊一个小时。“用玛丽苏(意指俗套的网络言情小说)的话来讲,就好像突然有人走进自己的心一样。”
就像经历过严重饥荒的人,一生都会对食物有种别样的情感,叶杨无法克制内心对陪伴与亲密的渴求。初恋之后,她在初中、高中、大学又分别谈过一个男朋友。
李咏嘉与叶杨中学时代就是好友,那时的叶杨显得很有个性,高中早恋被发现,居然能挺直腰背反驳老师:我们成绩都不差,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生活中的叶杨,显得古灵精怪,喜欢穿活泼的吊带裙,头发也染成了栗色,看上去就没有不开心的事情。李咏嘉对叶杨的深刻印象,就是断腿打石膏之后,还举着拐杖到处与人合照,“那个傻X”。
“上大学之后,我通过一些事情慢慢了解到,原来她的内心是这样敏感、脆弱。”今年三月,李咏嘉看到叶杨在朋友圈里发“想谈恋爱”、“某某健身教练好帅”,甚至会在一条状态里回复十几个“哈哈哈”,他察觉到异常,打电话给叶杨。没想到刚接通,对方就哭成了河水泛滥。“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她那个谈了两年的男朋友。”
分手是叶杨自己提出的,和前几次一样。她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的爱,也害怕对方离开,总会逼问男朋友曾砾:“如果我们以后没有感情了怎么办?”
这一次,曾砾的回答是,“不知道”。想想最终会被扔下,叶杨觉得难以忍受,就像顾城的诗——“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她自觉消极愚蠢,可还是被那个偏激的自己打败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曾砾曾为叶杨的“阳光”着迷,这个长发及腰,眼窝深遂,戴着圆框眼镜的姑娘,平日里总笑眯眯,卧蚕弯成一条缝,做什么事都有十二分的活力。但在感情的磨合当中,他慢慢感到叶杨身上的那层防备,“她从来不说她真正的感受,最初也会回避她的家庭和过去。”他也发现,叶杨总是会问“想我吗”、“喜欢我吗”,而不会直白地说“想你”、“喜欢你”。
吵架的时候,叶杨拒绝沟通,而是直接拉黑所有联系方式,总是一冲动就说分手。“在其他人眼里,她非常独立、要强。但是对于感情,她还是很依赖的,而且会故意表现出不依赖的样子。”
分手之后,叶杨才向曾砾坦诚,“我特别特别特别享受做一个‘小女儿’的状态。”现实生活中,叶杨的父亲性格死板,脾气暴躁,唯一的交流是每月定时转生活费。她把理想中父亲的形象投射在曾砾身上,渴求绝对的包容。
5月27日,叶杨独自走到武大后门的东湖栈桥上,哭了一小时。湖风凉凉,水潮拍打着水泥岸,她对刚刚终结的感情有所反思。“经历这一段,无论未来跟谁,我都会变得更坦白,对真实的想法和愿望直言无讳,做一个不伤害别人,也不因为矫情伤害自己的人。”
到大学以后,叶杨才慢慢地试着直视成长中的伤痛。
童年时候的她,对父母的依赖得不到回应,只能用坚强包裹自己。要强,执拗,凡事都想争第一,但总对自己存留怀疑。
有时,她梦到自己被狗咬,静静地看着它的牙齿毫无犹疑地深入,“那种感觉很熟悉,像日常生活中等待即将到来的痛苦的那一刻,隐藏着暴戾和痛快的情绪。”
高三的时候,内在的对抗难以承受,她开始焦虑失眠,手控制不住地抽筋,一度怀疑自己得上狂躁症。她尝试着用“写给未来另一半的信”来舒缓——“我唯有把你当作所有的信念依赖。”
随着眼界的拓展,她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安和自卑恰是家庭关爱缺失的后遗症,而现在,是否要为自己“卸妆”?是否要努力和自我和解?
即将大四的她,打算用接下来的一整年参与公益项目,“最理想的情况是去凉山”,出于私心,她想再回一趟自然,那是她少有的归宿。
在叶杨的留守童年里,被放养的她四处疯玩,与朋友一起坐公交车,晃悠一个小时,离开县城,来到农村。一位好朋友带她去乡下亲戚弃用的房子里,叶杨走进正门,穿过天井,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走进房子的后院。
她至今仍然记得打开门的一瞬间内心的震撼与感动。后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老树,孤独而傲然地存在了好多年,枝蔓肆意伸展,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败落下来的黄叶铺盖了地面,一脚踩上去,脚掌被叶子包围,温柔得让叶杨不敢用力。一阵风吹来,树上的叶子哗啦哗啦响,伴随着脚踩落叶的声音,叶杨兴奋地叫了起来。
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在自然面前发了呆。这份感动,滋润了叶杨好多年。
● ● ●
后记
大二时,叶杨曾去武汉一个留守儿童公益机构上课。相处一天之后,机构的校长问她,“你应该是被留守过吧?”叶杨当时“就像是被电到一样”,她反问校长,“你怎么知道?”
校长笑了,“从你的眼神猜出来。”他接着说,留守儿童在童年缺乏父母关心时,长大后有两个走向:堕落叛逆,或者是内心变得强大,但两者都对爱极度渴望。看起来很乐观很有能量的叶杨,总想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离开,但却又矛盾着,想把内心对爱的渴望向外界转化,以此缓解焦虑。
“我觉得他说到点上了。”
编辑:关军
本文为“2017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非虚构写作”板块特别约稿。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姓名均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