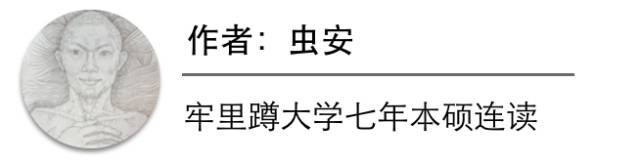《被告人》剧照
每天都有赶不上流水线进度的犯人发生殴斗,他们举起凳子,凳子被链条锁紧在机位上,他们又拿起剪刀,剪刀也被链条锁死在机位上。他们举起拳头站进衣槽里扭打……
前言:
入监的第一个夏天,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劳务监区度过。可怕的两个多月之后,我脱离了那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得以在非劳务监区度过自己漫长的刑期,这很幸运。
罪人真的可以通过劳动和汗水完成自我救赎吗?
我显然不是。
6月的某天,入监监区的大厅挤满了准备下队改造的新犯。八点钟的早晨,夏季火辣的热光从生锈的窗棂投射进来,十二架高风力的电扇丝毫驱赶不了日光带来的烦闷和燥热。
肥胖的组长举着手中的点名册正在大声喊叫:
“李欣和四监区,王伟十二监区,夏龙龙二监区……”
我听到自己的名字,应答之后迅速站进了“二监区”的方框里,那是一个用粉笔标识好的区域。组长点名的声音还未结束,四五平米的方框内又站进来几个新犯,我们忍不住交头接耳:
“二监区是干嘛的啊?”
“箱包监区,踩缝纫机。”
“你几年?”
“三年半。缝纫机要踩死了。”
听到三年半刑期的犯人都发出了恐惧似的抱怨,我把视线转向了窗外,十年六个月的刑期,会有多少个非同寻常的夏季等待着我。
在这种忧虑中煎熬两个小时之后,二监区的狱警出现了。健壮的年轻狱警敞着两颗印有国徽的金属纽扣,武装带的皮扣穿透了他级别尚浅的警衔。
签完交接,他抱起一摞牛皮纸档案,挥舞着长满了汗毛的手臂示意我们即刻出发。
一群人跟着狱警走出了监区大门,猛烈的日光瞬间向我们袭来,下意识地,大家纷纷举起手中的脸盆和凉席遮挡住光秃秃的脑门。
“放下!”
狱警的怒斥让我们迅速放弃了遮掩和保护,排成一列朝着各自被指派好的监区出发了。
二监区的劳动地点在箱包总厂的五楼,那栋楼就像一块躺倒的巨型长条积木。年轻的狱警把我们带到了二监区厂房的门口,那里贴着醒目的红色警戒线,他命令我们蹲在线外等待监区大队长的训话。
大队长迟迟未至,我们纷纷站起身来朝着门内张望。我看见宽敞的厂房里排列着十几条箱包生厂线,到处摆放着凌乱的半成品购物袋,蓝色的大塑料框内堆积着五颜六色的布条,电动缝纫机“吱嗞嗞”的声音片刻不歇。
门口的几个犯人正在给一沓橘色的购物袋包边,额头和胸口涌出油腻的汗渍,抬头与我对视时,眼神凶恶而又挑衅。
警务台上坐着两个中年狱警,一架小型风扇正在慢吞吞地左右摇晃。一条线上的前后道工序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个线长正掌掴某个压货太多的犯人;后勤和小岗躲在烫台上用熨斗烤馒头片……
这时,有犯医向狱警汇报,“报告干部,我要领一把老虎钳。”
在不远处,一个表情痛苦的犯人正在缓缓靠进警务台,他举起的食指已然被缝纫针扎透。
“他是哪条线上的啊?跟他们线长说产量不能降。”狱警说。
随即,犯医领到了老虎钳,用一把老虎钳帮受伤的犯人拔出了食指里的缝纫针。
● ● ●
大队长回来的时候,我们这群无知的新犯仍站在门口东张西望。
“哪个叫你们站起来的?”
大队长瘦长个,头顶微秃,他的怒斥令我们迅速恢复了一开始的蹲姿,我们看着他去办公室拿来了武装带。
“入监队怎么训练你们的?我还没见过这么不守规矩的新犯,不给你们长长记性,你们不知道二监区的规矩,一个个蹲到我面前来!”
第一个蹲到大队长面前的犯人是24岁的何华,他因为家庭纠纷砍掉老丈人两根手指,需要在高墙之内蹲够四年为自己可恨的脾性买单。
电警棍的火花在他的眼前悬空绕了一圈,他开始了尖叫,继而躺在地上打滚,就像一条在泥地里被曝晒的蚯蚓。
第二个吃电棍的犯人是55岁的陈和忠,他是个二进宫的扒窃犯。没等大队长喊他,他就已经站到他的跟前去了。
“干部您看,入狱前我往身体里拍了四根针,这些针现在已经游到胸口部位了。我怕我吃不住电,一打滚被针扎出事来连累了您。”
他在大队长面前撩开了囚服的领口,大队长看过之后又查阅了他的档案,然后他把电警棍收回了武装袋。
“今天就先不跟你们计较了,你们必须尽快适应二监区的改造生活,想清楚三个问题: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你们是什么人?”
大队长提的三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去思考。从二监区的厂房回到监舍,我被分配去了19组。
那个监舍破旧的如同得了皮屑病,在爬满飞蚁的墙角粘结着摇摇欲坠的蜘蛛网。幽暗的过道两旁分别摆放着四架双人床,返潮的地面令所有的床脚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铁锈。床铺上摆放着方正的被褥,但是在光线之中蓝色床单上轻蓬着的皮屑还是令人倍感肮脏…….
晚上九点钟,收工回到监舍的组长敞开了他那件被汗渍浸染的囚服,露出了肚子上松弛的皮肉。
他斜躺进床铺,几个年轻的囚犯给他递来了湿毛巾和凉席。舒缓了体内的燥热之后,他翕动着鼻孔,露出肉鼓鼓的嘴唇后面的黄牙开始让我挑选“新丁服务”。
“洗头还是踩背?自己选。”
我贴靠着墙壁小心思考,所有可怕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经历。我需要鼓起勇气迅速选择这两项难以避免的“新丁服务”。在片刻的犹疑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监舍肮脏的厕所,以及在看守所被四个人摁在便池里“洗头”的可怕场景。
“踩背。”我坚定又无奈地做出了选择。
话音刚落,六七个犯人就举着一条粗糙的军被朝我走来。我蜷缩在墙角,随即便被那条霉臭的军被覆盖,任由密集的拳头和脚掌对我完成了“踩背服务”。
组长揭开了罩在我头顶的被子,“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卧着,监舍里的活给我勤快干着,还得给我时刻记着:你他妈就是个新来的。”然后,组长继续斜躺进床铺,朝我露出了长满痱子的后背。
我想他已完整地替我回答了大队长那三个问题。
“你呀,还算有种。一般的新犯都选“洗头”,不是每个新丁都扛得住“踩背”的。快去洗洗睡觉吧。”
他说完这句话后,立刻响起了巨大的鼾声。我去厕所冲了两盆凉水,在从头蔓延至脚的湿润之中安抚自己早已瑟瑟发抖的魂魄。
整个无风的窗外弥漫着沉闷的黑暗,红外报警器的指示灯闪闪烁烁。
8月末,二监区的厂房在这些炎热的日子里突然停止了令人厌烦的生产噪音,整个夏季生产的箱包被全部退了货。
堆积如山的购物袋成了犯人们午休的枕头,每台缝纫机底下都躺有三三两两熟睡的犯人。他们敞开着胸脯,在两侧的脑门涂上了薄荷味的清凉油,味道在车间里到处流溢。
然而惬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在缝纫机底下互相自慰的犯人被巡视的督查组当场发现。他们从缝纫机的底部被揪到了过道中间,值班狱警让他们光着屁股去烫台上罚站,小岗打开了烫台边上的窗户,整个下午,饱和的光线在他们饱满的臀部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
昏昏沉沉的傍晚在午后急速迫近,成群的蜻蜓、大片的乌云、灰暗的黄昏,巨大的惊雷此起彼伏。
二监区收工的队伍被八月的暴雨冲刷得七零八落,犯人们顶着花花绿绿的购物袋在雨水中尖叫着逃窜,他们故意用脚踩出浑浊的水花,在奔跑之中相互推搡,收工队列之中那些“不许勾肩搭背、不许交头接耳”之类的规矩全被刻意破坏了。
回到监舍,大队长把所有犯人集中在了大厅,提着一根甩棍命令在队列中不守规矩的犯人站到讲台前。
二十几个犯人褪去了潮湿的囚裤站成一排,甩棍击打在他们湿润的臀部发出了清脆的噼啪声……
那个8月末的深夜,在一整个无所事事的、夹杂着痛楚的快感的非劳动日,我看够了红色的屁股,并在暴雨之后的深眠之中开始了入狱之后的第一次梦遗。
9月的第一个周末,正午的日光丝毫没有减退,箱包大楼在一场风雨之后被彻底擦亮了。
我和19监舍组长抬着一架电动缝纫机走在恼人的光线中,周围高大的杉木没给我们留下什么树荫。长长的搬迁队伍里,陆续从关停的箱包总厂走出来的犯人面目阴郁,烈日之下似乎找不到一张平静的脸。
我和组长皱紧眉头,笨重的机器令我们汗流浃背,在痛苦的路途中我们彼此咬紧牙关发起了喋喋不休的牢骚,而后又开始了一些无聊的谈话:
“老子还有两年啊,熬不住了。”
“我还有九年多呢。”
“快叫家里人找找关系吧,不然这种日子撑到头你小子就废了。”
“哪那么容易找到关系。”
“有钱就好办。”
……
这些平日里重复过数遍的谈话内容并没有消磨掉任何烦躁的心情,相反还令彼此变得口干舌燥。各自保持一番沉默之后,我们终于搬迁到了服装总厂,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四条繁忙的牛仔裤生产流水线。
布满蓝色灰尘的车间里已经有十几匹牛仔布料正在接受点位,二监区所有犯人在八月末享受的那段休息时间彻底停止,并且需要双倍偿还。
● ● ●
流水线就像一条不可停止的高速公路,任何的疲倦和事故都需要担负惩罚的代价。每天都有赶不上流水线进度的犯人发生殴斗,他们举起凳子,凳子被链条锁紧在机位上,他们又拿起剪刀,剪刀也被链条锁死在机位上。他们举起拳头站进衣槽里扭打,六七个骨干犯一同扑了上去,他们才得以被拉开。
使人发狂的劳动又持续了一周,我已经学会了以最快的速度将牛仔裤的裆部用拷边机缝合。飞速跑完一匹料子仍需要仔细比对编码,我拿起剪刀把连接在料子上冗余的杂线剪断,忽然,剪刀在我自认为熟练的操作中剪破了一沓料子。
我开始惊慌,剪刀瞬间又戳破了我的手掌,血液渗了出来,盐涩的身体让痛感集聚到了伤口的边缘,疼得叫我睁不开眼睛了。
我的后道工序是无期犯陈华伟,他浓密的络腮胡子在大半张油腻腻的脸面上蔓延,每周五他都需要额外领用剃刀才能阻止疯长的胡须。看到我的惨状,他幸灾乐祸地恐吓着我:“新来的,你完了,大队长不请你吃电棍我跟你姓。我的任务也被你害的要完不成了,操。”
他的话音未落,矮胖的小岗就开始喊我的名字,陈华伟听见后大声笑了起来,凸起的嘴唇兴奋而又结巴着喊了起来:“新来的快去快回,电上一次,你他妈以后就不会犯错了。”
我解开一条用来打包裤料的布条,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手掌上的伤口,跟着小岗去了警务台。陈华伟和另外几个犯人抻着脖子冲我送出了狰狞的鬼脸。
警务台上站着一个陌生的狱警,他和大队长正兴致勃勃地聊天。我蹲在他们身旁,直到他们聊天结束。
“你就是夏龙龙吧?”那个陌生的狱警问我。
“是的。”
“你被调到文教监区服刑了,收拾你的个人物品去吧。”
听完狱警的命令,我激动而又发麻的双腿颤颤巍巍地站立了起来,我知道我的幸运日来了,但我被糟糕的日子折磨到来不及感受它。
看着我回去收拾生活物品的陈华伟惊呆了,他厚实的嘴唇不断朝我抛出重复的问题:“你是不是找到关系了?”
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积蓄已久的嫉妒终于在脏话中彻底爆发:“操你妈,新来的有‘条’。操你妈,新来的调去文教享福了。操你妈!”
在他喋喋不休的骂声中,我径直走向了警务台,炙热的白昼已经收敛了最后的触角,九月夜晚的黑暗开始在浓浓的暮风中伸展温柔。我走在幽暗的监狱小路上,听着柔和的晚风吹进了二监区那个在暴躁中被点燃的厂房,然后便遗忘它了。
● ● ●
后记
我被调往文教监区服刑的真正原因大概是:入监个人信息登记的时候,我在特长一栏写明自己擅长美术。
当然,这个原因可能也并不足够令那些劳务监区的犯人们信服。但我并不在意。
编辑:沈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