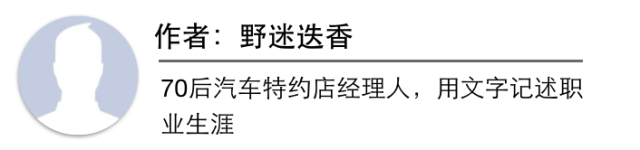《外婆》剧照
外婆熟路而且个子小,像一头小鹿,跳上甲板,窜进船舱到船尾,再跳到另一条船上,几个起落就甩掉了生父,从此断绝了来往。
前言
儿子五六岁时,有时我说他:“真系怕咗你先怕米贵!(广东话,真是怕了你才怕米贵)”
儿子自小受电视机和幼儿园老师的普通话影响,广东话并不灵光,就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我问:“谁是米贵啊?”
这句话,是小时候外婆训斥我时常说的口头禅。
外婆生于晚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本是江门滘头人士,姓赵,是家里降生的第一个孩子。外婆出生后,家里找了算命的看,说这女子命好硬,不能留在家里。家人信了,40天的时候就把外婆送了给了别人。
外婆的养父姓李,外号瘌痢头洪,四会人,住在广大桥,竹排街一带。
江门这地方,因着南边的烟墩山与北边的狗山隔江相望,中间夹着一条蓬江,两座山之间的河道中央有块礁石,与两座山形成门柱、门槛之势,于是有了“江门”这个地名。明清开始便有了商埠,各类货物沿西江顺水而下,就在这里集散。竹排街、葵尾路、竹椅路、水街、卖鸡地、京果街、打铁街、墟顶,都透着浓浓的功能性。
最初,太外公贩竹排到江门售卖,后来成为一名巡城马(曾经快递、邮差的称谓),是货主与店铺之间的经纪人。不久后在江门定居,娶了一个广州老婆。
养父给外婆取名李莲有,是“连有”的谐音,寓意在她之后,能够连续有儿女出生。但这不过是祈愿而已。外婆的养父母先后生了11个小孩,都是长不大的。有些胎死腹中,有些早产,有些出生不久就殁了。11次打击,怎一个苦字堪言。
太外公有个兄弟,英年早逝,留下几个儿子。兄弟过世后,太外公凭一人之力,把几个侄子抚养长大,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他,成为外婆的哥哥,也就是我们的舅公。
太外公在当地人缘不错,每逢中秋,各路货主与店铺送给他的月饼,集中起来可以装满一个糖缸。外婆的整个童年到少女时代,都衣食无忧。
等外婆长大,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跟亲生父母有了往来。十三四岁时,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女孩。亲生父母生了歹心,想绑她回来卖了换钱。
好在生父带人去找外婆时,外婆看出端倪,转身就跑到了岸边的船上。那时,蓬江岸边停满了船,是水上人的家,外婆熟路而且个子小,像一头小鹿,跳上甲板,窜进船舱到船尾,再跳到另一条船上,几个起落就甩掉了生父,从此断绝了来往。
● ● ●
太外公做巡城马虽然成功,但终归是跑腿讨生活的差事。他总想做个老板,平日就留意各种机会,直到认识了新会睦州的一个财主,两人一拍即合,商量各自出资在江门开个店铺。
为了筹资,太外公拿出多年积蓄,还借了贵利(广东方言,高利贷),才终于将股银交予财主的手里。谁知人心险恶,那财主出了阴招,把太外公的钱黑了。太外公因上当受骗,加之以债主催逼,一时想不开,吞鸦片自尽。
那时,外婆已十六七岁的年纪,生的人高马大。她气不过,便上财主的门讨要养父的股银。外婆的不依不饶惹怒了财主,财主拔出一支火枪,要赶外婆走。
外婆嘴硬:“够胆你打死我!”
财主当真朝天放了一枪,震耳欲聋的枪声吓得外婆落荒而逃。
太外公死了,被坑的钱又要不回来。外婆唯有跟舅公一起,用自己双手养活自己和养母。她身高有一米七,手脚粗大,却不识字,只得去做建筑工人。
那时盖房子,已经是用红毛泥(水泥),她在工地做小工,搬运水泥、沙子、砖头上楼。当时运东西要在楼上架一个滑轮,滑轮两头各绑一个竹筐,下面的竹筐装满沙土,高处的竹筐站人,人抓着绳子往下慢慢落,物料便随另一个筐上楼了。原理说起来轻松,但在毫无防护的工地,一个十几岁女孩,干起来也颇为费劲。
外婆去北街的教堂做工是,被作为业主的洋神父看上,想跟她交往。但外婆从未见过红须绿眼的洋鬼子,吓得便逃。
我的外公本姓李名卫,原是广东省南海人士。
李卫的祖父本是当地富户,人丁兴旺,育有七子一女,独女最小。其时,先祖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先祖的子女命格,叫作“七星伴月”,小女为月,照亮七个作为星星的哥哥。这个女儿不能出嫁,若是嫁了,月亮照不到兄弟,家族便会败。
先祖不信,待女儿长大,便把女儿风光嫁了。谁知道算命先生一语成谶,先祖父故去后,家道中落,七个兄弟全部沦落为种田人。
李卫的母亲出自中医世家,自小就在家里学习望闻问切,出嫁前已可给人断症,家道中落后,她平时就在家里帮四方乡亲诊病,帮补家计。先后生下几个小孩,李卫排行第四。
一天晚上,有人来请李卫母亲出诊。因为心急,她想在田间抄近路,谁知却一不小心跌断了脚。脚要医治,一家人要吃饭,万般无奈之下,唯有将十一二岁的李卫卖掉,筹钱治疗骨伤。
李卫被卖去江门一户卢姓人家,改名卢锦庆。
卢家住在江门竹排街附近,做的是撑横水渡的营生,兼着帮行驶在江门蓬江上的火船装煤卸渣。横水渡就是现在的渡船,只是那时还用人力撑船。外公正式入户时,家里已有四个女孩,外公自然加入了拣煤渣的行列。
十五六岁时,家里送外公去木材铺做学徒,三年学徒没有工钱,三年满师后才能成为伙计、师傅。
每年腊月十六,按惯例,老板会请伙计吃顿团年饭,唤作尾牙。团年饭应该是开心的事,但伙计们心里却惴惴不安。特别是主菜白切鸡上来的时候,一个个更是紧盯着老板,心脏跳到嗓子眼。
这鸡当然是分给伙计们吃的,分到鸡头、鸡脖子、鸡爪子、鸡脊背等杂碎的伙计,都满心欢喜,连声向老板道谢。而分到鸡腿、鸡胸肉的人,则神色落寞,因老板嫌你只会吃肉,不会啃骨头,让你明年不用来了。
靠一顿饭,公布明年的人事安排。
● ● ●
经媒人介绍,1925年,外婆嫁入卢家。
由于外公是懂事年纪才买回来的缘故,养母总担心他会跑,所以经常骂他。外婆嫁入门,谩骂多了个缘由,就是外公娶妻借钱,却要养父归还。外婆一直隐忍,直到母亲寻归宿的时候,外婆才表示决计要她嫁个外地人,不受家婆气。
外婆的堂姐是开杉铺的,外公便到堂姐的铺里做了木工师傅。
婚后,外婆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待二儿子出生,外公外婆便搬出去过自己的生活。直到1937年,一切的平静都被打破了。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中一条侵略线路是从海上过来,侵占了广州。一路烧杀抢掠。
闻说日本人来了,江门像被捅的马蜂窝,四散奔逃。外公带着一家五口辗转逃到了礼乐、麻园、外海、中山横栏等地。太外公一个人逃到了香港,此后便没了音信。一家人便在那时失散了。
外公一家在外逃难,人生路不熟,所带的钱银又有限,无依无靠,更加食不果腹,小女儿饿得脚都肿了。那时在江门礼乐,有个姓曾的财主,开了个救济堂救助逃难的小孩。外公外婆便将小女儿托付给善堂,四口人继续逃难。
逃到了中山横栏,两个儿子也饿得不行,无奈之下,夫妇俩把两个儿子留在当地,送给人养。
那时的人,如同洪涛中的浮萍,没有目标,没有明天。
逃难两年后,外公外婆感觉已陷入死亡的边缘,抱定哪怕死也要死在江门的心思,两人踏上了归家的路。
沦陷时期的江门,市面萧条,侵略者的总部设在常安路口一座圆屋顶的三层老建筑内。外婆堂哥的儿子由于懂日语,被拉去做了日军翻译。在他的关照下,外婆堂姐的杉铺重新开张。外婆夫妇便又去堂姐那里打工。
他们先是在浮石路附近租房子住。后又买下一条报废的渔船,拖上岸,在竹排街找块空地固定好,作为新家安顿下来。
那船大约五米多长,两米宽,两头是甲板,中间用木板钉一个船篷,大约几平方,便是寝室了,一家人,便全部躺在船板上休息,在船头、船尾洗衣做饭。
那时江里的水很清澈,挑回来可以直接饮用。遇上洪水,江水浑浊,只要用手捏一块明矾,在水里稍稍转一圈,沉淀完泥沙,就可以用了。
但洗澡和上卫生间就很不方便。始读小学时,总爱丢三落四,外婆经常用俚语训斥我:“屙屎不带棍,出门没贵人。”我一直不明白为何要带棍子,直到问起母亲,才知道棍子乃是清洁用品,与贾平凹小说里,陕西人民用瓦片、土疙瘩是一个道理。
这条船,一直作为外婆的家,直到1973年我出生后,外婆到我家,才将船转让给了老邻居。
● ● ●
局势稳定后,外公外婆便想着去找失散的三个儿女,但全然没有音信。
不幸中的万幸,是卖到了中山横栏的二儿子失而复得。我二舅一到买主家,只懂得日夜啼哭。买主也不忍心,于是当局势平缓以后,就上门把孩子送回。外公外婆千恩万谢之余,对二儿子格外珍贵,还送他到东海里的私塾读书。
生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突然有一天,二舅得了类似急性尿道炎的病。当时缺医少药,唯有求助于神婆。神婆说,小孩在私塾坐的座位,以前有死去的小孩坐过,现在那鬼魂回来催还位置。只要喝了她给的符烧化的水就可保没事。现在看来,这一切很无稽,二舅喝了符水,反而雪上加霜,很快便夭折了。
在这样悲痛的氛围下,大姨出生了。大姨原本行四,但是留在身边算是老大,她的降生点燃了外公外婆生活的希望。
那时,常有日本兵在附近巡逻,他们看着大姨可爱,抱起来玩,抛上抛下。有时喂她喝牛奶,但是大姨喝了就吐得满身都是,哇哇大哭,日本兵看着却哈哈大笑。外婆在一旁敢怒不敢言。
终于熬到日本人投降撤离,满江门的人都上街去看,沿路向他们扔垃圾。当年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在这天像只丧家犬一样低着头灰溜溜地离开。做翻译的亲戚一早便跑到了香港,从此没了联系。
光复之后,没过几天太平日子,又开始内战。
江门并没有被战火波及,但生活却大受影响。那时国民政府财政崩溃,金圆券疯狂贬值,朝不保夕。所有人都充满对物价飞涨的惶恐不安。一到发薪日,外公外婆就立刻去买米,买副食,如有剩余,就去买金器,买最小的耳钉,然后累积成耳环、戒指。
计划比不上变化。很快,一麻袋钞票就换不了一麻袋大米了。
那时,外婆最怕的就是米贵(米价上涨),一旦当天发的工资到手贬值了,买不够米,一家人就要挨饿。所以才有了那句口头禅:“真系怕咗你先怕米贵!(真是怕了你才怕米贵)”
1948年,母亲就在那动荡的年月降生。1952年,小姨又出生了。
解放后不久,外婆堂姐的杉铺公私合营,和其它几家木材店一起成立了木材公司。外公就成了国营厂的工人,而外婆也进入到竹器厂做了搬运工。外婆虽是女人,却顶一个壮劳力,跟搭档一起,两人一组,每天把河边的竹子抬到厂里进行加工。工作辛苦,但搬一根算一根的钱,按劳取酬。
1959年大跃进以后,城里所有物资实行补给制,凭票供应。但也有农民把自己种的精米、瓜果,榨的花生油、养的狗、鸡鸭和晒的腊肉拿到黑市上卖,外公外婆就是黑市的常客。
所幸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期,一家人生活还是温饱无忧的。
● ● ●
1962年,外公到北街加班搬运木料时,脚踩进了两块木料中间的夹缝中受伤。不过活儿不等人,外公没有休息,第二天脚就肿了,疼痛不已。那时外公也没看医生,只是拿点药酒揉搓一下,却不见好,脚越来越肿,脚脖子像大腿粗,很快人就去了,享年53岁。
家里顶梁柱没了,那一年,外婆55岁,大姨18岁,我母亲14岁,小姨9岁。人生三大憾事: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外婆占其二三,这打击可想而知。
外婆老年时,有句口头禅天天说:“真系前世唔修(广东话:真是前世不修)”。意思应该是:前世不修,今生来受。每逢遇到不如意的事,例如洗碗打破了碗碟,便会说上这一句。
外公走后的第三天的晚上,是鬼魂回家的日子。一家人都躺下了,外面还点着香祭奠。忽然间,整个船的甲板都在抖,船篷砰砰作响,外面的锅碗瓢盆也跟着响动。四母女吓得缩作一团。外婆念叨:“有什么话,你交代就是了,别吓人是啊。”念叨完,船也安静了。
到第二天,邻居们说起来,才知道是发生了地震。
外公去世后,十四岁的母亲便正式开始工作。大姨干了一年多临时工后也嫁了人,紧接着就开始十年文革。
那时小姨刚好十五六岁,街道的干部便上门动员外婆送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外婆开始不愿意,但随着干部上门的次数多了,以及附近邻居的孩子都被动员走了。外婆担心不送小姨去会被定为典型,只得忍痛点头。
当年由于要破四旧,不能回家过春节,小姨下乡一去八年,如同剜了外婆心头一块肉。从我记事开始,外婆和人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小姨下乡让她哭尽了眼泪。
文革后期,母亲23岁,外婆就委托周边的人帮忙介绍对象。父亲出自粤西北山村,淳朴老实,当过兵,还是公家单位,1.65米的个子,长得还算精神。外婆一下子就相中了。
父亲自己一个人在江门,认识母亲后,就把外婆家当成自己家,发的肉、鱼、粮油全部拿给外婆,外婆自然满意,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了。母亲说,到登记那天,她才知道父亲的全名。
父亲的婚房是找武装部老领导安排的,20多平方,一室一厅,带厨房的公租房,在当时是科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1973年我出生,外婆过来带我,之后就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
1977年1月,历经八年下乡再改造的小姨终于回城了,现在想来,1973年到1984年那段日子,应该是外婆一生最好的岁月了。
外婆有两个嗜好,一是抽烟,二是看戏。她抽的是用竹子做的水烟筒,叫大碌竹,抽起来隆隆作响。我父亲不吸烟,别人送他的烟都拿回来给外婆,外婆抽了,却说不够劲,要自己去买烟丝。那时,一条路上许多摆地摊的烟丝档,外婆全部试过,哪些够劲,哪些比较淡,哪些被石灰水泡过,她了如指掌。
外婆爱看戏,源自于小时候,她舅舅就是撑戏船的。那时,有钱人庆祝喜事,都是搭戏棚请戏班演出。戏班都是住在戏船上,去哪演出船就撑过去。外婆每逢有演出就去看,从戏班开锣看到收锣。
每逢大戏开锣,外婆中午就带我到了小吃店吃中饭。当热腾腾的云吞、面端上来,我吃得猴急,汗就冒出来了。外婆一向对我都有点凶,这时却总会温柔地给我擦汗,说:“吃人家的吃出汗,吃自己的吃出眼泪。”意思是,做人不要忘本,要懂得孝道。
那时小小年纪的我,很认真地对外婆说:“阿婆,长大了,我请你吃云吞。”
● ● ●
1984年,我小学四年级。外婆晾衣服时不小心摔倒了,造成盆骨微裂,不能行动,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勉强可以坐起来,但还不能下床。
一天早上起来,外婆并没有如常醒来,连母亲晃她都没反应,叫救护车送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中了风。住院几天后,医生对母亲三姐妹说,外婆已是植物人状态了。
回了家的外婆,保持着呼吸,但不能说话,也不能睁眼。看着身材高大,声如洪钟的外婆就那样无声息地躺着,我心里念叨她何时才能好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房间看电视,大姨夫妇过来看外婆,大姨父忽然说,“好像不对劲,”随后传来母亲的哭声,接着父亲进来,对我说,“不要出去”,我楞在那里。
跟外婆的最后一面,是在追悼会,当看到躺在玻璃棺中的外婆时,我一下子哭了出来。
阿婆啊,我还没请你吃云吞呢。
外婆去世不久,爸爸就分到了新的房子,两室一厅,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只可惜劳碌一生的外婆,无福消受了。
● ● ●
后记
儿子现在长大了,有时去爷爷奶奶家吃饭,我说他几句,他就回嘴道:“知道了,你好烦啊!怕了你才怕米贵。”他爷爷奶奶听了,都笑了。
外婆出生于1907年,儿子出生于2008年,相差近100年,一句口头禅却不经意间传了下来。但这背后的故事,如果不动笔写下来,或许就泯灭了。
编辑:侯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