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飞力笔下的中国有多个面孔,有站在现代国家起点上的中国,有叫魂恐慌笼罩下的中国,有乡村治理失序的中国,还有“兵为将有”中央权威旁落的中国。然而回望孔飞力笔下久远时代的中国,人们并不感到那是遥远的存在,甚至可以说那个“中国”所面临的核心命题与挑战,和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距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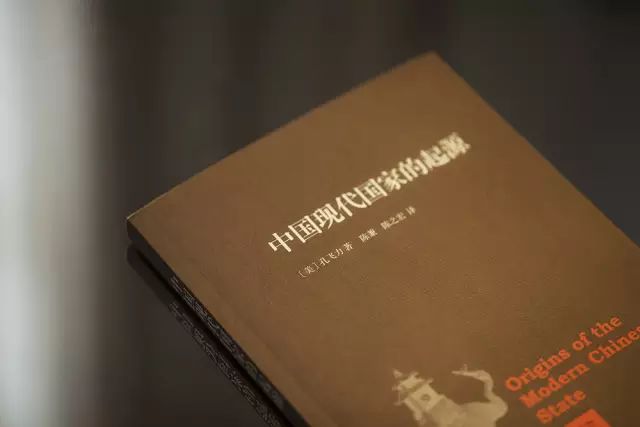
当然,孔飞力本人对这一局面早有预见,因此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导论里指出,虽然中国面临的“根本性议程所用语汇改变的同时,其内容也跟着时代的演进而得到了更新,但其中所包含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紧张却并没有获得解决,并一直存在到了今天”。
其实除了没有获得解决的“紧张”,议程内容本身也很难说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更新”,比如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理顺央地关系、促使官僚体系有效运转,以及如何满足人们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热情,等等。
以三农问题为例,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所给出的解释似乎依然适用于今天:以沿海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导致精英从农村单向流出,而“那些投身于城市生活中现代化部门的名流发现他们难以再与市镇和县城的现代以前的文化保持关系”,因此很少能在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方面有所作为。
在《叫魂》里,乾隆皇帝以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制度化的非制度化来推行王权政治,推动陷入怠政惯性轨道的官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运转。他热衷于以各种临时性的组织安排来凌驾于既有的规章制度和架构之上,这其中既有先帝爷们的政治遗产,比如以军机处和上书房来代替六部,以专折密奏来补充正常的信息收集渠道等,也有乾隆自己的即兴创新。这些上与下的种种离心离德和钩心斗角耗费了巨大的行政能量,然而同时也对帝王的偏激行径发挥了某种抑制作用。
《叫魂》同时提醒人们,经济上行时的种种制度自信,如何在下行时发生异化,一个内心深处不自信而又执迷于盛世图景的帝王会以何种偏执的方式进一步收紧原本也不宽松的政治缰绳,进而全面压缩民间舆论的空间。
略微让人心安的是,除了这些所谓的根本性议程,至少当年中国所面对的紧迫性经世命题如河务、盐务、漕务、银务、夷务等都已不成其为问题,卫星已经上天,航母业已出海,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早已一日千里。然而如果把以上各种经世命题替换成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粮食安全、人民币汇率、中美关系等等当下的议题,则很难说拥有着巨大的现代科技、财政和组织资源的我们就比魏源时代的人们做得更好,种种政策的推出同样需要在更好地集思广益、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方面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而猴年新春前后一系列为人所热议的时政话语,比如凋敝的乡村、某省干部组织学习大清相国陈廷敬、六尺巷的传说等等,更是提醒着人们两个“语汇”场的高度可沟通性。因此阅读孔飞力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挥别感,反而有一种检阅当下的应景之感,虽然这种应景之感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违和感。

事实上共和国的语汇场从一开始就不乏对满清的借用,且发端于官方话语,比如关于高级干部不得腐化堕落为“八旗子弟”的说法,比如“文革”期间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因“风庆轮”事件被戴上洋务派的帽子,至于以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驯服或激活失去革命激情甚至有了自我利益的官僚集团,更是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回响着《叫魂》中的核心命题。而当时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过激行为在海外媒体及学者的笔下则被描述为类似义和团的行径。
更令人尴尬的比附来自于法国学者佩雷菲特,他在《停滞的帝国》一书描述了马戛尔尼的访华历程,在书的导语中他以亲身经历指出70年代末期的中国与马戛尔尼眼中的帝国惊人的相似性:巨大的人口压力、严密的社会控制、自负与敏感交错的心态、对借助于外部资源实现现代化的向往及恐惧,而不定期举办交易会的广州则让人想起当年十三行的角色。
随着历史的演进,穿越式的借喻也渐次展开。改革开放之初的地方大员的危机意识、积极性和务实的行动能力,再次令人想起洋务运动的中兴能臣,而沿海开放地点选择带来的关于租借地历史的回忆及其引发的质疑,让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高层领导不得不亲自出面加以“辟谣”,而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共领导层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异常坚持。
此后改革开放的推进也一直不乏清史语境的陪伴,从民间热捧的刘罗锅、纪晓岚系列,到官学两界津津乐道的康雍王朝剧不一而足,你尽可以批判其中折射的清官英主情结,但其市场斩获和政治安全确保了清宫剧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产业。时至今日,除了江湖依然热追清宫剧之外,庙堂也开始组织学习清宫题材的文学作品,而朝野在涉及反腐等话题时对晚清人物和语汇的借用,更有自成一套政治学符码之势,不免让人偶生时空错乱之感。
在所有这些比附之后,某种程度的沮丧感不由得油然而生:为何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如此漫长且循环往复?或许答案就在于孔飞力对所谓“现代”和“中国中心史观”的误导性界定。欧美学界对多元现代性和去欧洲中心论史观的强调离不开1980年代的国际大背景,当时东亚模式勃兴和冷战渐至尾声,令欧美学术界追求一种更为包容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叙事,从而可以涵纳日本、四小龙乃至中国大陆的非西方传统模式的崛起。
在这样一种摆脱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叙事框架下,东亚现代化的自主性被强调,而其展开的时间也因此而发生前移。这样一种表面上更为强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内部史观”的表述,其实往往带来另一种扭曲。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为例,孔飞力以对所谓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设置来界定中国“现代国家”的展开,貌似在努力寻找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历史演进的内在机理,其所借鉴的脚本其实依然是英美所谓“不成文的宪法”或“看不见的宪法”这一学术范畴,其对魏源等人试探性地扩大“文人问政”的尝试,多少有着过誉和拔高之嫌。如果和我们的时代加以比较,会有一个吊诡而尴尬的发现:魏源们试图通过不成文的宪法来拓展参与,而有着成文宪法的人们,其政治参与却往往要通过不成文宪法规定的方式来实践。
去欧洲中心史观的矫枉过正,后来被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继经济崛起后的民主化浪潮有所纠偏,至此人们发现过于强调亚洲的另类现代性不仅混淆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区隔,过度拔高亚洲经济层面现代化的自身特色,而对亚洲政治现代化的普世性面向关注不足。
这种维度的解释或多或少让我们有些释然,或许我们“现代”的展开并没有那么早,因此也就没有那么漫长,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足够的耐心和勇气;同时也充分表明过于强调自身经验的特殊性,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自信和抗拒历史潮流的表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任务和挑战,抛开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机械界定,一个有弹性的、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制度并不仅仅体现在把前人所没能完成的任务给完成了,而是能够持续高效地应对新挑战。在这方面,孔飞力有着自己的乐观期许:“也许,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重新得到界定,而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也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
斯人已逝。斯言也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