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2月12日晚,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印尼病逝,享年79岁。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森出生在中国昆明。
▲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格曼·安德森(1936年8月26日-2015年12月12日)
安德森因《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而广为中国学界所知。我也受益于他的著作。
第一次读到安德森为“民族”下的定义时,我先是一愣,跟着一冷,因为它与我熟知的官方说法完全不同。安德森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民族竟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可是,民族难道不是我们与生俱来就属于的集合?它的历史难道不是坚固如磐石?

《想象的共同体》的中文译者吴叡人评论说,安德森大胆使用了一个主观定义,将民族置于集体认同的面向,从而聪明地回避了寻找民族“客观特征”的障碍。“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集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想象的共同体”指涉的并非“虚假意识”,而是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
安德森进一步揭示说,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因为民族的想象和个人无可选择的种种事物(如出生地、肤色、语言等)密不可分。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自我牺牲。民族主义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不会改变它的“官方性格”,也就是某种发自国家,并以服务国家利益为至高目标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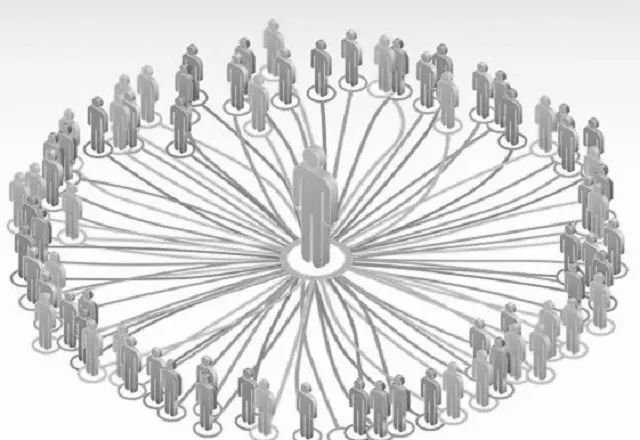
安德森的著作富含创见,但也有缺陷,他将民族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忽略了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的政治过程。
不过他的著作已赋予我们灵感,使我们能够勇敢而不冒失地去探寻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所归属的民族,是如何被想象出来的;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据近人于省吾在《释中国》中的考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出土文物支持了于氏的考证。目前“中国”一词出现的最早证据,是1963年陕西出土青铜酒器“何尊”上的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大意是说周武王攻克商的都邑以后,举行祭天仪式,报告上天:“我已据有中国,从此统治这些百姓。”而在《尚书·梓材》中,也记载了周成王的话:“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大意是说上天既付与人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作为天子就必须惟德是用。文物与文献,均证明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已使用“中国”一词了。
“中国”的本义,是指上古部落首领居住之都邑,后来渐渐扩大到以都邑为中心的地区。东周以降,由于周天子式微,诸侯崛起,“中国”将诸侯国也囊括在内。及至秦始皇一统天下,汉继其疆域,“中国”的范围就又扩大了。如学者葛剑雄所言:“秦汉疆域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不断变化和扩大。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戎、蛮,就不是‘中国’。‘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比较偏远的地区看成非‘中国’。”
“中国人”概念的出现,却要晚得多了。日本学者冈田英弘甚至认为,在宋朝以前,没有“中国人”概念。秦朝的人是秦人,汉朝的人是汉人,三国的人分称魏人、蜀人、吴人,晋朝的人则是晋人。人的统称依照王朝之名,个人属于皇帝,而无种族概念。直到宋朝,汉人在暌违数百年后统一中国,却又立即处于游牧帝国契丹的巨大压力之下,才有了“中国人”这一种族概念。
有种族概念,并不意味着就有民族观念。依照安德森的看法,民族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与北美产生的现代事物。学界一般也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至早不超过晚清。
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是没有什么中华民族的。埃里·凯杜里认为,国家先于民族。国家通过经常性的集体教育,在公民心中种下民族同一性意识,以使公民愿意成为国家的一员,保证拥护国家。然而,一种需要灌输的情感,不可能是自然的,如果灌输者是国家,民族就不可能先于国家。沃勒斯坦更进一步断言说,国家不仅先于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出现的不可缺少的先期必要条件。
在我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既有现实政治建构,也有古老传统影响。
古老传统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主要是正统论:1、夷夏之别。2、大一统。
夷夏之别的观念先秦就有了,以华夏自居者膨胀自大,对异族充满蔑视,但没什么仇恨。大一统观念也在先秦就有了,《诗经》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所谓“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荀子所谓“四海之内若一家”。到了秦汉,经由李斯与董仲舒,大一统观念更加圆熟,但它真正深入人心,也许要到宋以后。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都努力阐释发扬“正统论”,不过他们更注重纯正道统与政治统一,对种族差别似乎不太敏感。经历蒙元入侵,到明太祖《论中原檄》,夷夏之别与大一统再次被同时强调,并且发挥到极致。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关系甚大,1949年后又被共产党人注入新的意味。其实依照早期共产主义学说,民族主义是应该被勾销的选项,共产主义要完成的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而不只是某个特定民族的解放。不过1949年后,共产党人对民族主义大多数时候是利用而非排斥,1980年代之后更借助传统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使民族情感深入人心。(这里我参考了《罗贝尔辞典》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它将民族主义分为“民族情感”与“民族自治”。前者是热爱自身所属民族的特色和传统而产生的眷恋之情,有时伴以仇外情绪和孤芳自赏;后者是一种政治学说与政治行动,目标是争取民族自治的诸种权利与自由。转引自A.D.史密斯《论民族与民族主义》)
当代关于中华民族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形塑的。通过主流的学校教育、学术研究、新闻出版、影视文艺、博物馆、纪念碑、纪念日及仪式等,强调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在近代因为落后挨打又因为挨打而更落后,是共产党救了中国,如今正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同时,仇恨也安置在民族主义情感之中——“近代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亡我之心不死”、“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唱衰中国”……我们恨美帝,恨“日本鬼子”,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教育的结果。只是,我们却很少恨俄国人。
这就让我们的民族主义变得爱恨交织,一方面我们爱想象中的民族,爱中华文化与大一统,一方面我们又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深刻警惕、不无厌恶,甚至恨之入骨。
民族主义让人们产生同胞情感,国家可以藉此动员人民效力乃至牺牲。人们沉浸在民族“过去”的荣耀中,对“现在”相对忽略或麻木,因此失去反思及挑战的能力。当人们夸耀五千年中华文明灿烂、地大物博时,很可能会忽视眼前的苦难,不去探寻这些苦难的现实根源。人们眼中常含泪水,仍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当然,民族主义也有其积极一面,它可以在政治上把分散的个人组成一个共同体,赋予他们一个远古起源,一个共同祖先,一个共有的历史过程,一大堆共享的神话和象征,一个共面的未来,以实现自决和自我治理。不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也许还是消极成分更多,那就是通过一系列二元规则(自己/他人、朋友/敌人、纯种/杂种等),塑造出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制造与其他民族对立/否定的关系,同时将民族忠诚摆到高于一切的地步,说服公民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而融为一体之后,个人命运有时自然会被省略。
任何一种民族主义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学者王赓武发现,当代中国人除了被20世纪的革命遗产所塑造,也被古老风俗的碎片所吸引,这些东西又以各种方式与自由多元文化及正在扩张的全球消费文化混合在一起。
去世前一年,安德森到清华大学演讲,他说在民族主义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他。第一个困惑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你可能会给出反例来否定这个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确实都会对自己的国家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念。第二个困惑是,人们无论来自欧洲、美国或亚洲,都会提出这种疑问:我的国家所做的究竟是对是错?不过这意味着,无论你的国家是对是错,你依旧热爱它。
安德森去世前为之困惑的问题,在我们这儿似乎还没能进入问题之列。
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雷南说,民族是共同拥有历史记忆、也因此希望共享现在与未来的一群人。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历史记忆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共享的现在也许是黯淡的,我们希望共享的未来,则是扑朔迷离的。

【注】本文发表时有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