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孔飞力反复申明,中国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不应该以西方视角来观之,它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国的“反应”,而是中国自身的、内部的问题。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巴黎的讲坛上,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模式,来探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能否采用真正的中国内部视角是可疑的,但是孔飞力确实提出了真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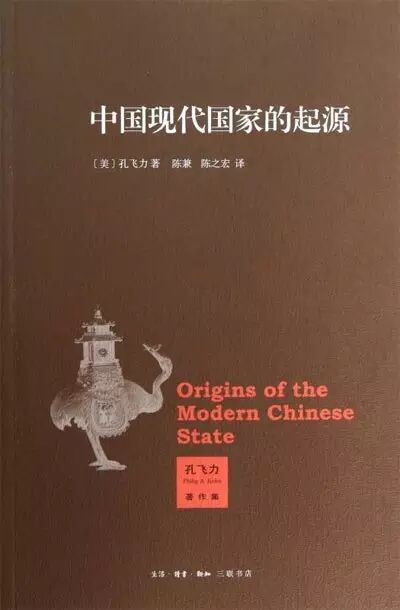
他要探讨的核心议题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其中,第一个问题最为关键。乾隆统治的末期,中国已经危机四伏:经过长期的和平后,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极限,开荒导致环境恶化,最终洪灾连连;贪腐现象极其严重(和珅把持朝政),人们怨声载道。孔飞力认为,即使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这种内部危机,也足以产生现代性议程:一个“文人中流”阶层,要求扩大政治参与,而全国性的危机,又要求中央政府加强权力,两种倾向有着内在的张力,而这也成为中国自晚清以来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所谓“文人中流”,是指一大批通过了县级院试的生员和省级乡试的举人,他们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是却没有机会做官。以获得举人身份的为例,全国就有一万人左右,其中八千人会每三年一次前往北京,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会试。当然,通过考试并有机会做官的少之又少,绝大部分是徒劳奔波。
这是一个独特的精英阶层,他们在文化和认识水平上,并不比那些官员差,但是却由于运气或者人脉的关系,只能做纯粹的读书人。他们称得上是中国独特的“知识阶级”:在漫长的读书生涯中,他们所阅读的典籍是一样的,他们拥有儒家的政治抱负,关心“天下”。去北京考试,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交际,他们了解全国性问题,并且还同其他对全国性问题非常关切的人有来往,这让他们知道,自己事实上属于一个“共同体”。
孔飞力认为,尽管不能做官,很多文人还是利用自己的功名地位,转而“在官场之外投入了广义上属于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地方社区,文人们一般都会从事代理税收和诉讼活动,尽管这些并不“合法”,却仍是官方所默许的。另外,他们还从事一些官方鼓励的活动,比如编篡地方志,促进或维护地方文化事业,这样的机会唾手可得。文人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是“准政治性”的,他们是官方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尽管一直都是“中央集权”,但政府的权力并未真正掌控到底层的农民,对地方官员来说,要进行有效的治理,保住官位或升迁,就必须依靠广大的“文人中流”。
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冯桂芬,他们都靠自己的著作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
孔飞力认为,魏源是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扩大政治参与”的主张,“智士之同朝也,辙不必相合;然大人致一用两,未尝不代明而错行也”。魏源的看法是,政府若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需要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相互之间展开竞争。真理来自于不同观点的冲撞,让人想起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的“言论的自由市场”。但是,很明显魏源并不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君主权力,而是相反,他渴望能有一个更强硬、更严酷的皇帝,来进行更有效的统治,从而应对晚清一盘散沙的政治局面。
▲清末思想家魏源
相比之下,比魏源晚生15年的冯桂芬更进一步,提出了由下级官员选举上级官员的想法,“千百人之公论”应该成为衡量官员是否有为官资格的标准。冯桂芬的方案是,六部九卿这些中央部委官员,应该有下级官员来选,而地方官员,则由那些生员和举人(也就是“文人中流”)来选,很有一些议会制的味道。冯桂芬为了躲避太平军而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当时的上海,已经被迫“开放”,冯的想法,很明显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魏源和冯桂芬的主张看做是一股要求“政治参与”的潮流。晚清危机深重,尤其是外敌的不断侮辱,让广大的“文人中流”深感不满,对朝廷的各种指责当然就多了起来。和大搞文字狱的康熙比起来,他的后辈对社会的管控力大为下降,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让满清统治者不得不对外依赖洋人的武器、对内又必须依赖曾国藩这些地方大员,言论控制能力大为减弱。“政治参与”如果进行升级,就是分权和民主,这确实是“现代”的。
但是,从魏源到冯桂芬,很明显都还处于“参与”阶段,没到吁求民主的阶段。“文人中流”们有参政议政的冲动,或许也有“联合”的冲动,但是他们却很难真正联合起来,发展成真正的政治力量,他们害怕的是一个“党”字。
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来说,“党”是一个敏感字眼,也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字眼。《论语》中孔子就告诫:“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党”和“群”都是一种联合,但是却有着本质区别。“党”不但要求其成员有共同的主张,还要求成员互相支援,这是一种更有机有力的联合,因此,“党争”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高压线,是皇帝最忌惮的。党争是导致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清朝的统治阶层中是一个共识,在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文人在政治上的结合被指控为党争,会受到坚决镇压。因此,要联合起来,精英阶层(当然也包括官员)“要克服自己根深蒂固的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的冷漠,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33页)。对魏源和冯桂芬来说,要处理的就是联合的边界问题,“党”是他们绝对要避免的。
从魏源开始,一方面,“文人中流”们对政治参与有着越来越高的热情,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尤其是于外国交战的需要,又要求国家权力更强更集中,这是一对长期的矛盾,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李鸿章,他在上海对冯桂芬很不错,但是他又是强烈反对冯桂芬“选举官员”主张的人。
对体制外的“文人中流”们来说,他们政治参与的高峰,无疑就是康有为策划的“公车上书”事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触碰到了知识阶层的底线,因此,大量的举人聚集到北京,要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历史教科书中的“公车上书”大意是这样:康有为获悉清政府要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名举人到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5月2日,各省举人排着长队到督察院呈递,而督察院借口皇帝已经在合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维新改良的纲领……
但据现代史专家姜鸣先生考证,这是一个大大的谎言。据他实地测量,松筠庵的小院子根本容不下一千多人聚会。“万言书”在上海以小册子出版,附上了支持上书的举人名单,不过六七百人,这些人有可能是松筠庵聚会签到的名单,是否签在了万言书的原件上也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根本没有把万言书呈递给督察院。不同的资料都证实,5月2日的集会,到会的举人们大多认为局势已经无法挽回,最后放弃了上书这个想法(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
▲当代画家想像中的公车上书
历史真相可能更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表面”的结论:“文人中流”最勇敢的一次联合,不但在人数上有“虚报”的成分,就其行为来讲,也不过是在一份万言书上签字而已,而且这份万言书最后还没呈给最高统治者。这有可能是理性分析的结果(呈上也没用),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在作祟。这也说明,在晚清的体制内,要做到真正“现代”的革新,是根本不可能的。光绪帝非常喜欢冯桂芬的著作,他向大臣们推荐,并让他们写出读后感。孔飞力很独到的一点是,他没有仔细分析冯桂芬的观点,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那些大臣的“读后感”上,他发现,这些人大都持非常激烈的反对意见。
或许正是既没有纵向的通道(当官),也没有横向联合的可能,才导致了“文人中流”们的现实主义选择。他们和地方势力结合起来,除了当幕僚以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事的其实是危险的行当,比如代收税款,这最终让他们与地主和胥吏(听命于县衙的基层办事员)一起,成为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地方势力不但不能解决晚清的难题,而且本身就成为晚清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这样,“文人中流”要求政治参与的问题,就和孔飞力所要讨论的第二个命题“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交织在了一起。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地方精英有自治的需求(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而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多数人都渴求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集权)。这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仍没有办法越过地方精英,彻底掌控农村的资源。直到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不但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清除了乡村社会种种地方势力,权力才抵达到每一个人。
当然,这时已经没多少“文人中流”,在科举制度废除(1905)后,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过去的生员、举人,成为遗老,本身就早已日渐边缘化了。“文人中流”有了自己的现代版,知识分子,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