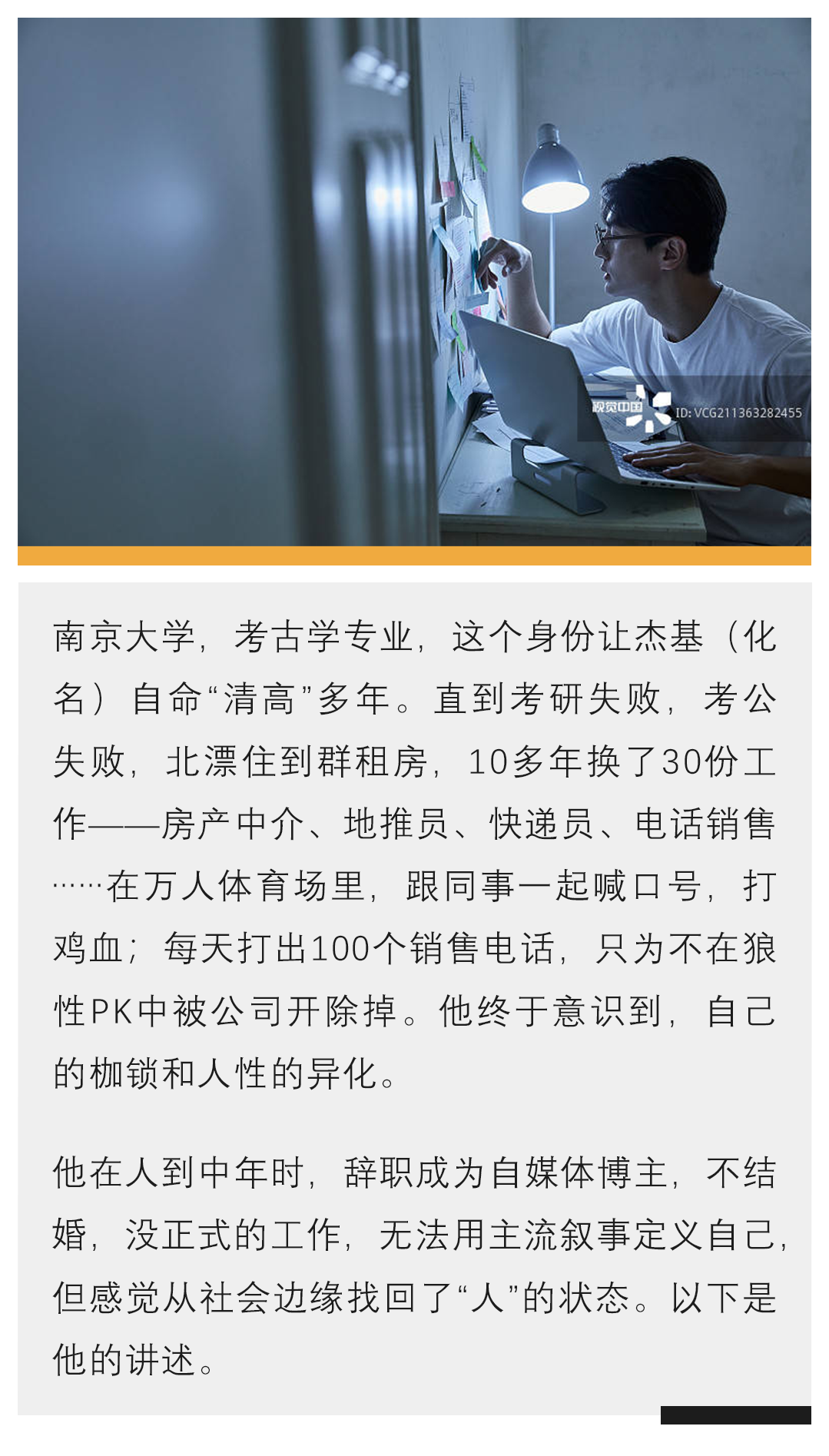
文 | 解亦鸿
编辑 | 毛翊君
身份枷锁
最后一次辞职是去年7月。那会儿疫情居家办公,我这个人力总监做成了裁员总监,批量地辞退别人,干的全是脏活儿,还被欠发工资,觉得自己像狗一样,就把公司给告了。那会儿也33了,感觉到35岁危机,一冲动,主动离职“退休”。
在这之前七八年,我都在各个金融公司、互联网公司做人力相关的工作,招人、裁人、代表公司参与仲裁。招人的时候,我要给人家画饼。裁人的时候,我又要跟人家说,这家公司多么多么不好。
我面试过许多应届生,总会问到他们未来的规划。其实这是一个无聊又无效的问题,却成为面试中常用的提问套路,他们也会用学来的套路回答,重复讲对工作和职场的粗浅理解,我就想起以前的自己,如何肤浅,天真,喜欢投机,又怎么面对失败、自处,再陷入虚无。
2012年毕业时,家里不巧欠了债,非常缺钱,为了快点找着工作,我在北漂前就先投了几家公司,攒了好几个面试,结果发现流程都很漫长。唯独房产中介不是,面完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进去一看,大部分同事没怎么上过学,总监冲大家说:“我们有一个新同事,是考古学的毕业生,可见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蓬勃。”
我读的是南京大学考古系,因为当初觉得自己喜欢历史。上学时,我从不和同学讨论就业跟出路,假装不想挣钱,只在乎学术理想。然而在这第一份工作里,被带着喊“挣钱!”“挣一百万!”“成功绝不容易,还要加倍努力!”我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第一天就想跑路,但是家里也没钱供着我,不想灰溜溜地回去。
其实,在大三去汉江边的考古工地里实习前,我就意识到,专业跟我的兴趣有偏差,考古研究物质文化,需要反复摆弄挖出来的瓶瓶罐罐,分类、写报告,很枯燥。但临近毕业,我还是选择考研,报了北大考古系。因为班里几乎都被保研了,我不考,那不是低人一等?对不起自己上的这个985?
最后,内耗、失眠,没考上,只能去工作,也不知道想干什么。迷茫中去了南京一家出版公司做教辅编辑,和我同批次入职的有南大、东南大学、武大的,9个985聚到一起,又开始互相比较,说自己“其实还拿了某某offer,但是这里工资给的高,所以就来这儿了。”
我很快对没完没了校对高考题感到窒息。强撑到了第四个月,老板突然在周末让我们去仓库一起搬书,没加班费,工人讲话还很不客气。我觉得自己一个985毕业生却不被尊重,跟对方吵起来,差点打一架。就这样,马上辞职,接受了爸妈说的回家参加公务员省考。
我根本不想当公务员,但辞职的时候想的是,“老子不伺候你们了,我以后是公务员,不会在你这个破地方受这气。”备考又重复了考研的状态,甚至更痛苦,胡思乱想:当年考了个好大学出去了,现如今又跑回来考公务员,是不是没出息?难道活着就为了图个安稳体面?可又没退路。
我父母都是体制内的,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一眼望到头。最后,考公的成绩我至今都没有去查。消沉了半个月,决定重新回大城市找工作。我爸只给了我1000多块,我也不好意思索取更多。
那几年,除了这传销一样的公司,我还做了一个月地推,每天在街上给陌生人推广APP,让他们扫码下载,还要在身上挂一台录像,把自己去过哪里都录下来,好让老板监督你有没有摸鱼,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就立刻跑路了。又送了一天快递,一单只能赚几毛钱,第二天我就开始躲活儿。
我逐渐明白,自己当初不愿意放弃的,是一种“身份”。不读研,我的身份就变得比同学差了,失去了优越感。表面上考虑的是“理想主义”,实际上是“面子”,我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清高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那些思考就业、挣钱的同学才是俗咖,是不纯粹的。
“清高”是一种身份的枷锁,带来“我不能被落下”的焦虑。但是在学生年代,我很难意识到这些,扔掉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为了赢
在最初的工作里,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学到。领导教了我一种作业方式叫“集攻”,一个月不到,我开单了,提成赚了3000块。我立刻在想,这是不是有戏?
这操作就是,每周挑一天晚上,拿出某个楼盘的业主资料,集中给他们打电话,而且语速要快,语气要表现出癫狂:“请问您要卖房吗?!”有时业主会骂我,“你神经病吧!”这时就赶紧换一种话术:“那xxx的房子您要买吗?”
公司每天给我们讲“吸引力法则”,很多同事真的信这个,开工前给自己打鸡血,把嗓子都喊哑了。有一次公司租了北工大的体育场,给全体员工开季度会议,上万人一起在体育场里喊公司口号:“超越巅峰,挑战极限,坚持不懈,直到成功!”会场里的吼声震耳欲聋,排山倒海,我也跟着喊。
很多人问我,你一个985的毕业生,在那个环境里,会觉得荒诞吗?或许有那么些个瞬间,我会觉得荒诞,但这会一点点淡化,大多数时候我的感觉恰恰相反,那种荒诞变得无比真实,它就是我的处境。我思考的是很实在的问题,比如“每天这100个电话怎么能少打几个”“怎么快一点开单”。也许学历并不会塑造一个人,环境可以。
开会时,领导反复提及一个成功案例,女孩大概姓“陈”,在公司里做了个佣金100万的单子,外号“陈百万”,领导以她为例鼓舞大家。听的次数多了,我也开始幻想,我是不是也能挣到大钱呢?
公司会给业绩好的员工进行“加冕”,有次会务组悄悄把排名第一的区域经理妈妈从老家请来现场,他特别惊讶,跟妈妈在舞台上拥抱,发言感谢,哭得稀里哗啦。就算他原本可能反感这个仪式,但是当他在聚光灯下被嘉奖,被注视,被充分肯定,这种凝视给人的冲击太大了。
但那个季度,我们组的业绩很惨淡,在月会上得到的是“负激励”。业绩排倒数的三个店长,同样被拉到舞台上,特写灯光打在他们身上,背景音乐播放刘欢的《从头再来》。台下所有人看他们如何被羞辱。
我心情特别低落。我一直很想拿下大单,给家里还钱。有段时间,我疯狂地去看各种大标的,我也要做“李百万”。但一个客户也没有。我后来才知道,看的那根本不是什么大标的,项目运作方就是利用转让这种方式,利用中介,来给一个有问题的楼盘带客户的。
散会之后,刚被羞辱完的店长也一脸丧气,他却还想拉着我们加油打气,号召我们再喊一遍口号。我当时就怒发冲冠,真的受不了了,我说,“你他妈别喊了,都这么惨了,为什么还在打鸡血?”第二天,我提了离职。
在类似工作中折腾了大概两年,我找到一个相对白领的工作,在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做管培生。入职后才知道,这和房产中介的“集攻”差不多,其实是做电话销售,邀请教育产品入驻我们的线上平台。
老板搞出狼性竞争,让第一届和第二届管培生之间小组PK,比谁每天的邀约入驻数更多,输了的那一组要内部投票选出一个员工,当天就把他开除离职。为了赢,我每天打100个电话,跟打了鸡血一样,连赢了一周,把对手组打得只剩一半了,就两组合并,再招一届新员工进来,继续两组PK。在这种环境下,人已经被异化了,我有段时间看到对手组的同事离职,不会同情和惋惜,更多是胜利的快感。
那个让我们搞狼性竞争的老板,其实是北大毕业的,但是老板的人品跟学历无关。我曾经在象牙塔里以为,高等教育可以赋予一个人更加完整的人格,其实不是的。老板之所以能做到老板,首先要剥离他“人”的那一面,剥离人性之后,不能把员工当人来看,必须把员工当成物品,当成耗材。
最后我们组连赢了三周的PK,把每一届招来的人都吞并了。第四周,虽然我们一直在赢,还是只发了3000块钱工资,听见老板说,还要继续搞PK,我实在是忍不了了,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那部分快被消耗殆尽了。我就在办公室里大闹,把桌子掀了,凳子踹了,指着老板的鼻子骂,然后辞职走人。
两个赛道
刚在房产中介工作时,我还会冷不丁地问同事,“你哪个大学毕业的?” 被问的同事,有的都是初中毕业的,不搭理我,人家知道我在干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找优越感的行为很可笑。但我当时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消解“身份”上的不自洽。工作不顺的时候,我也一度想过要不要脱产考研,我知道那还是在逃避。
身份焦虑这个东西,我从小就有体会。我一个高中同学考上复旦大学国防生,高考分数不如我,但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别人都会夸复旦,自然而然地把我忽略了,我就感受到落差。这落差会驱使一个人去做本不愿意做的事,比如我就是要通过考研,回到我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处于的社会位置中。
刚开始工作那三年,我攒的钱都只住得起群租房。东三环一间朝北的三居室,不到90平,摆满30多个上下铺,厕所门口和阳台也有两张。一个月租金500块钱,满铺率很高。有的舍友往床头贴豪车的照片,也是践行“吸引力法则”。头天晚上,我就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失眠了。
那阵子我大概换过十几份工作,很焦虑,每次辞职,就意味着没钱续租,可能维持不到一个月,又要灰溜溜地回家了。自暴自弃,导致我一直陷在这个循环里——因为重复性作业太无聊,觉得没前途,很快辞职,但又实在缺钱,想快一点找到下一份工作,立即挣到钱。我那时觉得喘不过气,不仅要自力更生,还得帮父母还债。
一次过年,回家的路费还是我问同学借的。有发小当时在太原工作,家里给安排在不错的单位,我先跟他打电话,“能借我300块钱吗?”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妈让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跟你妈要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他,特别受打击。
心里头也有点埋怨父母,为什么偏偏在我毕业、找不着好工作这会儿,家里没钱了。后来有天很晚下班,走在路上我突然觉得,家里的债不是我欠的,我也没有能力去还它。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折腾大标的,发疯似地跑房源、带客户,强迫自己相信能挣到大钱。有次为了留住一个客户,我专门在他唱歌的KTV外等了4个小时,只为了他午夜出来时,我能带他去看一个底商。
天天加班的那几个月,我回到群租房身心俱疲。有时穿过狭窄的客厅过道,能看到几个长住客摆一桌盒饭,十来瓶啤酒白酒堆在脚边。室友多数是普通打工者,也有破产小老板、躲债赌鬼、无业游民,还有个天天跑北影门口干群演的哥们。我慢慢也混成老资格了,没事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吹牛打屁。
我在学生时代也接触过底层,但没有切肤的体会。那时在考古工地,我指挥工人挖坟,刨了50多座明清墓。黑灰色的棺材,打开之后有两片死人枕的瓦,旁边撒着几片铜钱,都是穷人的墓。工人是附近的村民,一天25块工钱,都抢着干。还遇到一个驼背的老奶奶,佝偻得快成90度了,没人敢聘用她,怕她死在工地上。
后来在群租房里,中秋节前的一天,一个甘肃小伙张罗了一桌酒菜,热情招呼我一块喝点。第二天我还得上班,碍于情面,坐下喝了杯就回屋睡了。早上起来,看他床边围了好多人,说昨晚喝多了耍酒疯到半夜被抬上床,现在怎么也叫不醒。我看见他的脸,紫了个大鼓包,呼吸急促。
120来折腾好半天,心电图还是一条线。最后,他的遗体被拉走,还一块带走了几个人去做笔录。想起来,我有时还会恍惚。再后来,二房东因为开设群租房被拘留了半个月,我住到房东来收房,又搬了个群租房。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很长时间不再跟985同学去比较了,与读研的那些人已经分开两个赛道。
从做题家变成挣钱家
在打鸡血PK的活儿里,开除了对手,我也要参与招新人,积累下招聘经验,发现做HR是个相对后台的工作,应该比前台销售的焦虑感小很多。那时经济没有那么紧张,可以花更长时间去应付白领工作的招聘。就这样,在之后的七八年,进入了另一套生存法则里。
第一次裁人我觉得开不了口,领导说他来示范,让我坐一边看着。这种时刻,面对平时一块吃饭一块下班的同事,把面孔换一换:“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我们的劳动合同关系今天就终止了,你收拾一下东西。”然后谈赔偿,给解除协议,签字,结束。
技巧是一点点跟领导学来的。他是个懂得世故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常嘻嘻哈哈,但工作中面孔变得很快,切换自如。我有时见他半跪着跟老板讲话,像狗腿子一样,感到很不适,但是在他看来,“只要钱给够,干什么都行。”
后来,辞退犯了错的同事,我也能有控制感地拨弄对方的神经:“虽然你犯了错,但老板确实也有一些问题,你没摸清他的脾气,不该那样做。” 训完了再往回收,有点像PUA。做着做着,我也到了中层,可以顶着人力总监的名头招摇过市了,不参与物质生产,却手握“分配”的权力。但我发现,往高层做,离老板越近,工作中那种不适感反而越强。
冲动辞职“退休”后,我感到自己成了社会边缘人。虽然我已经暂时没有了收入焦虑——做HR这些年攒下了几十万,现在住在北京郊区,每个月租金和社保加起来5000块,平时没有太大开销,但我不结婚、不工作,没办法用主流叙事定义自己。
我的时间也不再值钱。为了探索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去做自媒体创作,一年只挣了一万块,全靠积蓄活着。但我把曾经的专业知识放进了短视频里,用政治经济学解释社会现象,在创作中找到了价值感,不再有身份的焦虑。这是前十年的工作里非常稀缺的体验。
今年年初,我发了一期视频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那些曾经被我定义的“失败”。我觉得许多刚进就业市场的毕业生会产生共鸣,遇到类似困境的人比我那会儿多许多。
刚发出来没有多少流量,后来考研出分了,数据突然上涨,还上了热门。大家很详细地剖析了自己的经历,普遍全是迷茫。他们只知道自己过得不如意,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当下的失败算是什么层次的处境。
名校毕业几年,考不上编,考不上研,考不上公,工作也不顺,没有钱——处处是这样难以启齿的耻感,和死循环。有人看了我的视频有些释怀,但仍然觉得很迷茫。
我想起当年保研的同学,学了文科,后来去读博士,今年5月回国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个教职。出国之前谈的女朋友前年分手了,人家从某财大毕业,去了四大做审计,在金融圈挣了几年钱,按揭买了一套房子。而他没钱买房,没法在北京落脚。他又去读了一个博士后,进科研工作站当一年临时工,现在也到期了。
那姑娘后来写了一段时间的相亲日记,发在公众号上。她写每天跟有房的男方相亲,发现这样的人很多,有房也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小中产,她又焦虑了起来。
这不是重现我们当年本科那一套吗?自以为985的学生,象征着一种“身份”,毕业之后回头一看,985跟屎一样,一块板砖拍下去能砸死3个985。现在只不过是从一个做题家,变成一个挣钱家罢了,变成了一个业主。人真是永远也不吃教训,永远困在自己的符号系统里面,还是一个单向的人。
我家里有时候也催婚。我妈有一次不知道听哪个七大姑八大婆给的馊主意,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年要不结婚你就别回来了。”整得我还有点不习惯,她很少这么演戏。我就跟着她一块儿演,不跟她硬抬杠,敷衍过去就好。
我跟我女朋友都不想结婚。她见过她妈妈生三胎之后,怎么操劳,得癌症,60岁不到就去世了,不喜欢婚姻生活里那种状态。我也是,不想过我父母那样的婚姻关系。我愿意抚养一个孩子成人,可现实来讲,我承担不起养孩子这个成本。我俩可能都对人进入婚姻之后的生活有一定的怀疑。
工作以来,我有时会觉得孤独,对于社会、历史、价值观的思考,身边人很难共鸣,也没有那么多场合去跟人交流这些。好在我女朋友是理解我的,现在在心理上,跟我贴得最近的人就是她了。
我的视频对于网友来说只是一种安慰剂,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不可否认的是,我确实感觉自己更像一个“人”了。我时常想,人还是得经历苦难,才能获得自由。失败的意义不在于要去获得成功,而是要解构成功,解构功绩主义。不过我很难这么去劝慰这些年轻人,都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