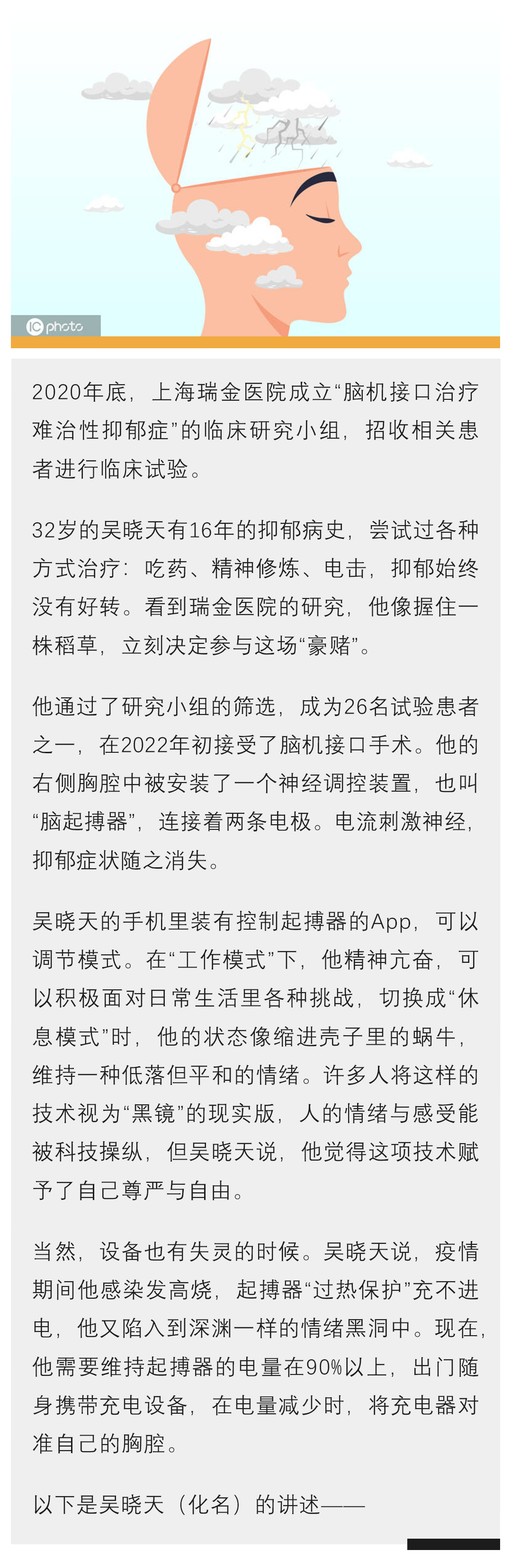
文 | 殷盛琳
编辑 | 王珊瑚
做脑机接口手术是我的一场豪赌
最早知道瑞金医院的脑机接口项目是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是初代(注:第一代神经调控技术),据我所知有病友去做过了,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也在犹豫。当时我已经做了12次电击治疗,每次治疗效果只能维持一两天,很痛苦。2021年年末,我遇到另一个病友,他是强迫症引发的抑郁症,是通过脑机接口治好的,不过是在华西医院做的手术。我本来准备也去华西,但那边说瑞金医院做得更好,而且是专门针对抑郁症的,有临床招募的项目,我就选择了瑞金医院。
脑机接口项目有一定的筛选标准,需要你是难治性抑郁症。基本上你吃过市面上所有治疗抑郁症的药,都没有效果,而且患病史要达到两年以上。医院需要你提供很多证明,确诊病历之类的,并且要观察你当时的症状,看你是否有造假,有的人会谎报病情的。
我患病16年,几乎算是“神农尝百草”,尝试过各种药物。最严重的一次,被人家给坑了,吃到进医院差点死掉,直接体验到濒死的感觉,后来索性也撑过去了。
16年里,我的人生也被改变了。如果不是因为抑郁,我可能也能考个好大学,但现实里只能去读高职,学了五年的汽修专业。
毕业之后,大部分学生都改行了,没什么人去从事这个行业。为了应付家人,我先在餐馆里工作了一两个月。他们说毕业一定要去工作,我老妈那个时候盯着我去人才市场的。但在餐馆,我每天都感觉快要休克了,实在逃不掉。还要被经理骂,我都快哭了,一句话说不出来。
后来辞职,我就去家里的店里呆着。那会儿我家在景区里面开丝绸店之类的,我就躺在小仓库里面,拿一把椅子。让我去面对客人说什么“欢迎光临,这里有新款,还挺适合你的”这样简单的话,对我来说好像是外星人在学地球话一样艰难。话卡在嘴边,吐不出来,一定说出来的时候就是颤抖,口吃结巴。
我内心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有时候熟人看到我要打招呼,我内心想,我出来上厕所而已,你不要跟我打招呼。
当时做(接受脑机接口手术)这个决定,我几乎没有顾虑。因为当时我已经决定要自杀了。16年,你看不到任何希望,时间太长了。有没有希望我其实已经不在意了,我只知道那个当下非常痛苦,压抑得太久,选择自杀是死路也是生路。
既然横竖都是死,我不如赌一把,去试一下人体实验。
脑机接口的手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在脑袋头骨两边各钻一个洞,就像装修大队那种钻孔的机器一样,钻出洞来,然后再把电极条埋进去。打了麻药仍然能感觉到疼痛,太痛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痛到直接要吐出来。
第二步是在胸腔里装一个脑起搏器的核心装置。我是躺在移动的床位上被移到手术室的,把你五花大绑地固定起来,感觉自己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猪一样。然后全麻,眼睛一闭一睁之后,我就开始呕吐了。头上还有之前立体定向仪做脑部麻醉的血,要把(嵌入脑袋的)螺丝拆掉。
手术结束了。我没有真正见到“脑机接口”的装置实物,只是之前在新闻上看到过它的样子。但它已经在我的身体里了。
上吐下泻的生理反应结束,设备开机,效果很好。像中了彩票一样,我感觉“自己”终于回来了。
“鸵鸟”与“婴儿”
但效果没能持续多久。出院当天,我其实就感觉效果在衰减了,但我想是不是心理作用?接下来的几天,效果越来越差,最后好像手术白做了一样。后面,我又去了一趟上海,医生给我做了调控,当时感觉好了一点,但回去之后又不行了。
前一个月里,一直这样反反复复,我真的内心非常痛苦。因为疫情,我也不能随时去上海。后面医院给我寄了一套远程设备,直接投到电视上医生可以远程调控。
我跟医生建议说,不如模拟一下神经调控的环境,找到它的规律,让它自动调控,比如几点到几点之间,是这个靶点程序组,其他时间是另外的靶点组。医生刚开始其实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这个想法太大胆了,以前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医生让我尝试一秒开机一秒关机,以及两个靶点组的程序切换,太可怕了那个感觉,相当于一秒天堂,一秒地狱。就像《黑镜》里的虚拟人意识上传到服务器,被游客折磨一样。
直到去年4月21号,医生调成定时切换模式。但我的生活不是定时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要出门办事,但正好切换成“休息”模式了,我怎么办?有时候凌晨切换模式时,我已经睡着了,被切换的时候突然醒过来。早上8、9点自动切换成“工作”模式,因为那个时候要做核酸,是(医生)根据检测时间来设置的。
瑞金医院的孙伯民医生比较开明,他们后来给了我自主切换的权限。现在我手机里有个专门的App,可以完成模式切换。
目前App里有4个程序,我一般只用前2个。3、4是在前面两个的基础上进行的微调,靶点位置有偏移,但是效果其实并不理想,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要在点位上面,稍微移动一点点都不行。
也不能一直在同一个模式下面,如果一直处于同一个状态,时间久了会产生疲劳感,一种麻木的感觉。尤其是工作模式,是需要一定的缓冲的。休息模式相当于给大脑喘息的时间。
人都是贪心的,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一直都是工作模式。一开始感觉很好,后来衰减,直到最后没有感觉。就像每次有困意的时候强行喝咖啡把自己弄醒,最后就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感觉。
后面,我会根据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状态来调控两种模式。程序一,也就“休息模式”下,其实是处于鸵鸟状态。你把头埋在沙土里面,杜绝一切信息,在这种状态下,我连手机都不想看,只想休息。程序二,“工作模式”下,有时候会变成像婴儿一样的,感受直接,很开心。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我的两个模式的感受越来越稳定,不需要频繁切换。如果有时候太累,也会让“鸵鸟”加一下班,在白天切换成休息模式一两个小时,观察情况,再切换回来,OK,又满血复活了。这种时候,休息模式对我来说,就像王者荣耀里的“回城”补状态,而且是坐大乔(王者英雄)的电梯回去的。
现在我工作比较自由,做民宿运营,是我家里面的产业,不用去坐班。一般来说,我是看早晨民宿的情况,如果客人那边有急事的话,比如早晨7点多他遇到什么事情要咨询我,我就要提前切换成工作模式,如果没什么急事,我一般会在9点左右切换。晚上一般凌晨1点左右切回休息模式,看自己心情。
但无论怎么切换模式,都不能关闭。不然会回到真正的抑郁状态。
我会很注意脑起搏器的电量。一般来说,让电量保持在90%以上是比较稳妥的。我最近很忙,每天都会充一次电。脑起搏器和手机里的App是通过蓝牙连接的,就算是在飞行模式下,照样可以运行。
但手机的卡顿会影响App的打开。有一次我的手机电量降到了10%以下,系统突然卡顿了,我想切换模式但打不开App,那个时候是真的有点恐惧,还好后面调整回来了。现在我的手机会保持至少60%以上的电量。
还有一次比较惊险,是我第一次感染新冠的时候,烧到40.6度,然后脑起搏器忽然充不进去电了,我赶紧去咨询医疗器械的厂商,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这款脑起搏器是非常先进的器械,有过热保护机制。
脑起搏器的充电器上有电量提示,三个进度条一样的点,如果往前进,就说明在充电,如果是常亮就是没有在充电。有时候它会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那是我胸腔里的机器偏移了位置,电没有充进去。
机器装在身体里,平时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只有当侧着身子,尤其是肉比较多的情况下,去挤压它,伤口才会感到疼痛。我喜欢侧卧,有时候刚刚卡在那个位置,会感觉到。
其他一切正常。可以剧烈运动,当然也可以游泳。除了核磁共振检查时,只能做1.5T,不能做3T。
至于什么是因技术而产生的快乐,什么是我真实的情绪,我觉得并不重要。另外,我觉得工作模式下的我,就是真实的我自己。我的同学们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和他们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差不多。那会儿我的抑郁还不严重。
握住一块橡皮泥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对于它的作用,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之前我不管用什么疗法,顶多维持三个月。脑机接口能带给我多长时间的效果,我不知道,会下意识地想,会不会没有效果?会不会不行?
一周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三个月的时限过去之后,我特别兴奋,就像通过了某种考核,试用期转正了。以前像是在用手握住一把沙子,无论怎么用力,它马上就全部流下去了,我不知道原因。这次做手术,给我的感受是把一块橡皮泥握在手里,有了实感。怎么都跑不掉。
至于脑机接口带来的改变会不会也在某天突然消失,我现在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去想这么远的事情。哪天地球爆炸了也说不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在全球范围内,那么多人装了这个东西了,癫痫、帕金森病人,也没看见哪个新闻讲,机器突然失效的,对不对?顶多哪天忽然出故障,但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
很多人说,做这项手术,装这个东西只是让你变得开心。当然不是,抑郁症不是简单的开心或不开心这样简单,它是生命力整个的衰弱。脑机接口对于我的抑郁状态有改善。
最明显的变化是食欲。以前经常觉得自己不怎么饿,没有吃东西的欲望,吃东西对我来说只是填饱肚子的行为,会觉得麻烦,吃什么都是一样的。连上厕所我都觉得麻烦。
但是现在,只要一切换到工作模式,瞬间就会感觉到饥饿。身体的感受力比以前更敏锐。我做手术之后,身材都变形了,感觉是“副作用”,本来可以去做明星的颜值(笑),现在胖得像只猪。我身高1米83,体重现在87公斤,没办法,是幸福导致的,快乐这个东西,没办法的。
我目前在苏州运营民宿。之前抑郁状态时,基本遇到什么问题我都找我老爸,每次去民宿里打扫卫生,我都要喝很多咖啡,再喝红牛,然后再抽烟,再喝水,需要一系列类似兴奋剂一样的东西才能保持状态。在线上接待顾客,我只能机械式的回复,一定打字,不敢打电话的。现在我算是应对自如了,而且很享受这个过程。遇到难缠的客人,我也没什么好怕的,可以直接面对冲突。
在患有抑郁症的16年里,唱歌是我缓解痛苦的方式,给我很多力量。做完脑机接口手术后,我感觉唱功明显提升了,医生说很多病人在做完手术后音量会提升,确实是这样的,那是对声带肌肉控制能力的提升。
唱歌是有序的,是可以预知、可以控制的,永远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存在,所以它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财富。
我现在自己在外面住,虽然偏一点,但是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小区,人车分流,而且远离我的父母。说实话,我父母至今都没有办法理解我这个病,包括我装了脑机接口以后,他们不了解这个技术,也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记得签手术同意书的当天,医生会正常告知风险,说最严重的会是死亡,其次是成为植物人,或者没办法掌控身体一些器官的机能。我妈当时就哭了,哭着说,我不要听,几乎都要跪着求我不要做。我犹豫了5秒钟,然后签了字。
长痛不如短痛。我感觉自己无路可走,因为我不甘心,我有一种执念,为什么我就要这样沉沦下去?为什么我不可以快乐起来?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到?
许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就消失了,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隐私。他觉得这个东西,相当于半机器人对不对?包括网友,很多人去调侃,说这是赛博朋克半机器人。我愿意出来说这么多,是觉得总要有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让抑郁症患者们知道,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这个(公开表达)事情无非是影响以后择偶的问题,结婚之类的,我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如果能够穿越时空,重新回到2021年年末,就算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依然会去选择做这个手术。
编者注:
吴晓天完成的这项手术,是首次用具有脑机接口功能的脑起搏器,多靶点联合刺激治疗抑郁症。项目主导者孙伯民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尽量简单地解释这一过程:“人的大脑中,神经聚集,形成神经核团。有些神经核团控制人的运动功能,有些管理情绪。所以我们想,植入脑起搏器后,电极刺激和情绪相关的神经核团,或许就能够改善抑郁症。”
孙伯民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研究初期,项目面对很多争议,“瑞金医院伦理委员会很重视这项临床研究,也很谨慎。前后不断补充材料花了一年时间,反复论证研究,最后才得以通过。”
这项技术并非没有风险。根据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研究,侵入式技术需要通过手术把电极植入大脑皮层,可能会对病人产生许多损害。比如植入物的排异反应,改变情感和个性等长期伤害。
另外,电极也有时效期。最长2~3年就会因为神经胶质细胞等包裹,不能持续记录神经细胞的放电信号,信号质量逐步下降,电极性能也会慢慢失效。病人可能会因此遭受二次伤害。
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也梳理过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人类身份、自主性、大脑数据隐私等。
比如,它可能会侵犯我们思考自由的权利,“在过去,思想在本质上被认为是私有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访问。然而,技术手段改变了这一局面。”
它也可能冲击人格尊严的权利。“研究表明,一位使用大脑刺激治疗抑郁症长达7年的患者,在焦点小组中表示对自身身份倍感困惑,开始怀疑他与他人交往方式是自主决定的,还是由所佩戴设备所决定。这种自我身份的混乱会带来许多困扰,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情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