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黄轩合作的《陌生人》才刚刚杀青。
他还在朋友圈祝贺和鼓励年轻电影人。
以悼念万玛才旦导演。
编辑:刘亚萌



万玛才旦电影里的藏地风貌
我生在青海安多藏区的昨那村,是半农半牧的一个地区。我从小就接触传统藏文化,这种文化确实有一些神秘和魔幻的地方。
比如我爷爷,坚信我是他的舅舅的转世。他的舅舅是个宁玛巴僧人,有很多经书,算是有学识的人。据说我很小的时候,说过一些跟爷爷的这个舅舅有关的事情,就被爷爷认定是他的转世了。所以我在家族里的地位也相对比较特殊,从小就给我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我去学习。
我身边也有“神授”的真事。就是一个完全不认识字的放羊娃,突然有一天昏睡过去,睡了七天七夜之后,醒来就能滔滔不绝地讲《格萨尔王传》,词汇量很大,情绪很优美,完全超出了他的知识水平。

电影里呈现的藏地男性


电影里呈现的藏地女性,传统与现代
走上电影之路,我觉得也挺魔幻的。我本来读的是一个师范类的中专,相当于高中,毕业之后就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工资99块钱。那是1987年,其实是挺多钱了,工作也稳定,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职业吧。这个学校就那么两三个老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都得教,每天的作业堆得就跟个小山似的。白天学生们吵吵嚷嚷的,很热闹,你不会感到寂寞,你也没有时间去孤独。可是到了晚上,整个学校就你一个人,批改完那堆作业本,一个人闲下来,内心就会时常被一种排遣不掉的孤独和寂寞包围。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惟一的消遣就是看看书,然后写写东西。
▲
万玛才旦青年时期
写作是从这里开始,没发表过,完全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要。当时写处女作《人与狗》,就想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对人的认识全部呈现出来。
当了四年小学老师以后,就觉得心里不安分,想要出去,到更大的环境里去。

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但是单位不让考,让我写保证书,说如果考不上的话,公职也放弃。我二话没说就写了保证书,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引起了轰动,等于是自己放弃了铁饭碗。
后来就去了兰州上大学,读藏语言文学,毕业以后去机关做公务员。后来又去读硕士,藏汉文学互译专业,其实一直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直到碰上一个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专门赞助藏族的学生去学习一些比较新的专业。那个时候很少藏人学电影,我申请说我特别想学电影。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我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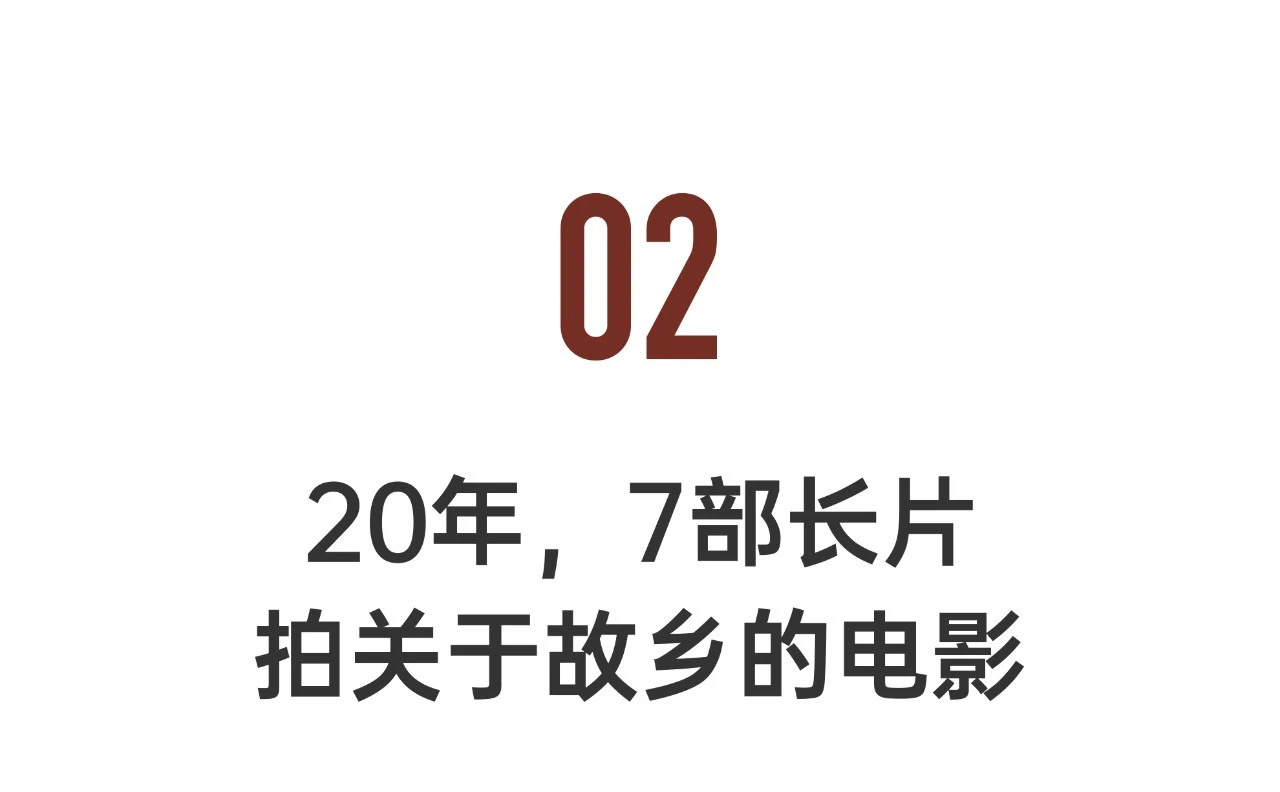

《撞死了一只羊》在威尼斯电影节获最佳剧本奖

《静静的嘛呢石》剧照
学生时期,我花了五千块,拍了作业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在国际上拿了一个奖,奖金几万块。我拿这个奖金买了一台DV,然后又把这个短片的故事扩充成我的第一个长片,片名还是《静静的嘛呢石》。
2005年,《静静的嘛呢石》参加金鸡奖,获得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那一年也正好是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
看到电视里播获奖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藏族人都非常高兴。有人告诉我说,他甚至高兴得把电视机都砸了。
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是一种他者的目光在讲述藏人的故事。1960年代的《农奴》,1980年代《盗马贼》,1990年代的《红河谷》,都不是藏人的思维方式。直到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才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藏人的电影。
之后,我又继续拍摄了《寻找智美更登》《老狗》。这三部片子,有人说是我的“故乡三部曲”。


《塔洛》剧照
我小时候在山上放羊,大白天见不到一个人影。一个人在开阔荒凉的地方行走,你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孤独,强烈到有了具体的形状。
《塔洛》的故事就来源于这种孤独。这部电影改编自我2013年的同名小说。当时,一个留小辫子的男人形象突然进入了我的脑海里,“塔洛平时都留着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
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着自己的羊群,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跟现实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白天放羊出圈,到井边打水,喂狗,收集羊圈里的羊粪,晾晒羊粪。晚上把羊赶回羊圈,喝着白酒,抽自己卷的烟,点上篝火,听广播,放二踢脚吓唬狼,学唱拉伊(牧羊人唱的情歌)……
可以说,塔洛身上有我的影子,我的身上也有塔洛的影子。它是在我的家乡昨那村一带拍摄,电影中,塔洛在山上的部分,16分钟没有台词,需要依靠动作和画面去塑造他孤独的生活状态,而我对这些生活细节很熟悉。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撞死了一只羊》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孤独的故事。司机和杀手,都是常年在路上独自行走,心中带着一股强大的执念。
这种孤独的情绪,我觉得适合在一个开阔、荒凉的地方拍摄。我们从西宁一路找,最后在可可西里找到那样一段荒凉的路。
可可西里无人区海拔5500米,我坚持在冬天拍摄,冬天的温度低于零下20℃,给影片的肃杀氛围定下了整体基调。
可可西里有很多的藏羚羊、野牦牛,但这些动物都是神出鬼没,常常长时间看不到任何活物。
片中,司机开车到了一个湖边,没有看到任何动物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就撞死了一只羊,是一种突然袭来的荒诞感。


《气球》的灵感是偶然间诞生的。那是2010年的秋末冬初,我要去中央民族大学见朋友,路过中关村,突然在天空中看到一只红色的气球在飘。当时已经有很多以气球意象为主题的经典电影。我的电影,怎么才能跟藏地的当下发生关联?我马上就想到了“白气球”,避孕套。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生育,藏地也不例外。卓嘎家有3个孩子,两个儿子把她藏起来的避孕套偷走当玩具,她也因此意外怀孕了。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上师认定是家里长辈的转世,这下所有人都逼她把孩子生下来。但卓嘎却非常纠结,因为她不想生。这部片子是讲生育的,很多人说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女性主义的东西。比如女医生对卓嘎说“我们女人又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以及最后卓嘎对妹妹说,有点羡慕她出家当尼姑,无牵无挂。


影片是一个开放式结尾: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卓嘎跟着妹妹去了寺庙,她到底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甚至于她会不会出家,我们不知道她最后是如何决定的。我没办法帮她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后我让气球飘走了。越飞越高,几乎要消失不见了。气球本身就有一点象征含义,象征着生命或者希望。

我早期的电影风格比较平实,《撞死了一只羊》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我的电影开始变得有些魔幻了。比如有一场戏是“梦中捉痣”,弟弟把哥哥背上的痣,很轻易地拿下来,给哥哥看,然后他们嬉笑着在沙漠上奔跑,跑向蓝色的青海湖水。
还有卓嘎姐妹的“窗前谈话”。年轻的妹妹(未出家时留着长发)缓缓走来,她美丽地笑了一下,停在姐姐的身后,而姐姐的表情有点恍惚。这里表现出,姐姐和当年的妹妹的命运产生了某种重叠。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刻意地转型。我的小说里很早就有了超现实主义的元素,比如在《乌金的牙齿》和《嘛呢石,静静地敲》里,现实与梦境、此时和彼时完全是没有界限的。只能说早期拍电影,会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局限,那时只能拍一些现实题材的。


《气球》拍摄期间,在家乡勘景
我坚持拍藏语电影,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被一位名叫端智嘉的藏语作家影响。他可以说是藏语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启蒙的意义。他的作品一登在刊物上,我们都抢着去看,把他的散文集整本地背下来。他也是我读中专时的老师,我们经常听他的课。他跟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留着长发,穿很长的风衣,戴着一副眼镜,不要求学生脱帽行礼,一边上课一边抽烟。讲《罗摩衍那》,他可以随口背诵,4行诗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节课,完全不需要讲义。一天早上,我们听说他因为煤气中毒而死,是自杀,留下了遗书,死的时候才32岁。据说他自杀是为了唤醒那个时期的藏民相对封闭的思想。他有点像藏族人的鲁迅,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直到现在,他写的歌现在还在青海湖传唱,每到忌日学生们还是会自发地念他的诗。
到了我做电影,更多地希望纠正外界对藏人固有的看法,用自己的目光、自己的创作,去呈现更加真实的藏地、藏人。其实,我希望自己电影的主创都是藏人。因为很多细节,不熟悉藏地的话是很难用心捕捉到的。比如拍摄《老狗》的时候,有一场在草丛中行走的戏,录音师德格才让要求工作人员都光着脚,把裤子也脱了,避免发出摩擦声,这样才能录下这片草原的干净声音。


一种以往没有的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肯定是很难的。有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来了三个免学费的拉萨学生。松太加和我在黄亭子请他们吃饭,作为长辈告诉他们,你们要好好学习,珍惜这个机会。一个月以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学习压力太大了,他们已经回拉萨了。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更多的藏族年轻人都加入进来,形成了所谓“藏地电影新浪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自己也鼓励这些年轻人。我的朋友松太加,原本是画画的,我鼓动他去北京学摄影,以后一起搭档拍电影。松太加做了我几部电影的摄影、美术之后,拍出了自己的《河》、《阿拉姜色》。2018年,我的副导演拉华加拍出处女作《旺扎的雨靴》,获得当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录音师和配乐师德格才让,原本是搞摇滚音乐的,也是在我的鼓动下来了北京。现在他自己也拍片,后来就有了《他与罗耶戴尔》。

藏地一直在改变。《静静的嘛呢石》中的很多生活细节,现在都已经消失了。我老家的那个村子,大概只剩山坡顶上还没变。 我觉得比起物质上,其实藏族人精神世界的变化更剧烈。我的电影很多都在表达这样的变化。接下来,我的题材可能会做一些改变,以往,我拍的都是生活在“故土”的藏族人,之后我可能会去拍生活在城市里的藏族人,去拍汉语电影。从本质上看,藏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是只给藏人拍片,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超越民族、超越地域,和更多的人发生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