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夏天,1076万应届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新考验。
在这个疫情与人生不停较量的毕业季,我们与四位“97后”聊了聊。他们有的正在为留学的高昂费用打工,有的在准备第三次法考,有的毕业两年后才找到心仪的工作,有的还在为了理想的学术梦孜孜不倦。
在从学生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丢掉了应届生身份,也逐渐在各自的人生奇遇中拨云见日。以下是他们与“应届生身份”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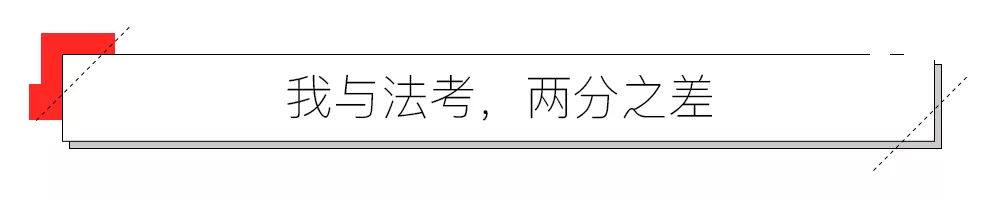
所有人都在我的朋友圈照片下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你胖了”。
我光着脚站在镜子前,看着日渐圆润的脸,捏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攀上了腰际的肥肉,有些沮丧。
直到大学毕业,我都还是一个符合世俗定义“好身材”的95斤女孩。不过短短两年,我的体重就已逼近110斤。都说过了二十四岁,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开始减缓,人就很容易长胖。连我的身材都在暗示我,自己已经过了那个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年纪。
这样的失落,间歇性地笼罩在我毕业后的两年里。
我毕业于云南的一所二本学校,学习法律专业。
第一学历的平庸让我清楚地知道,必须以“法考”为基础,才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通过法考就是我的“人生头等大事”。尽管每一年我都会跑到家乡周围的大城市,认真甄别各个法考机构,一轮又一轮地进行长达半年的学习。可是在去年刚刚结束的法考中,我以两分之差落了榜。
两分,只是一道选择题的分值。看似微乎其微的差距,或许能让人燃起“我只差一点儿了”的信心,但更多的只会是无尽的挫败感和悔意。
又一次的努力与等待付诸东流,我无奈从天津的培训学校回到了河北老家。
我那些同期毕业的同学,有的已经顺利拿下法考进入律所,有的转了行进入新天地,有的考上研究生继续学业,有的即将与心爱的人结婚,而我的生活却没什么进展。
空档的两年让我丢掉了最年轻的状态,陷入了疲软。
我还能想起来毕业那年的我,一边急匆匆地写着毕业论文,一边风风火火地拉着同学扎进学校的校招亭。可现在,我既不想工作,也不想开展其他计划。如果在该做某件事情的年纪没有去做,那惰性就会占领心智,需求也会变得迟钝起来。
第二次法考失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了严重的焦虑,每天日夜颠倒,胡吃海塞,身材很快走了样——这让我焦虑的维度又增了一层。
不过平心而论,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相反,“通过法考,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是我六年里养成的一种惯性自我认知。
记得大学最后一堂课,老师对我们说,“走法考这条路,没必要与别人争快慢,一位律师的成长,更重要的是经验和案源。”而在备考过程中,我也见识了形色各异的法考人。
不同于其他考试,报考法考没有年龄的限制,因此,在法考班里不只能看到像我一样刚毕业的法学生,还能看到很多已经进入社会、从事各行各业的人。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来自东北的阿姨,她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闲聊时我才知道她已经有了孙子,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因为她家里人牵扯到了案子,又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她就决定自己来学习法律。
无论是以“过来人”身份给了我慰藉的老师,还是这位迎难而上的阿姨,亦或是其他正在为法考努力的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法律人特有的蓬勃生机。
我在备考课本扉页上写下了这句话,并笃信法律信念可以助力我的法考。两年来,我依然会为逝去的时间以及短期内无法以“正常的节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而感到失落,但也在一次次考试中坚定了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
一转眼2022年已过半,我依旧在准备今年的法考。这一次,我打算自己在家备考,依托这两年的系统学习,琢磨出一份针对自己的专项复习方案。
不仅如此,我也开始去健身房、游泳馆,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健康饮食。过去两年的生活并不如我毕业时想象的那般顺利,甚至还一度因为目标灰暗而失控。可最近,对生活的掌控权似乎又一点点地回到了我的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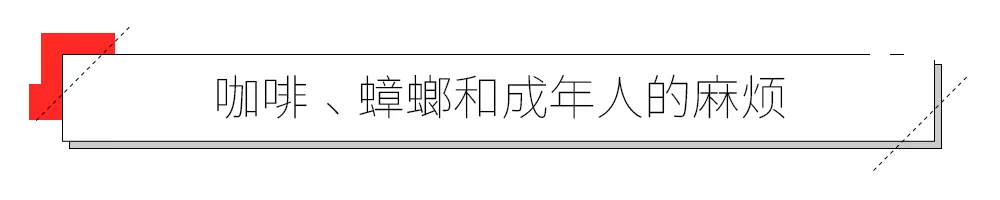
上大学之前,我总以为自己的生活已经足够优渥。
那时我还住在一座北方沿海小城,海风徐徐地吹,殷红的车厘子总会在六月涌上大街小巷。课余时间里,我学画画,听摇滚乐,打架子鼓,看书看电影,觉得生活并不难。
直到生活被真正交到自己手中。
安放我四年大学生活的小天地,这里有我做的模型、画的画和一面手鼓。在北京读完四年大学,我打算出国读书,却没有如愿拿到心仪学校的offer,于是决定先找份工作。
一家坐标深圳、业内小有名气的工程公司是我的目标,我郑重地投下了自己第一份全职工作的简历。
仍记得,在接到录取结果的那天夜里,我梦到了一条半干枯的河,顺着河岸走过去,看到河里有一只巨大的乌龟。第二天去网上解梦,屏幕上赫然写着“乌龟象征着财富”,我心里暗自开心。
即将脱离学校的庇护步入社会,心情谈不上喜悦,却对未来充满了干劲儿和好奇心。我只身前往深圳——一座从未谋面也无人可依的南方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我在不同租房软件上找房,计算交了公积金和社保后到手工资还有多少,处理各种在校园阶段无需面对的琐事与难题。那时我才发现,成为一个成年人的过程是繁复的。
同样复杂的还有我的心事。每做完一项“成年人要务”,我心里总会充斥两种情绪,一种是对自己越发独立的庆幸,一种是感到离孩童时期越来越远的酸涩。
不过,生活大体是顺利的。找房、搬家、进公司,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月后,我拿到了一张全新的、印着广东省深圳市字样的身份证。
虽然偶尔也会崩溃,比如南方的蟑螂总会在凌晨四点和来自北方的我相遇。每当它们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家的每个角落,我都会恍惚,仿佛它们才是正义凛然的孤胆英雄,而我则是那个交了房租却备受挤兑的滑稽小丑。
我常常走进真实的建筑物中,感受并记录它的结构和光影。实际上,我的成功入职并不是好运的开始。相关行业陷入冰点,每个员工也都心知肚明。可是,行业的含金量与内卷程度并没有被稀释,反而人人自危,没人甘心躺平。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卯足了劲儿上网课、学软件,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近乎疯狂地汲取各个领域的知识。
尽管无意“卷”入其中,可深陷在这种不进则退的环境里,我也不自觉变得随波逐流起来,去留学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
从好的方面来讲,学习是必要的,留学可以让我以更好的姿态重新进入这个行业。除此之外,我也有另一层小心思——或许等回国时刚好能碰上行业回春,也能让我从自耗和内卷中暂时抽身,这是缓兵之计。
一名合格建筑人的必要支出:以箱为计量单位的咖啡胶囊。于是我开启了边工作边申请的状态。即便身体无比疲惫,下班回到家中,还是会马不停蹄地准备申请材料,常常熬到两三点,第二天再顶着黑眼圈继续参加早会。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个月,还没等来考试,我就先把自己送进了医院。斟酌良久,我决定辞职,专心准备申请。
经济上的压力也随辞职到来。没有稳定收入,我只能找一些兼职挣外快,在淘宝上接设计工作,帮其他留学生改文书,或者进深圳的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拿两百多块钱的日结工资。
我还给自己制定了每天花钱的限额,尽量缩衣节食,控制日常开销。正值租住的房子到期,因不想再支付高额的中介费,我搬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酒店房间里,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
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一年,时常会想起大学宿舍楼下绽放的月季花。在毕业后的一年里,我触摸到了社会的真实温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简单,而是更难。尤其随着眼界的开阔,我更能发现眼前的局限与自己的不足,而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努力地生活。“努力”,在这里或许并不是褒奖,而是为了理想的未来不得不做的事情。
今年3月,我收到了心仪学校发来的录取信,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大把的时间空了出来,我就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昏暗小房间里,继续上网课,学习法语、C4D和手绘......把时间再度填满,直到没空闲再去焦虑,忙碌又平静地等待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到来。

在和旧友们闲谈时突然发现,大家毕业后都在继续往上读,而在高中时一直是年级第一的我,突然变成了身边朋友里学历最低的那一个。
怎么稀里糊涂变成这样了?我不懂。
我不懂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大学的学生会选拔,比如校招对应届生身份的限制,比如一份挑不出瑕疵的完美简历,比如“被社会化”,我对这些东西都很模糊。
可能是我过得太抽象,不太想花时间去研究这些条条框框;也可能是这个社会太具象和功利,让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其实,大四时我考虑过跨专业考研,去读戏剧类院校。戏剧是一个复合的艺术体,可以为我提供一片广阔天地,把从文学和生活中汲取的美与经验融入其中,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备考的那段日子,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每天下午钻进图书馆,乐此不疲地看很多书,考研成了我可以尽情学习知识的“幌子”,不必对没有认真钻研本专业而产生负罪感,可以在喜欢的内容里尽情畅游。
但是,那一年学校的录取机制临时发生了变动,我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复试却报空了。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产生过多负面情绪。我一贯是这样,坚信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走哪条路都是对的,如果此路不通,那就换一条。
那之后我来到北京,尝试过在传统报社当实习生,应聘过剧场的工作,也给剧院杂志供过稿。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但同时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过着一种近乎悬浮的生活,继续徜徉在感兴趣的领域里,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搞那个,什么都想尝试一下。而这看似反复折腾的尝试过程,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自我。
创作仍是我短期内的首要目标。既然与目标院校失之交臂,无法继续学业,那就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去。我更长远的目标,则是做一份能够把自己的积累转化出来的、有创造性、有意义的工作。
这是我生活的支点,让我在茫茫人生和花花世界里,找到了定位和方向。
但迷茫也是无法避免的,尤其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
人生的前二十年,我按照社会制定好的骨架顺利行进着。读完高中考大学,读完大一读大二,可是读完大学要做什么呢?没人能给我一个范式,当时就有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我决定先找份工作过渡。
我去了一家科技媒体公司。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但它可以为我提供稳定的收入和相对自由的环境。
但是,当一枚社会螺丝钉的感觉并不算好。我的生活被无谓的职场社交、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填满,导致我一下班就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手机里,报复性地刷起来,直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最终,我的创作者状态和精力被无限度地耗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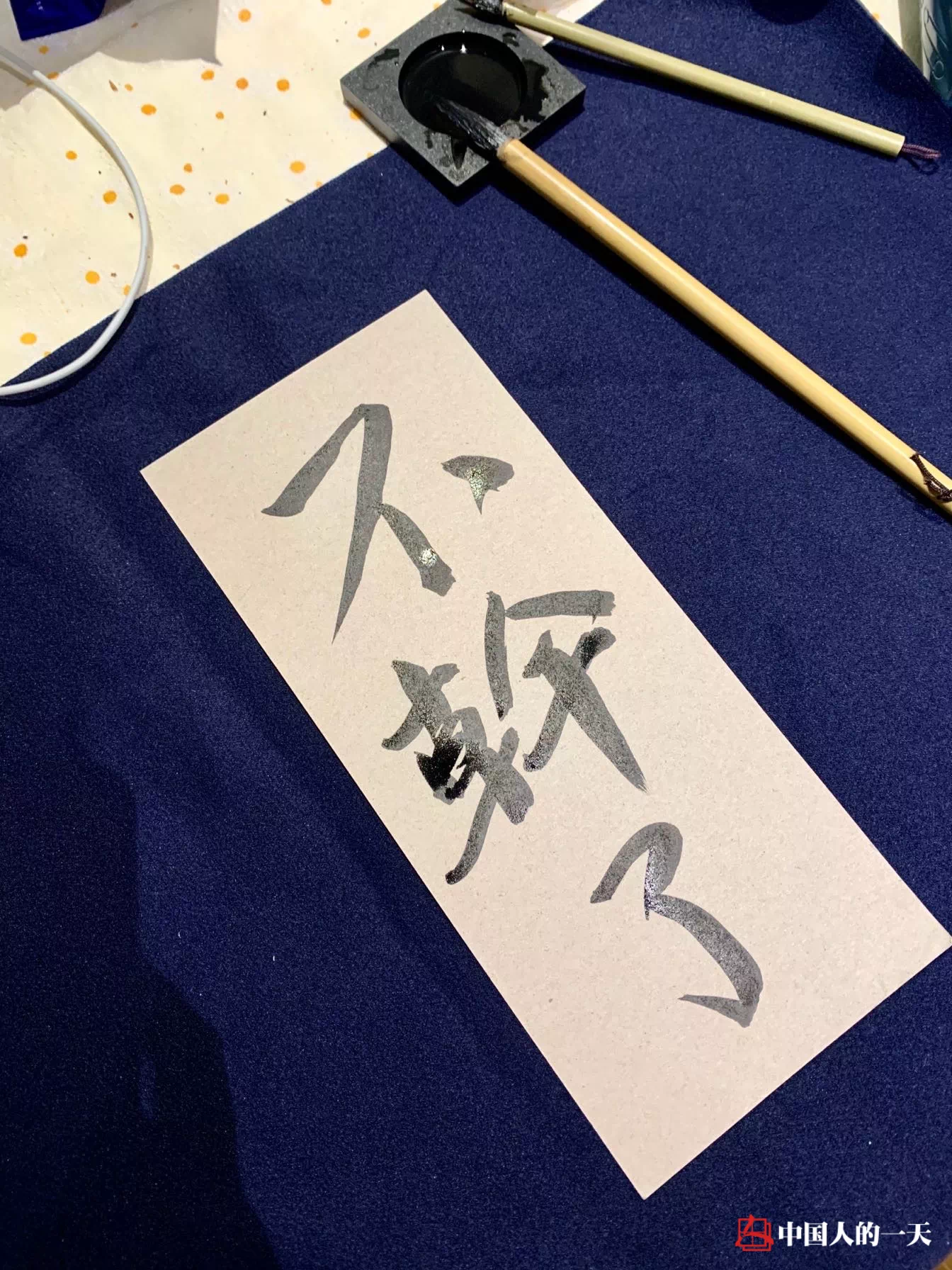
我写了一幅毛笔字来给自己出气。
好在今年年初时,机缘巧合之下,我接到了一个剧本项目。签约后,我爽快地辞掉了之前的工作,没有一丝留恋,向着成为一名职业化的全职编剧发展。
难掩刚入行的新奇和兴奋,我很快进入了状态,开始系统学习。
哪怕在大学时接触过写脚本拍东西,但如何把剧本写规范,怎么把握体量和结构、控制预算,都需要更实际的工作经验。
之前,我以为自己不擅长合作,但现在我却能和同事开上几个小时的脑暴会,从他们身上吸收经验,拓展创作的思路,这对我而言是另一种打磨。
还有一次,我和一位资深导演聊天,他告诉我哪些地方还能修改,场与场之间怎么处理会更顺畅。听完我恍然大悟,因为这不仅可以用在我的剧本里,也能运用到我创作的小说中,一切都是可以触类旁通的。
入行三个月,目前为止我是感到舒适而愉悦的,一切都值得期待。
在走了不少弯路之后,我终于正式踏入了喜欢的领域。
过去这两年,我总是用两句话来鼓励自己,一个是“要沉得住气”,另一个是“不要怕走弯路”。其实走弯路没那么可怕,只要你能再绕回来就好了,而且还能多看看路上的风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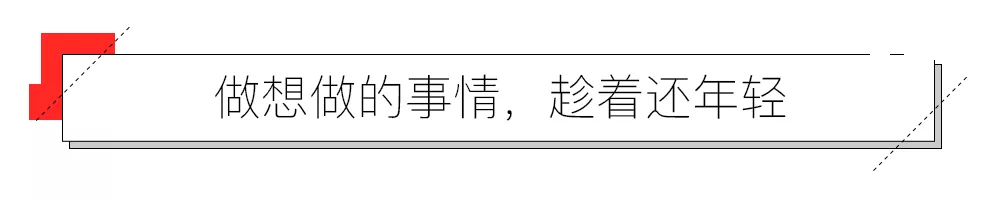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宣布暂停2021年社会学专业的博士招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专业停止招生,阿拉斯加大学宣布一次性暂停39个人文社科的本科、硕士、博士学位项目......"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这些字,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头也跟着疼起来。
如果说2021年是美国人文学科的悲伤之年,那也将是我的悲伤之年。
受到疫情的影响,美国财政缩减,各个高校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纷纷减少“非必要”的专业名额,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社科专业——我即将报考的专业。
本科期间,我早早明确了出国学习性别研究专业的学术发展之路,但2020年全球疫情肆虐,面临毕业的我出于安全考量,决定缓一年再申请。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准备申请,无论是基础的语言、材料、成绩单、实习课题,还是参加国际组织、做NGO项目志愿者等专业相关实践,我都完成得很漂亮。因此,我非常有信心,时常会幻想,我远在大洋彼岸的未来导师能透过这些材料,看到这个来自东方的小女孩儿心中沉甸甸的炽热。一切准备就绪,我向心仪的学校递交了材料。
煎熬的等待时间里,我一直在网上关注其他留学生的进展,大家的反馈普遍不乐观。录取名额都少得可怜,按往年的数据来算,一个偏理工科的专业,一年大概能招二三十个学生,文科专业一般会招十几个,但这次某个文科项目的硕士生只录取了三个。
我要学的性别研究专业,更是社会学大类中的小众,只有为数不多的学校开设,录取人数少之又少......
形势的严峻超出了所有人想象,原以为受疫情影响,申请的竞争压力会变小,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我的信心很快被冲垮了,以致于在收到拒信时,我并不感到意外。
收到拒信的同时,我也收到了喜欢的作家林奕含的日历。收到拒信的那一天,我坐在电脑前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边为自己忧愁,一边暗自感伤:似乎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文科生和文科专业都逃不过这样的尴尬处境。
尽管在外人看来,做学术是枯燥乏味的,文科相较于理工科又不够实用。但文科有自己的逻辑,而社会学更有着独特的魅力。
它像是认知世界的工具,帮助人思考、归纳,用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已经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问题。研究社会学的前辈们,往往也都心怀热忱,对世界充满了探究心与责任感。
每每遇见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也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能用多种媒介将其诠释出来,刨根问底,试图总结背后条理。因此,在社会学的学习中,我感受到了归属感和雀跃。
或许很多真相对世界来说并不“实用”,也不够“重要”,却是我在意的。
2021年申请失败后,我找到了一份新闻行业的工作,权当做田野调查。
这并不是一份绝对“体面”的工作,而是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外包。我不太纠结于此,对于工作,我的态度总是随遇而安的。
因为要兼顾申请和学术,我会早起一些,安排好一天的时间。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到国际新闻,便顺带着巩固了英语。遇到感兴趣的选题,我会把它们也变成我做研究的素材。这是读书的最大好处——任何事都可以变成自己的,只要足够用心。
原本大段的学习时间被压缩,我就把能利用的间歇充分利用起来。眼下自己能做的事不算多,但我从未停止过做些什么,这让我感到欣慰和踏实,哪怕在这两年中一直没有更瞩目的进展。
我一直在尽量淡漠他人作用在我身上的压力。但当身边人向我投来目光,哪怕并无恶意,我还是会感到难堪。他们的关心仿佛一种责备,提醒着我在过去的两年、未来的一年中,自己都没有能像其他的同龄人一样,走上一条足够稳定的道路。注视之下,我的不顺显得无比刺眼……
申请失败后待在家里的那段时间,妈妈看出了我的落寞,就邀我一起到屋外散心。走在小区楼下,我丧气地说:“如果再没有申请上,该怎么办呢?别人就会说,‘不要再由着她的性子了’之类的话”。
“你管别人怎么想你呢”,妈妈说。
黑夜里我看不清她的脸,我们没再说话,相互陪伴着静静地走了下去。在感到不安的时候,身边人的认可给了我最大的支撑与安慰。
遛弯时,有一个穿着超人衣服的小孩儿跑了出来,妈妈跟我说,“看,你一定会有好运的”。其实我也犹豫过,要不要放弃留学这条路,选择一个更稳妥的工作。但我觉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不会因为当下选择了一些看似稳妥的方式就会消失。我想趁着自己还年轻,享受一种更开心的生活方式,更专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仍在时刻关心身边或远方的人,关心周遭发生的一切, 乐此不疲地写论文,用笔记录,用心剖析,认真搞学术,认真准备下一年的申请。
尽管远方的路尚不明晰,但那忽明忽暗的光也足够支撑我前行。
面对即将到来的毕业季,你有怎样的打算呢?
第4034期
撰文 | 高歌
编辑 | 高歌 Vayne
出品 | 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