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赠送了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的戏剧集《安魂曲》,我先是随意地翻阅了一下。感觉真是好!我热爱话剧,这种爱,甚至超过了电影,因为它能守护和捍卫一个时代的人文品格、精神高度以至人的思考深度,与喧嚣的商业市场保持一种必要的冷静距离。很可惜,中国的话剧舞台如今成了群魔乱舞的杂耍场所,除了洒狗血、无厘头及沽名钓誉,再难见到真正的话剧艺术了。
曾几何时,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百花争艳,百鸟争鸣,佳作迭出。那还是在改开初期的那个年代,以《于无声处》为发端,《丹心谱》《假如我是真的》《枫叶红了的时候》《法庭内外》等等,等等,风起云涌,看着让人热血沸腾。那是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诗意盎然的年代,万众一心、全民皆具共识的年代。可惜昙花一现,过早地凋谢了。
我多么怀念那个年代!
我原想就简单地试读几页,然后搁下,以后找时间再细读,孰料,一个试读,一下子就将我彻底淹没在了列文的第一个剧本中——《安魂曲》。剧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做棺木的生活捉襟见肘的老人、他濒死老妻、车夫、妓女、嫖客和一名卫生员,场景显然是极其简陋的,人之状态亦见了粗俗、卑琐、肮脏和丑陋,几乎没有什么我们习见的那种激烈的戏剧冲突,台词亦是些貌似疲疲沓沓的家长里短,显得有一搭而无一搭的,各说各话,但却弥漫出了一股浓浓的的末世情状。
我兴奋地读出了剧本中散发出的一种惊人的伟大感———是深埋在作者心中、流淌在他血液中的伟大感。剧作家列文是悲悯的乃至悲世的,他的目光像一把闪烁着逼人寒光的利剑,挑开了笼罩着人世的面纱,直见人性和人间真相,逼问着世界的真理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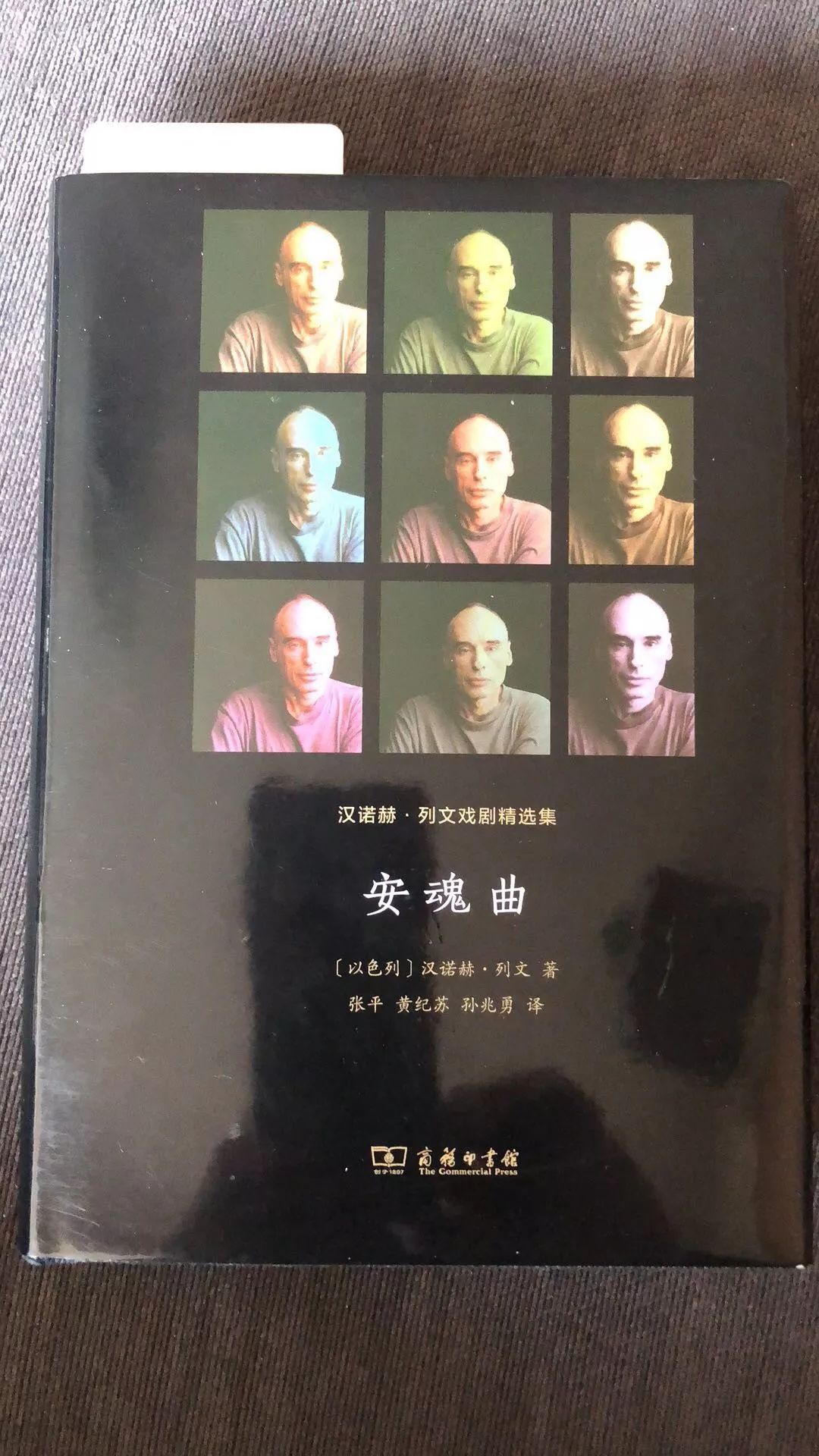
几年前,当我分别阅读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哥本哈根》《怀疑》《安娜在热带》《求证》《山羊》《枕头人》时,我就突然意识到了,在今日之世界,西方的当代戏剧可谓一领风骚,正在无所畏惧大踏步地走在文学精神的最前端,沿着由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奥尼尔所开创的探索人生的道路。这些戏剧皆具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以为早已在消费与享乐的时代消失了的悲世情怀,以及对我们自身人性弱点的勇敢面对。读时时常会觉得心尖很疼,刺骨入髓,但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时,便从虚幻的臆造的梦境中惊醒,觉知身上其实流淌着沾染了太多的世间之风尘的淋漓鲜血,从而我们亦知,疗伤靠的还是我们自己,只有自我拯救,而最好的医师,乃是我们内心那未死的残存的良知。
我们从尘埃中奋身站起,眼前依旧是看不见尽头的漫漫长夜,但我们开始了孤独的长旅,因为只有远行,我们才能迎向大地的黎明。哦,朋友们,请相信我的推荐,读读这些书吧,我们在污浊的尘俗中昏睡的时间太长久了,该被它们唤醒了,否则,我们的惨淡的人生,将错过多少展现希望的黎明之光?我们需要精神拯救,以不负此生。
列文的《安魂曲》写得无法形容的好,那经天纬地博大的人道主义力量,那对苦难人生深切的感同身受。其中有一节,剧中之那个吝啬的老人,为了安慰那位被别人烫死孩子的17岁的母亲。母亲当时抱着孩子,那个被人烫死的、她不相信他已死去的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发出绝望的哀鸣。老人不得已假扮了一圣人,由此出现了下面的一段对话,将我们人人无从逃避的人生悲情,以最质朴的隐喻方式传达了出来:
老人:那你的这一生干过什么呢,孩子?
母亲:就这些,洗衣服、扫地……
老人:可是更大一点儿的事情呢?做过吗?
母亲:没做过,先生。
老人:你是个人,你有头脑,你有自己的愿望,你怎么对待这些呢?
母亲:我活着,先生。
老人:你从没有站在哪个十字路口吗?
母亲:没有,先生。
老人:你从来没有说过:喏,我要走这儿,不要走那儿?
母亲:没有,先生,生活带着我走,我就走。
老人:这是什么生活呀,孩子!……
母亲:跟所有人的生活一样,先生,我站在长长的队里领我那一小把糖,队很长,我没有排到。
……
老人(在她面前站住了片刻,不知该做什么,触摸着她的脸颊):喏 ,我抚摸了你,好让你能哭出一点儿来。
(停顿,她沉默着)
要是你能哭出来,你会轻松些。
(停顿)
母亲:要是我哭出来,先生,这世界就会轻松些。他们就会说:“你从没有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吗?”——我就回答说:“我站了。在一个黄昏,我站在我孩子的墓前,我可以哭泣也可以沉默,我做了选择,
老人:那……就这样吧。这样就是了。
(老人远去。停顿。母亲爆发出哭声,趴在坟墓上,努力在说话时抑制住自己的哭声)
母亲:……我的孩子,你在那儿,你活着,谁说幻觉是谎言,我们的生活才是谎言,这个世界才是谎言,真实的世界是闭上眼睛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当你不再向世界睁眼的时候,真实才在那里。……


《安魂曲》剧照
读到这里,我的情绪突然失控,泪如雨下。就在这时,这个我所在的、熟悉的世界,也突然在远去,我像处在一个被悬置的天穹上,俯瞰着这个布满蝼蚁般人来人往的流动的人世间,与此同时,我亦觉自己忽然获得了一种心灵被荡涤后所获得的升华了的精神境界,那是别一样的崇高感,在这里,没有盖世英雄,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悲天悯人和与苦难同在的生存勇气,内心的卑污在此刻被濯洗净尽了。什么才是伟大的文学?这就是——《安魂曲》,它让你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这也是由古希腊悲剧延续下来的伟大传统。
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一天,我在文学创作上要突然掉转头,回归传统之经典叙事的文学之路。是的,那是文学之原乡呵,我们曾经忘记了家乡之所在,忘记了回家的路,在今天,我们终于觉醒了,踏上了一条返乡的路。家乡亦遥遥在望了!
就这么,静心读完了列文的《安魂曲》,心境其实难以平复。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描述这种心境,痛苦、难过、悲伤、哀痛皆有,但又超越了这些情感之元素。我突然发现,语言在此时此刻乃是彻底失效的,因了难以描述。只能用心去体味与感受。
伟大的艺术作品必是如此的,宣告俗常的语言概念之所指,纷纷坠入了空幻,作品深在之意蕴中所升腾起的能指,则穿透、穿越任何语言意指之定义,为读者重新开创了另一广阔悠长的视域和另一心灵的感受空间,在哪里,言语尚未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它仍在空中做无根的飘浮。而一旦被我们找到,一重生命之门,便由此向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定义"也就随之而光荣诞生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伟大的艺术作品,常常会让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在它面前顿然失语,苍白无色。我们只须再想一想诞生于公元前的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在历经了二千年后,才于上世纪初幸运地由一名精神分析医生弗洛伊德给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而在此之前,它始终是一悬浮在人类历史上空的一个巨大的命运之谜。
我看了一下列文的成长简历,他出身在一个犹太教之家,是杰出的波兰拉比的后代,十二岁丧父,在特拉维夫的贫民窟长大成人,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他对人生苦难会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特别的深度感悟,列文笔下之人物多涉死亡,而死亡之因,又与人生之困窘与苦难相伴而生,这也是为什么他对死亡常会发出惊世骇俗的浩叹,显然在列文看来,唯由此——死亡,人才真正的回归了人之为人的那个真实的自我,只是以长眠的形式而存在。
这本书居然是以以色列大使馆的名义资助出版的!若按照我们的观念来看,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它写的几近是从色列人"丑陋不堪"的国民性,卑琐、肮脏、可怜、痛苦和迷茫,乃至人生之无望,而正是因了此,创作了它们的作者汉诺赫-列文却被他的祖国以色列视为"以色列的良心"、“最激动人心的剧作家”,成为了以色列最受尊敬和爱戴的艺术家。
为什么?一个若从表面上看去并没有赞美他的祖国的人,一个看似丑化了民族同胞的人,竟会在自己的祖国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甚至不惜将他对以色列民族之"暗面"透彻地揭示,以国家之名义向国外予以推广?
这本戏剧集(四部剧)是揭露,是批判,是无情的鞭挞,而非赞美与歌颂,但我们在此却见证了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自信、骄傲和强大:勇敢地正视民族内心的晦暗、肮脏与怯懦,从而认识自己。向以色列民族致敬!
接下来,我又一鼓作气地读了列文的另一部戏剧:《俄亥俄小姐》。
这部剧中的人物,浓墨重彩的人物,一如《安魂曲》,也只能在伟大的荒诞派剧作家之贝克特后才有可能幸运地出现:一个街头寻客的娼妓,一对一贫如洗的乞丐父子,而故事之原点,居然起始于在现代之戏剧兴起之前不可能去刻画的"性",由此而又激荡出了被社会遗忘乃至抛弃的底层人的内心苦难与垂死挣扎。它以揭示和洞察浮游在享乐时代表面上的丑陋与肮脏,从而折射出了由于社会阶层身份之分化所导致的不公与非义,而支撑这些人物得以苟延残喘的,仍然是那个遥不可及的虚幻之美梦(在剧中,此一虚幻之梦,被命名为“俄亥俄小姐”———它其实从不存在,仅为一南柯一梦,但却给予了剧中绝望的人们以微茫的希望。
它是黑色的,也是可怜而又荒诞可笑的,但它却像一把无比锋锐的尖刀,在割破了用以掩掩世间无耻与邪恶之帷幕时,也让它祼露出了不忍直视的阴冷的真相,亦如残酷地在搅剜着我们翻江倒海的内心,让人读着欲哭无泪。
有好几次,我不得不让自己中途停下来,放下这本书,缓上一口气,静静地点燃了一枝烟,烟雾瞬间把我包裹了,我想让被列文的文字搅扰且刺疼的心绪,稍稍地获得一丁点儿平复。只是那么一点儿。
人世之梦,真的被无情地撕碎了,击穿了,在凄风冷雨中飘摇,一如目下窗外传来的呼啸的狂风,冷冽刺骨。我战栗着,想推拒迎面袭向我的这种阅读感受。
我能拒绝得了吗?即使我能拒绝继续阅读这本书,可我能拒绝的了我每天都必须去面对的现实人生吗?
纯粹的艺术是从不撒谎的,就像列文由一个个文字所构筑的,这个以文学的名义存在的世界————它从来就不是滞留在纸上的世界。
哦,不是!它就是我们必然在遭遇着的真实的、赤裸裸的世界。对于列文而言,他不过只是先把你从梦中摇醒,然后告诉你,看那,这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我所做的,只是用上帝赐予我的这把刀,拆除这个世界的伪装与虚幻,唤醒你们睁大眼睛去看着它,从而不被它所欺骗和讹诈。你只有在认清了它时,你才知道怎么去设法改变,这就是自我救赎。
列文,这位"以色列的良心",似乎被赋予了一双上帝之眼,若非如此,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能做到像他这般博大、深刻、高远,充满了如上帝一般为芸芸众生的悲悯与苦痛。


汉诺赫·列文(1943 –1999)
是的,列文的作品、尤其他的《安魂曲》,达到了《圣经》般的高度与深度。
《旅人》是《安魂曲》中列文的最后一剧,也是第一次在他的剧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此前的三部剧,仅是一围绕着寥寥数人展开的,相对于他另外三部小剧场式的戏剧,《旅人》的主题则显多少有些散乱,不像其它三剧那样能够一"语"中的。
但在这里,依然笼罩着一抹末世般的悲鸣,几乎可以说,这就是列文戏剧的基本底色了,若一旦失去了它,也就将失去了列文作为列文的戏剧底色,它烙上了一道极其鲜明的列文的印记,一如签上了他名字。
《旅人》再次显示了列文对死亡的高度"迷恋"———不仅仅是海德格尔式的"向死的存在",在此,死亡也不仅仅如同《圣经》所昭告的那般,是一可让有罪的人从中获救的彼岸。
是的,列文是将他笔下频频出现的死亡意象,设定为一个美好的寄托与梦境,但与此同时,“死亡”在列文的戏剧中又是以戏谑、嘲弄和反讽的方式来予以反映的,于是单纯地,以彼岸作为生之寄望在这里一下子变得滑稽可笑了起来;亦由于此,彼岸之魅,似乎也被列文式的黑色幽默一并消解了。
但又好像没有那么的简单。在列文的戏剧中,他似乎认为"死"才是人生中最真实的长眠(活着只是人之受罪和自欺),是对这个自身之原在(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回归与还原,是那些对于生活无望的人(他写的人物,都是处在绝望中的社会边缘人),在生活中,他们唯能展望的就是那个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之梦境,但那个彼岸,又因了它的那个遥不可及,只能是通往最后的死亡之境。
列文究竟在他的戏剧中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尽管他对其笔下可怜又可笑的小人物们竭尽嘲弄,但你丝毫不觉得他在居高临下,相反,在他的黑色幽默背后隐藏着他深切的同情、怜悯与哀叹。不仅为他们,也像在为我们和这个丑陋的世界。
列文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疑问、困惑的,也充满了一种怨愤乃至敌视,他似乎觉得上帝承诺给每个人应享的公平与正义是一巨大的谎言,他很想把被这个肮脏的世界"窃"走的、曾许诺过给穷人的好东西还给那些处在绝望中的人,但他又深感无能为力,他只能仰天长叹了!
我一边读,一边在想,列文身上的这种浓郁的悲剧性从何而来?少年记忆?是的,他在贫民窟长大,因穷曾一度辍学,甚至有可能还受尽了屈辱。但在压抑中长大成人几乎是肯定的。那么,这段经历显然铸造了他的人生。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他的那种"圣经"般强大的天道良心缘于何处?
应该是犹太教了。毕竟其父是以色列著名的拉比,父亲走时,列文已经12岁了。宗教之精神氛围一定浓烈地环绕过他的成长之路,从而让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蕴含了悲悯与拯救的主题。只是发出悲悯之声的这个拯救者不是来自上帝,而是——而且只能是,我们人类自己。
这也就是列文戏剧独一无二的伟大之处。在其他具有宗教情怀的艺术家身上,作品也会显现一个上帝之在的,比如贝多芬与托尔斯泰,马勒与陀斯妥也夫斯基,前者是上帝之荣耀足以让人类战胜困境,而后者,乃是哀叹人类在离弃与背离上帝,走向了末路。
而这一切在列文的作品中都被扬弃了,上帝回到了自身,不再是作为一个"祂者"而存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神,那不过是一幻象。拯救在己,无论你身份高低,卑微如是,你都要在现实的苦难中最终发现和找到属于自己的救赎之道,尽管现世时常是那么的令人绝望,但人,应当永不放弃自我拯救的希望。
列文无愧为以色列良心,不,他也是人类的良心。
(本文原标题:《<安魂曲>的安魂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