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光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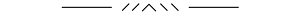
食物中的当代微观小史
文 | 西门媚
要说对于挑嘴的我来说,北京什么最好吃,我肯定会想到煎饼果子。
曾有一段,连着吃煎饼果子,吃到后来,再也不想吃了。但还是觉得,这是北京最好吃的东西。因为它的刻痕太深了。
1995年的时候,忽然得了一个机会,去一个大媒体。关键是,是在日思梦想的北京。
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所在的成都某小报,正好面临关张。我马上收拾行李,连最后一月的工资都等不及领,就飞去了北京。
那时已经十一月下旬,成都已经进入初冬。想着北京肯定更加寒冷,没去过北方的我,里三层外三层地穿着,我最厚的外衣毛衣全都上了身,里面裹着的是一颗兴奋热烈的心。拖了一个超大的行李箱,连床头台灯都带上了。毕业不久的我,这些是我全部家当。带上这些,是我对北京的全部诚意。
下飞机,坐大巴,下到复兴门。发现复兴路跟复兴门不是一事,又打车。看着计程表一阵猛跳,心也猛跳。司机告诉我说,到了。我拖着行李箱,下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
门岗打电话进去,等了一刻来钟,出来个女孩。女孩说她叫小鑫,来接我去编辑部。她给门岗解释,说,这是我们的客人。
客人?我听着就心里打鼓。不是说好我是来工作的吗?
在大院走了很久,到了后院的一幢小楼。进到楼里,看见了这家媒体的牌子。牌子和办公室都不大,但是口气很大。叫“世界XX年鉴”。
小鑫领我去见总编。总编是个邋遢的中年男人,头发上是油垢,牙齿和手指上是烟垢。他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似乎真是不知道我要来工作。
我着急了,说,是陈主任叫我来的。然后说了一串名字。这些名字,就是介绍我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转弯抹角的关系,介绍了这份工作。听说陈主任讲,马上来工作,我们这儿还分国内部和世界部,国内部又分文化部、经济部,等等,条件好,还有宿舍。中间传话的朋友对我说,赶紧去,这么好的工作,好难得。
周总编听了这一堆名字后,又听我转述陈主任的话,似乎明白过来了,说:“小陈出差还没回来,你等几天吧。”
他语焉未详,也没说让我工作,还是不工作。看着我和我的大箱子,他叫小鑫带我去办公室。
看来小鑫就负责办公室工作。我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无事可干,室内暖气烧得很足,我学别人那样,脱掉外套,但里面一层又一层的毛衣不好脱,身上燥热难受,再加上心中忐忑,百般不自在。
小鑫抱了几本的精装书过来,说:“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年鉴,你先看看。”
这些红皮大书,很厚很沉,外壳上烫着金字。里面翻开,前面一些难懂的文章,主体部分是企业名录。
在成都的时候,我也见识过一些媒体了。那几年,正是媒体走向市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我见识过的小媒体,好些并不靠内容或者发行为生,单为广告存在。
拉到广告才印,印出来直接给客户,并不在外发行。这样的“媒体”,没有读者,没有媒介作用,客户有的是为了私人得到丰厚回扣,有的是为了借公款为个人扬威,有的是为了讨好上级单位。
我心里越来越疑惑担忧,终于熬到下班时间。小鑫过来对我说,我老公正好出差了,你住我家吧。
我像看救星一样看着她,跟她回家。她家也在部队大院里,一间小小的宿舍,中间一张双人床。
小鑫其实大我不到一岁,但非常能干,这样萍水相逢,却对我热情照顾。我住在她家,她烧饭给我吃。还陪我去银行开户——那时银行之间不联网,去外地得带着现金去,重新开户。又陪我去买羽绒服——四川没有暖气,穿衣习惯和北方相当不同,主要靠多层毛衣取暖,外套并不厚,所以到了北京,就得按北方的习惯来置衣。后来和小鑫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是另话。
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并无具体事情,总编老周拿一堆企业名单,让我抄到信封上。信封里装进广告,宣传这“年鉴”如何有影响力,进入了有什么好处。
几天以后,“陈主任”出差回来了。呆了这几天,我差不多明白了。所谓出差,也就是去到“下面”跑了一圈,拉广告。北京之外,皆为“下面”。但他去的下面,是真有点“下面”。大城市已经跑完,大企业也拉得差不多了,他们最近在重点攻克一些小煤矿。“陈主任”在内未必是主任,但在外面,“编辑部主任”的名头是必需的。他告诉我窍门,他拿着主管单位的介绍信,先是对接省里建立联系,然后再下去,就比较好办。我明白,他们是一级级地拉大旗做虎皮。我也就知道,这介绍工作的误会是从何而来的了。
陈主任是四川人,回四川探亲,也延用这些说法,我朋友的朋友就信以为真,替我找了这份好工作。估计他看着弄假成真,也不好说破,只好任由事态发展。
明白这点我就急了。这样拉广告的事情我做不来,也不愿做。他们有男生宿舍,却没有女生住的地方。小鑫的老公出差已回,她家里再住不下。
我搬到办公室住下。办公室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半夜暖气一烤,沙发背上,暖气片上,会爬出许多小蟑螂。我平素最怕这些虫子,但在这些天,形势所迫,居然也能睡着。
我开始积极联系工作。离开成都时,朋友熟人给我开过一些我的名单,让我有困难可以去找他们。这是我的路条,是真正的护身符。打了电话,就挨家拜访。差不多每天都向老周请假出门。老周心里肯定明白,我不合适他们这里,但他不为难我,也不赶我走,有一晚某醉汉还来推过我办公室的门,吓得我一晚不敢睡,第二天我告诉了老周,老周还去帮我打了招呼,从此相安无事。
那时,每天早上,我出了大院的门,就到路边,去买一只煎饼果子。
小贩照例问一声,要不要辣?要!我答。
然后看着他熟练地把面糊舀到锅上,转成圆形,再打上鸡蛋,加上辣椒酱,加上别的配料。
当然要辣椒啦,在北京吃得没有滋味的时候,煎饼果子的辣椒酱也能解解乡愁。

鸡蛋也给人安慰。如果是中饭的时候,吃煎饼果子,就要求多加一个鸡蛋,顿时觉得自己很会照顾自己,吃得很有营养。
大半个月跑下来,很有成效。先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某大报当夜班编辑。这份工作,没有“指标”。那时,北京的媒体,没有指标就不能正式调入,只能临时聘用。干的活比别人辛苦,收入却只有别人的几分之一。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好的选择。接着又找房。都解决好了,可以去上班了,才跟老周辞职。
老周一点没为难我,甚至还给我结算了这半月的工资。这让我有些意外。我到的时候,并没跟他谈过工资,甚至他也没承诺给我这份工作,后来,我多数时间都在外面跑工作找房子。
那时,我接触到的老周手下,好多对老周都有微词,觉得他抠,觉得他精。我不喜欢他做的事情,但他对我,真是宽容,并无计较。
我后来再没见过老周,十多年后,听小鑫讲,老周已患癌症去世,去世前,他的公司已经远不如1995年。
【作者简介】
西门媚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新闻三部曲”,随笔集《纸锋》《心怀野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