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妈给我读童话故事,最后一句话总是:“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总是爱问:然后呢?
我妈虽然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但对我向来是很不耐烦:“然后就完了呀!”
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妈说的是婚姻的常见情况。
再美好的爱情,真正走入婚姻,走进生活,就会掺杂进太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在同一屋檐下,山盟海誓不能当饭吃,公主和王子遇到的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最夸张的例子就是李敖和胡茵梦。当记者问他们的婚姻为什么只持续了三个月,李敖回答: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有一天,我无意推开没有反锁的卫生间的门,见蹲在马桶上的她因为便秘满脸憋得通红,实在太不堪了。
这句话实在太混蛋了,当然,要是被阳子听见,肯定会告诉自以为是的李敖老师:一份幸福的婚姻的开端,是坐在丈夫刚刚大过便的马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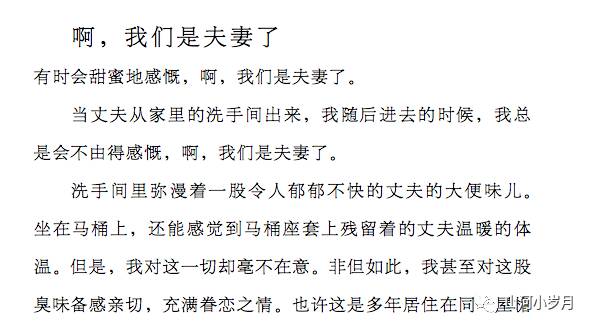
我是在去三亚的飞机上读完《我的爱情生活》的,全程三个多小时,我一直在哈哈大笑,阳子是我见过的最擅长把这些夫妇细节写得有趣而温馨的美女。

难怪,荒木经惟爱了她一辈子。
* * *
对,就是那个,你们都认识的荒木经惟。
一提起他,我们总是会想起:裸体的女人。有一年去东京,遇到田原老师,他热情地要带我去荒木家:“他会很高兴给你拍照的!”
秒怂如我,脑子里想起来的画面,是这样的:

可是,荒木镜头里的阳子,是这样的:

对初次见面的人,荒木会这样介绍阳子:“这是我的爱。”
他甚至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的摄影生涯,是从和阳子的相遇开始的。
他们是如何相遇的呢?
电通广告的打字员青木阳子是有名的美女。在公司工作的第二年冬天,20岁的阳子被通知,因为要做企业内刊,需要拍摄一组照片。她和打字室的同事们走到一个房间,见到了一个“穿着一件织得粗粗拉拉的、好像是手织的黑色对襟毛衣,脖子上印度产的项链叮叮当当地响着”的男人,这时候,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将是她命运里的那个人——荒木经惟。

▲正中间不笑的那个是阳子
全部拍摄之后,荒木叫住了阳子,表示想要拍一张阳子的个人照。对于他们的初次见面,阳子记住了一句话:
“啊,不要笑,刚才那个不高兴的表情就很好。”
阳子愣了一下。
“对了,你不笑的时候,表情很漂亮。”
听了这句话,二十岁的阳子忽然心情很激动。
* * *
阳子和荒木的人生,简直是两条平行线。
一个是听话的乖乖女,一个是离经叛道的摄影师。这两个人的相爱,源自乖乖女心里的疯狂小念头。
永远都是那么听话,祖母让干嘛就干嘛,老师希望读什么就读什么,其实,阳子有一颗的内心。而荒木,则是那个激发她心底那点小秘密的开关。比如,按照他的指示,光脚穿着木屐从地铁月台的厕所里出来;拍照时渐渐摆出一些不文雅的姿势,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24岁的阳子对母亲和朋友的不安置之不理,嫁给了31岁的荒木经惟。他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在婚宴上放着新郎给新娘的裸照,阳子的祖母气得回家病倒,在被窝里不停地叹气:
“竟然和这样一个够呛的男人结了婚。该怎么办才好呢? ”

嗯,这个男人,确实有点够呛。
给朋友送的新婚礼物是一个剑玉——就是下面这个东西。这不算啥,关键是,他专门在木球上画了“乱蓬蓬的阴毛一样的线条”,结果,被拒收了。他对阳子说:“好不容易像这样连毛都给他画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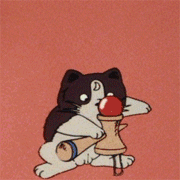
不跟妻子商量,就辞掉了电通的工作。回家买了一瓶红酒,对太太说:“今天有好消息,我辞职了。”最艰难的时候,家里存折上只有六千日元。
电影《东京日和》曾经描述了荒木和阳子的这段生活。为了养家糊口,阳子曾经去朋友的公司兼职,走之前帮他把早饭做好放在冰箱里——他居然要花一段时间,才适应要自己把饭菜拿出来热一热。
这么够呛的男人,阳子却一直致力于发现他的各种可爱。
* * *
她喜欢他给她写的信,信里夹着枫叶:“因为外景拍摄,我来到架着小木桥的河边。如果阳子在这里,我们不要手拉手,也不要相互拥抱,只要两人肩并肩地 站在木桥上就好,阳光温柔地包围着我们。 ”
她喜欢他给她拍的照片,哪怕是疯狂而限制级的,“比起看到我喝醉了酒和旁边的男子接吻,在一旁大发雷霆的丈夫,我更喜欢在接吻的时候,一边说着‘舌头再伸进来点’,一边拍照的丈夫”。

她喜欢他得了痔疮,要自己给屁股打膏药。因为害羞,他把房间的灯关了。后来,朋友介绍他去针灸,他治疗回来,夫妻两个人的对话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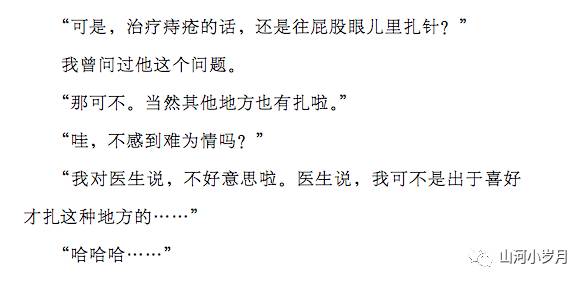
她也感激于他的体贴。婚后,阳子不会做饭,一开始只能做煮毛豆。朋友们说:“煮毛豆也是菜吗?”荒木在旁边给妻子解围:“也是菜啊!”
她喜欢他,因为在结婚之后,她变成了自己喜欢的阳子,他也变成了自己喜欢的荒木经惟——在交往中,我们变成了自己更喜欢的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但他们之间,并非没有过隔阂。

一家杂志社策划了一场关于性工作者的拍摄,荒木接到的任务是去美洲,和这些性工作者发生关系,然后再一一拍摄。出发之前,杂志社的编辑邀请荒木和阳子吃了一顿高级西餐。
编辑把红酒一饮而尽说:“夫人,没有关系的,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把您丈夫平安无事地送回来的。”
荒木娘娘腔地回答: “一定要带上很多抗生素才行啊。”
两个男人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吃嫩煎肥鹅肝。
再大度的女人,遇到这种场合,也会大怒不已吧。阳子当时非常生气: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对他与别的女人(而且是 和好几个人)睡觉一事(无论是多么专业的外国人),我是不 可能做到完全心平气和、无动于衷的。一想到丈夫与那些陌的女人发生关系,我就忍不住怒火中烧。回来后,绝对不让他捧我。即使一年不做也没有关系。啊,真是脏死了,讨厌!
——《我的爱情生活》
丈夫出发了,时不时寄来一些明信片,只写了一些在宾馆的游泳池畔喝着冰镇银子弹(Coors)啦,在海岸边抹上厚厚的擦身油啦,诸如之类的事。然后,阳子说,“明信片里只字未提女人的地方, 反倒让人感觉弥漫着一股女人的气息。 ”
丈夫回来了,阳子有一堆问题等着质问丈夫。
然而,渐渐地,问题变成这样了:
“和外国女人做,感觉怎么样?”
“毕竟是工作嘛,很够呛的,不可能有什么愉快的。”
荒木是细心的,他知道阳子虽然故作大度,心里仍然介意这件事。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出发去箱根泡温泉,荒木说:“不如在温泉里把那儿消消毒吧!”(他们的温泉对话又黄又好笑,建议去看一下《我的爱情生活》这本书)

阳子忿忿不平地对荒木说,下次她也要出轨,然后让荒木给她拍现场照。
荒木的回答是:
“是嘛,那么,我从后背拍吧。”
“为什么?”
“如果在正常位置拍的话,乳房会显得太平坦了呀。不过,本来就很平。”
* * *
1989年,阳子开始连载《东京日和》,写了三篇,就被发现患上了子宫癌。
病情发展很迅速,1990年11月26日,医院通知荒木,阳子病危。他匆匆买来阳子最喜欢的木棉花,放在她的床头。

第二天,阳子去世,荒木说,阳子弥留时,他对她说了最后的话:“谢谢。”
然后,他忽然发现,床前的木棉花开了。

他几乎拍摄了阳子从患病住院到故去的每个阶段:在医院里,插着管子的妻子和他与紧握着手、棺木里沉睡的妻子……最后送灵出殡的时候,荒木忽然说:
不烧送神火 不让你回去。

阳子去世之后,荒木曾经打算上吊自杀。他的好朋友为了鼓励他重新振作,特意组织了一个“鼓励会”。站在台上的荒木说:“我现在好不容易能够心情稍微宽慰一些地回味那份悲伤,你们就不要鼓励我了,让我尽情地悲伤吧。”
阳子去世两年半,荒木在阳台上抱着猫咪奇洛,按下了这张照片,他这样写道:
东京的太阳就照在外边的阳台上,就象你在的时候那样。猫懒洋洋的爬在椅子上。桌上的烟缸架着支没有抽完的香烟。旁边是你的照片。对面仍然没有高楼。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站在那里,可以看见太阳下山。
阳子,你一直都没有告诉我,我说的很多话你都听不到;其实很多话我只是在心里对你说。
阳子,那天你对我说,“你不要对我太好。”当时你穿着和服,就站在不远的地方。
阳子,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一个孩子。
阳子,你曾经离开我三天,那三天我在想你会不会永远的走掉,不再回来。如今,你已经离开了2年半。

忽然想起归有光的一句话: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东京日和》里,荒木演列车员,和好基友竹中直人演的自己,望着中山美穗演的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