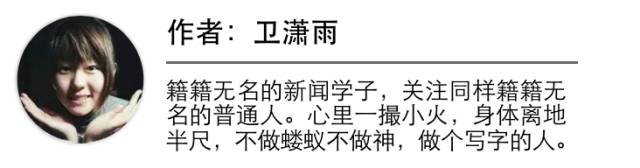《怒》剧照
http://mmbiz.qpic.cn/mmbiz/yqVAq ... krfPw/0?wx_fmt=jpeg); background-color: rgb(241, 241, 241);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background-position: 1% 5px;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no-repeat;">聊QQ、玩别踩白块和开心消消乐,看守们从不管陈嘉琦,也没要求过看她的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然而,她同样没有想过向外界求救。
陈嘉琦跑了。
失踪86天,前后落入十个人、两个团伙手中,辗转赞皇、天津、邯郸三地被逼卖淫,两次回到了离家五公里的县城、又再次被抓走。整整86天后,才终于跑回了家。
跑之前,陈嘉琦在学校总是受人欺负,班主任不管,在家也没人喜欢她,好几年的生日都是一个人过。
跑回来后,陈嘉琦把自己闷在房间里大半年,吃饭、睡觉、看恐怖片,几乎不怎么出门,再出来时仿佛换了个样子:不再和学校里的朋友联系,开始反抗控制了自己16年的父亲,纹身、交“社会人”朋友、打扮自己。在快手上,她有三千多个粉丝。
86天以前,陈嘉琦丢了。
初二刚开学,她就不去学校了,每天在外面上网。5月,陈嘉琦告诉爸爸,自己要去同学家写作业,转头就进了网吧。
在网吧,她认识了张文强和另外两个男孩。几个人玩高兴了,就一起离开网吧,在县城里的宾馆开了个房间,住在一起。
在宾馆玩了三天,钱就没了,张文强张罗着让陈嘉琦卖淫赚钱。陈嘉琦不乐意,可他们不让她走,吓唬她、骂她,后来,陈嘉琦才松了口。张文强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朋友,第一单生意成交了,她一整晚都没睡着。
后来,张文强带着她去了天津,把她交给了邯郸的另一个团伙。辗转赞皇、天津、邯郸三地,陈嘉琦一直住在安排好的房子里,每天都有人按时送饭,吃了饭就歇着,睡觉、打牌、看电视、玩游戏,到了晚上就接待客人。做得多了,后来也不会睡不着了。
这是陈嘉琦刚跑回来的时候,陈浩带着女儿去公安局做笔录,这些是我从笔录中得知的信息。陈浩说女儿说话时一直“摇头晃脑的”。我听了当时的录音,她声音小,只会“嗯嗯啊啊”地回答,即便问到最隐秘的部分,也听不出来语气上有什么起伏,至于更多的细节,她什么都记不起来。
在天津的时候,住的地方不能洗澡,尽管每天都要接待客人,但每隔三天才去洗浴城洗一次。“会觉得脏,要洗澡吗?”我试探地问她。她说,“没。”
陈嘉琦表现得麻木,像个不相干的人。在被控制的86天里,有两次她都回到了赞皇,离自家所在的村子五公里、打车二十块钱就能到。
“为什么没想着回家?”我问她。
“没车了。”
“有没有想给爸爸打电话?”
“早忘了。”
“公安局离宾馆几百米远,有没有想求助?”
“早忘了。”
“想回家吗?”
“早忘了。”
和她一起被控制的女孩给家里打了电话,走了。陈嘉琦又去了网吧,在网吧遇见了前男友,跟着去了永丰村。结果,她又落入另一个团伙手里,被控制在永丰村继续卖淫。
● ● ●
永丰村距离赞皇县城,开车六分钟就能到,如果直接回家,也不到二十公里的距离。陈嘉琦没被完全控制,至少她没被绳子绑着。她经常跟着这些人一起去县城的餐馆吃饭,去的都是熟悉的大馆子,饭点的时候,餐馆满满当当都是人,上厕所时也行动自由。
可她根本没想着跑。
在邯郸的时候,陈嘉琦想买个手机,看守带着她去了赌场对面的手机店,一千多块钱挑了个,用她卖淫挣的钱结了账。手机没有卡,但能连着无线上网,陈嘉琦一直用手机上QQ,我问她,“有人在QQ上问你去哪儿了吗?”
“没。”陈嘉琦聊QQ、玩别踩白块和开心消消乐,看守们从不管陈嘉琦,也从没要求过看她的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但是她没想过向外界求救,理由是“我不知道我在邯郸哪儿,怎么让人来救我?”她甚至没告诉别人自己身在邯郸。
事实上,这成为了之后警方判决的重要依据,警方相信,她是自愿的,至少很大程度上如此。她只是不想回家,其他干什么都行。
● ● ●
永丰村团伙的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打她,九月七号,陈嘉琦又挨了打,用镐靶打身体,用鞋扇脸。陈嘉琦回家的时候,脸肿得不成人样,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陈嘉琦这才想跑了。
那天,看守开着一辆面包车带着她去县城吃汉堡,傍晚六点多,车停在了妇幼保健院的十字路口,趁看守下车买东西,陈嘉琦拉开门跑了。外婆家就在附近不到一百米远,她跑上四楼敲门,家里只有外婆和还不满十岁的小妹妹在。
陈嘉琦给爸爸陈浩打电话,让爸爸来救她。外婆喊了两个邻居,拿起扫把棍跑下楼,三个人在楼下堵着追来的看守。
从村子里到外婆家,陈浩听孩子打了电话,哆嗦着上了摩托车,只用了十多分钟就赶来了。到了楼底下,遇到了拿着棍子的外婆,外婆让他快去救孩子,一进去单元楼,就看见陈嘉琦在楼道里探着头往外面看,看到了爸爸,她跑到陈浩身边,“爸爸快走,他们看见你就把你害了。”
失踪86天,陈浩这才见到女儿。
陈嘉琦怕爸爸打她。我问她,“爸爸打你是什么理由?”
“不回家。”
“不回家就打你?”
“嗯。”
“那你为什么还总是不想回家?”
“不想回。”
在弟弟的记忆里,爸爸打姐姐不需要理由。有时候是因为做饭不及时,有时候是因为和别人拌嘴,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她总不回家,九月刚逃出来,陈浩就狠狠打了陈嘉琦一顿。
每次打姐姐,陈嘉华就缩在一边,听见姐姐又哭又喊,也不敢进去拦着爸爸。爸爸也在妈妈面前打她,就在临街的铺子里,用晾衣杆打,打到妈妈把他赶出去了才收手。
奶奶觉得,是爸爸把孩子打傻了,小时候陈嘉琦也挺机灵,和人亲近,现在有时间都在炕上躺着,也不干活,也不说话。
这个家庭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小,陈浩在做手工香肠的生意,做好的香肠都要用保鲜膜缠起来,孩子们都争着帮他干活。每天天不亮,陈浩就要出去送货,等天亮以后回来,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饭,端到身边让他吃。
陈浩对两个孩子也好,陈嘉琦还在私立小学读书的时候,他总带着东西往学校跑,后来学校里的人都认识他了,一看见他出现在门口,就说,陈嘉琦的爸爸又来了。
陈嘉琦九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妈妈跑到两个孩子面前告诉他们,以后妈妈不管你们了。奶奶告诉她和弟弟,妈妈要走了,你们快哭,别让妈妈走。弟弟扑腾跪下就哭了,陈嘉琦不哭,死死地站着。她性子像爸爸,犟,不听话,有什么事死撑着。
妈妈还是走了,在县城里又结了婚。
● ● ●
离婚以后,爸爸不让妈妈去看孩子。
有一次,孩子病了在学校卫生所输液,妈妈挺着怀孕六个多月的大肚子去看,结果被奶奶拦在门口,带的东西都摔在地上。在两个孩子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缺席的。上中学的时候,妈妈在学校门口看见了弟弟,喊他的名字,结果他吓得一溜烟跑了。
而爸爸则是家里的权威,小的时候,爸爸每周都要和他们两个坐在一起聊天,往往是爸爸讲道理、姐弟俩听着。除了说教以外,爸爸很少平等的和他们有什么交流,记忆里也从来没有夸奖。
那时候,陈嘉华班里只发了条两红领巾,他是其中一个。等回家高兴地告诉爸爸,爸爸问,“老师为什么给你发红领巾?”陈嘉华说了一大堆,他表现好、听话,结果爸爸说是“因为老师看到你的脖子黑,像轴承一样,他看到了吃不下去饭,给你红领巾让你把脖子围起来,看不到,就可以好好吃饭了。”
在家里,没有人关注陈嘉琦。我问陈浩,“姑娘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他想了想,“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我问弟弟,“你喜欢你姐姐吗?”
“不喜欢。”
“会和你姐姐说知心话吗?”
“不说。”
“姐姐不在了你是不是特别慌?”
“都是平常的样子。”
“心里也没担心?”
“那是有点。”
“你有问过姐姐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她都说‘你管呢!你不要管。’”
“姐姐在家和不在家的区别是什么?”
“多个人。”
初中的时候,陈嘉琦想去县城一中读书,差了三十多分,爸爸找关系把她送了过去。结果成绩不怎么样,反倒被人欺负了。
有次学校放假,陈嘉琦一直没回来,爸爸找不到她,情急之下报了警,后来在同学家找到了。爸爸着急,夜里九点多,把她拎到街上就打,打得特别狠,同学跪下来求他,“叔叔你别打了,她不想上学,学校总有人欺负她。”
“你不能告诉老师吗?”陈浩问。
“告诉的话还会被打。”
陈嘉琦说她不想去上学了,但爸爸要求必须得坚持到初中毕业。
到了三月底,陈嘉琦就不去学校了。她瞒着爸爸,整天在网吧上网、看电视剧,到了周末就说要去同学家写作业,一直瞒到了5月失踪的时候。
陈嘉琦至今都非常抗拒谈论学校里的事情,她否认了自己曾经被人欺负,不想上学也只是因为“同桌不读书了,觉得上学没有意思”。她拒绝再和过去学校里的朋友们联系,交的新朋友也都是那些不上学不工作的人。
学校老师则说,如果陈嘉琦真的被人欺负了,“班主任应该知道,当时应该帮她处理了”,事实上,我试着联系她中学时期的班主任邓翠萍,去了办公室几次都没能见到她,所有的电话都被挂断了。在短信中,我表明了来意:“现在嘉琦不上学,她爸爸很着急,希望能联系您找找之前的朋友劝劝她。”也没有回音。
当然,这倒和班里其他学生的情况相符——初一刚开学,班里有七十多个人,后来有的不念了,有的转班了,初三正常高考的只剩下四十多个。除了分数以外,班主任不给他们倾注多余的关心。
我去找曾经带过她的几位老师,只有一位老师在听了陈嘉琦的名字后絮絮叨叨讲了几分钟,说她是个内向的姑娘,话不太多,成绩处在中下游,没什么出彩的地方。聊到后来才发现,他说的那个姑娘比陈嘉琦大了三届。
“喜欢邓老师吗?”我问陈嘉琦。
“不喜欢。”
“喜欢小学的老师吗?”
“差不多。”
“小学成绩好和老师有关系吗?”
“有。”
“那个时候还挺喜欢学习的?”
“嗯。”
孩子丢了以后,陈浩到处找孩子,也报了警,可派出所也没那么多人,不能跟着他满大街找孩子。
有次,有人告诉他,嘉琦就在县城的宾馆里,陈浩马上骑着车赶过去宾馆里找孩子。
还有一次,听说孩子在邯郸,陈浩、孩子的妈妈和另一个同被控制的孩子家人,四人一起打车去了邯郸,花了四百多块,司机开车一直绕路,就是不肯上高速。陈浩着急,加钱让司机从高速走,想着能快点去救孩子。晚上八点多到了邯郸,绕了一圈,什么都没找着。
这是他离陈嘉琦最近的两次,孩子依旧没找着。直到9月7日,陈嘉琦自己跑回来。
陈嘉琦回来以后,邯郸团伙、永丰村团伙的两个主犯分别判了十二年、十年零十个月,其余八个从犯各判处了拘留和罚款,没几天全放了;派出所负责这一案件的队长也受到了行政记过处分。但陈浩觉得这还不够,对方应该被降职。他实在咽不下去这口气。
2016年初,陈浩托远房亲戚找了个相熟的律师,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来找律师一次。律师告诉他,公安已经处分,法院也已经判决,再追责很难,建议走民事诉讼争取赔偿,陈浩不愿意。
后来,也没和律师商量一声,陈浩就直接就跑到北京去上访了。2016年3月去了一次,2017年又去了一次,舍不得一百多块钱的住宿费,在北京的晚冬,缩在胡同里挨了一夜,最后,还是县里的人把他接了回去。
7月,陈浩买了电脑,花了1600块,再加上500多一年的宽带费,这是他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在电脑上找记者的联系方式,16开的纸张,订成了一厘米厚的一本子,记者们的电话、QQ、邮箱,按名字、单位、联系方式依次排好,一页四十多个,杂志、报纸、公众号全都有。
有了联系方式,他开始挨个给记者发消息,等着人家来报道女儿的事儿,希望能推动案子重审。
陈嘉琦则抗拒媒体。因为媒体来了,村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了她的事,出门的时候,她总是觉得有人在自己身后指指点点,“说我被卖了,陪着别人睡觉这样的话。”还有人专门告诉她弟弟,“千万别学你姐姐那样。”
2016年底,有记者从北京过来,陈浩带着记者来家里,当天正好赶上女儿的生日,他买了个蛋糕带过去。进了房间,看见陈嘉琦正躺在床上,他高高兴兴地迎上去祝女儿生日快乐,陈嘉琦却没什么反应,就说了句“放这儿吧”。
● ● ●
和陈嘉琦聊天的时候,我意识到她抗拒回忆,也没再继续问。临走时,陈浩紧张地问我,“今天采访的怎么样?”我告诉他,“女儿比较抗拒回忆,这块就不问了。”“那哪行,你们报道,该问就得问。”陈浩说。
当晚十点多,我又接到了陈浩的电话,他说自己已经成功说服了女儿,“我就拿我找她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手上这个伤反复劝她,她现在答应了可以回忆这个事情。”然后邀请我,“明天你再回来,专门采访她被拐走的经历。”
第二天,我再见到她的时候,陈嘉琦缩在角落一张椅子上,说什么也不肯再坐近一点,我问了几个问题,没忍心继续问下去。陈浩表现得相当热心,不断向我确认采访的资料够不够。
离开的那天,他特地带着女儿去车站送我,陈浩站在巴士前挥手,陈嘉琦陈浩低着头蹲在地上。我能感受到,陈嘉琦一直抗拒回忆那86天的经历,但是她也不敢反抗父亲;而父亲似乎并不在意女儿的想法,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奶奶也告诉陈浩,赔偿争取得差不多了就算了,她不愿意再追究了。可陈浩不答应。
“你再弄就把我气疯了。”奶奶告诉他。
“你不叫弄就把我气疯了。”
女儿回来以后,除了上厕所外,整天就在家躺着,饭端到床边了也不吃。陈浩几次提出要带她去看心理医生,陈嘉琦害怕得不敢回家,悄悄告诉弟弟,她怕一回去就被爸爸送进去精神病医院。
但陈浩执意觉得,女儿心理已经扭曲了,必须得去看心理医生。以前,女儿听话,告诉她办什么事情绝对不说二话,但是经过了这个事情以后,和她说什么也不听,就算约好的事情都可能突然反悔。发火、摔东西、打人,爸爸、弟弟和奶奶都挨过她的打。
陈浩在家里准备了一条铁链子,说陈嘉琦再失控,他准备把女儿锁起来。
孩子找到了以后,陈浩每天还是魂不守舍的,一次做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胳膊伤了,小臂被卷进机器里搅,肉都没了,就剩下一层皮盖着骨头。受伤后,全家人一起陪着他到手术室门口,哭得不成样子。但陈浩瞥见,陈嘉琦笑了。他更加确定,孩子心理扭曲了。
陈嘉琦决定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她告诉爸爸,她想纹身。
“不行,”陈浩马上回复,“正经人家的孩子没有纹身的。”
“我已经做好了。”
陈浩一下子火气就起来了,“已经做好了,你告诉我干嘛!……你就是不认我这个爸爸。”
后来再见到陈嘉琦,她右胳膊上已经有了一块纹身,爬满了半个胳膊,那是个艺伎图案,在纹身店里选的。
陈嘉琦新交的朋友都是些“社会人”,出门叼根烟、烫泡面头、刘海垂下来盖着一半眼睛,QQ里一千多个好友,走在县城,一路上都有人和她打招呼。
我们一起住在宾馆里,夜里十二点多,她一个人出了门,坚持要去另一家宾馆赴朋友的约。后来又在网吧看了一晚上的恐怖片,凌晨四点多才回来。
她似乎换了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曾经在学校里受欺负的角色,对于夜晚、宾馆、陌生人和网吧,这些可能唤起创伤回忆的部分也毫不在意。
● ● ●
对于女童受性侵案件经验丰富的律师李莹告诉我,遇到性侵后,有的人会有强烈的应激反应,会精神崩溃、会沉默寡言,甚至有个孩子丧失了表达能力,连数数都不会了。但也有孩子就像陈嘉琦一样,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依旧正常的生活、社交,也不惧惮回到可能唤起创伤回忆的场景。但实际上,陈嘉琦只是把创伤藏起来了,但那不代表伤不存在。
然而,她们的开朗也仅限于浅层的交往,曾经的创伤回忆会重新塑造她们对亲密关系的看法。
这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到陈嘉琦的时候,她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两个人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脚链,还在右手手臂纹了同样图案的纹身,这是她现阶段最好的朋友。事实上,她们才刚刚认识四个月,我问陈嘉琦,“她知道你以前的事吗?”
“不知道。”
“那你们会谈心吗?”
“不会。”
陈浩想让陈嘉琦上班,或者再去读书、念技术学校,可陈嘉琦只是闷着不说话,最后冒出来一句“不想上学”,就想着玩儿。妈妈给她找了个理发店的活儿,结果去上了两天班,就坐不住,又跑了。
我问陈嘉琦,“以后打算怎么办?”
“走一天是一天。”
(王雪欢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沈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