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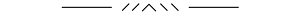
文 | 陈思呈
在村里,有人是一对近义词,比如七娣和鸡姑;有人则是一对反义词,比如米筒和四点五。
这对反义词关系很不错。四点五路经米筒家门口总会大声跟他打招呼。打招呼的内容很奇特,有时说,“走,去打头野猪中午吃。”有时说:“赶紧穿鞋子,带你去娶个年轻老婆。”其实人家米筒的老婆就在院子里洗菜。
米筒也习惯了四点五的无厘头。他有时朝四点五扔根烟,有时则笑一笑表示听到了。村里人的语言交流,常在我意外的地方省略。他们来串门时很少打招呼,直接走进来坐下。要走的时候也不说“再见”,站起来就走了。也许因为串门是随时发生的事,如果每次都要打招呼和告辞就太忙了。
有次我蹲在米筒家客厅看他做木雕,邻居乌叔走进来,在木沙发上坐下就朝米筒扔根烟。两人默默抽起来。乌叔抽得快,因为他手里空着;米筒抽得慢,因为他一边叨烟一边凿木头。抽完一根,米筒又朝他扔了另一根,两人又默默地抽起来。好像他们就是为了呆在一起抽几根烟,又好像那些烟圈代表他们做了一些交流。
总之要听米筒说话很难。以至于我想不起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对米筒的所有认识都是从四点五那里听来的。
四点五说——几十年前他和米筒都想去当兵,他骑单车搭着米筒去报名。那一路,骑车一个多小时,他只能一个人自言自语,时不时还要用手扫一扫后座那人还在不在。
四点五说——人分两种。一种是出门都要带块蔗渣。(以前蔗渣可以当纸擦,也可揩油用,出门带块蔗渣,你能意会不?)另一种人就是米筒这种,直肠拉直屎。连多抽人家一根烟也不愿意。递给他第一根烟他拿着,第二根要再递给他,他就赶紧摸出自己的。
还是四点五说——米筒太老实,也没用。全村是他第一个有驾驶证,也不晓得开车赚点钱,只会在家里刻木头。他十五岁就学木雕,但他的木雕卖不出高价。他没大师证(注,这一带从事木雕业可以考工艺大师证)。上次有人说出三万元可以买个大师证,他也没买。我怎么知道他为啥不买,让他说话,比求**拉尿还难。
至于米筒为什么不买大师证,我想,倒未必因为狷介。三万元也不是小数目,虽然做大师证后能卖高价,等于是买鸡来下蛋,但吾乡还有另一句叫“百赊不如五十现”。没有大师证,也能过小日子。
四点五认为米筒干的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活。他觉得做木雕的痛苦跟钓鱼不相上下。四点五曾去钓过一次鱼。坐到焦躁一无所获。最后直接把鱼竿扔进水里,再往水里填了块大石头解恨。令我想起《世说新语》里对鸡蛋泄愤的王蓝田。
米筒的沉默,既不是拒绝,也不是谨慎,更像是空白。他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他的每一天都是重复,仿佛连自己也可以省略掉。我有次问他:“米筒,你能不能雕个别的东西,雕一只猪试试吧?”因为吾乡木雕,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雕蟹篓。一个篓配几只虾,几只蟹,再配一条绳,外面再配一些梅兰菊竹,都是固定标配。不仅村庄,城里也有不少木雕作坊,但也同样只雕蟹篓,作坊里会收学徒,也是雕蟹篓。

▲ 资料图:木雕蟹篓
米筒只笑不答,意思是这个问题太荒谬了,不值得回答。就算把梅兰菊竹改成桃花栀子,大家看了也会大摇其头,叹息它卖不出去的命运。就像吾乡的西红柿炒鸡蛋是用白糖炒的,如果用盐炒,大家就会嗤之以鼻,仿佛你对生活极缺乏认识并且极不尊重。
所以大家都按套路做,安全地,无欲无求地,从一而终地。这样的蟹篓米筒做了二十几年,无数个,想必会再做无数个。这个情景,其实也可以被表达得很有“情怀”,我都想到可以怎么配图了,特写:米筒粗糙的手,和没有表情的侧脸,文字的关键词大概是:“乡村最后的手工艺者”“恪守祖先技艺的工匠精神”“隐居乡间的淡泊”“甘于寂寞”“岁月静好”“古意”“乡愁”等等之类的。
而我在米筒身上感受到一种空茫——每一天都重复同一天的人。劳作但不需要作品的人。不需要署名的人。不需要表达的人。可以“没有”的人——这一切是因为他的过分沉默吗?《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唐娜布里特曾说,没有无聊的人,只有未被发现的人。所以,也许米筒只是一个未被我发现的人?
而四点五则是一个过度开发的人。他对自己过度开发。
四点五其实快六十了。因为他生命力过于旺盛,也因为他太没正形,总之,直接叫他四点五顺嘴得很,不止是我,村里人都这么叫。
四点五在村里是一个异数。村里绝大多数人,都被生活推着走,但四点五,是要推着生活走。
但他没有惯常思维里的“享受生活”。烟酒茶,他只爱抽个烟。吃饭他也不喜欢。他说,米饭五分钟,喝粥两分钟。早上六七点去山里砍树,下午四点多才回来,和搭档一天能斩了一万八千斤,一粒米没吃只喝水,这样的事他是干过的。
他就是热爱工作。当然他也热爱赚钱,但这两者并不同一回事。我在莲村住在他隔壁,常听见天未亮他就出门去干活,屋里传来他老婆的骂声:“抢宝也没这么积极”。然后天蒙蒙黑他回来了,又传来他老婆的骂声:“你怕自己命短,想干没命干是不是。”常听人骂老公(或婆)懒,他家倒过来。
在山上,四点五向我展示他种的花生苗和别人种的花生苗多么不同。我犹豫地说:“你种的比别人的高一点。”四点五相当不满意:“高一点?这叫高一点?我收三斤他才收一斤我告诉你。”我不识趣加了句:“是不同品种吧?”这下他简直震惊:“不同一品种能比吗?这都是航空二号!”他不屑地指着人家的地:“它们长得不好是下肥晚了。我都是未发芽就下肥,它们一出世就能吃到。会不会管才是大关键!”

四点五讲起农作物时,仿佛它们是他亲生的。有次我听到他边下肥边自言自语“再不喂肥的话,就太饿了。”农历十二月是苦瓜催芽的时节,天太冷不便催芽,他把几十颗苦瓜种子用布包好,晚上放在被窝里,白天又放在棉袄里,走哪带哪。他还啧啧有声地跟我说,这些苦瓜籽有多贵你猜一猜?未待我猜他又自报答案,五块钱一颗。虽说确实是不便宜,但他的姿态仿佛它们会孵出婴儿。
有次我带他去城里,想让他和我爸交个朋友。谁知道他们见面一个沉默地喝茶一个沉默地抽烟,两个人面面相觑,场面一度有点尴尬。过了一会儿,四点五灵光一闪找到话题,问我爸:“你退休金这么高,门路一定很广,这些年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好的花生种介绍?种了几年的航空二号我种腻了。”
我爸也灵光一闪地找到了话题:“你有没有办法弄死一棵树?我屋后长了一棵,把墙都撑裂了。”四点五一听,脸上那种“你找对人了”的兴奋和笃定,我现在想起来都替他高兴。他神秘地说:“你要偷偷弄死,你买一种叫‘柴王’的药,沾在铁钉上钉上树干,不出几天树干就开始流出白沫,几个月内必死,没人知道它怎么死的……”
我爸连忙表示,树是野种,没主,不需要偷偷弄死,可以光明正大地弄死。他们终于热烈交谈起来了。四点五痛悔我爸没有早点告诉他,早点告诉他,他必定会带个“百草枯”来,或者机油,往上一浇……。他用类似于“大腿一拍”的表情:“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带个龙头锯来,几分钟我就把它斩干净。再不然,你家里有没有&¥(这里没听清)……”侃侃而谈的样子显然是找到了归宿感。
我最佩服四点五的是他对生活的研发精神。他种植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植物。他种过洛神花,向日葵,秋葵……这些农作物在他开始种植之前,村子里从没有人尝试过。它们,就像西红柿炒鸡蛋却放盐一样,在吾乡乡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赋予沉重或者沉闷的农业生活一种天真的魔幻感。他做西瓜酒。在西瓜长到七八分熟的时候,他把西瓜朝上的那一面切开一个小口,在里面填进酒麯,然后封好切口,让西瓜继续成长,酒麯开始发酵,最后,彻底成熟的整个瓜,变成一汪巨大的西瓜酒……他让丝瓜跟葫芦瓜嫁接,认为那样会产生出一种兼具两者优点的新品种,但失败了;他又继续试图让茄子跟某种野生植物“刺茄”嫁接,他信誓旦旦地说某乡某处有人曾经试过并成功了,其实他又用不着对我信誓旦旦,那是他一个人的土地,他爱怎么作怎么作,最多就是让他老婆再继续骂……
与米筒不同。四点五热爱表达。种植也是他的表达。他对每个从外面到村里来的人都充满兴趣。偶尔有朋友到村里找我,四点五热情洋溢地给她们取了各种外号。比如“环保”,这是我某个同学,因为她来的时候特别指出村里人随便扔垃圾很不环保。比如“相机”,这是某个摄影师朋友。“你的相机能给我闻一闻么?”四点五问她,“我看不懂,只能闻一闻。”他嘻皮笑脸地补充解释。
以前他喜欢去很多地方砍柴,一斩就是十几天,在村里找一家借宿,天冷一点就用芭蕉叶和麦杆草塞在席子下当棉絮。有一次,他的牛走丢了,他四乡六里去寻牛,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来到一个陌生村子,看到有家人客厅里挂了一面镜子,镜子里写了一个名字,跟他的学名一模一样。他停下脚步,讨一碗水喝,边喝边攀谈。他的学名不算稀奇,同名同姓也不奇怪。但那一个停留,他交到了人生最好的朋友。
他那么投入又充分地活,让作为过客的我,也深受感染。而他“四点五”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他刚出世时,他妈已经生了六个儿子,听说又是个男孩,但喊他爸去灶头拿把灰,把新生儿闷死。他爸不忍,只对那无知小婴感叹:“你这命啊,只值半个狗。”狗在当地发音等于“九”,半个狗(九)也就是四点五。
【作者简介】
陈思呈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