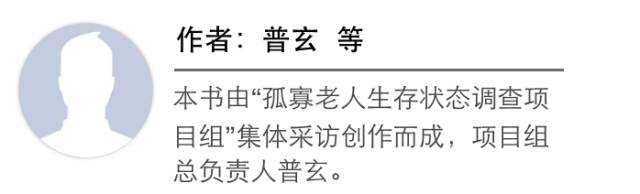网络图
“哪里来的,到李沛街干什么?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一齐质问我。
我说,“老子来买盐的。从来没背过书,背个鬼,背什么语录!”然后我就被抓了。
编者注:
许多人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你身上,砸中你。每个人生,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
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组用大半年的时间,在湖北、河南采访了七百多位孤寡老人,重点撰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位,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这些寡居者,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
此文为寡居者的故事第二篇。
口述人:樊孝海,男,1946年生
湖北省咸安区双溪桥镇李沛村人
大半辈子养猪,坐过四年牢,2006年住进横沟桥镇福利院
我坐过四年牢,是个有案底的人。
1972年,刚入夏,趁天气好,我到李沛街买散盐。买盐是必须的,三个月去一回,自家炒菜做汤要放盐,生产队煮猪食也要放盐。散称便宜点,比袋装的划算。李沛街是条十字街,有公社、供销社、农资站,还有集市。农历逢五有集市,赶集时很热闹,街边摊摆满了,农副产品都拿来交易。
那天撞邪了。我走到十字路口,被红卫兵拦住。三个糙伢子,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还没长开,瘦得跟麻秆似的,要不是戴着红袖章,我才不怕呢。
“哪里来的,到李沛街干什么?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一齐质问我。
我说,“老子来买盐的。从来没背过书,背个鬼,背什么语录!”见不得那些小鬼,毛没长齐呢,还一拢一伙的,举着红宝书发号施令,我即使会背语录,也不想背给他们听。
红卫兵本来就是找碴,这下当场扭住我,说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是现行反革命。我又急又气,辩白不过,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吓得心里直打鼓,手脚不敢反抗,就被捆起来抓到公社,在黑屋里关了一夜。
之后,我稀里糊涂进了“李沛公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待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就是开会学习,吸收和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学习内容主要是“毛选”,还有《人民日报》社论,也有别的解读文章。
我真不是读书的料,又是背诵“老三篇”,又是谈心得体会。背书心好烦,搞得每天都睡不好觉,三四十人挤在礼堂睡通铺,好多学员说梦话都在背语录。每一段语录,我都觉得很长,总是翻白眼背不全。
学习期满,终于放我回了家。我一寻思,回去肯定没好果子吃。上十天不见人影,队长不扒了我的皮,说我破坏革命生产,弄不好开我的批斗会。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坐土飞机,都不是闹着玩的。
不如跑出去讨米,白白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就让他们以为我死在外面了。
● ● ●
我到处游荡,像一条流浪狗,东家讨点吃的,西家讨点喝的。许多生产队在收割麦子,这季节要饭容易,有煮麦粒,有黑面馍。我学机灵了,向人乞讨时,先背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主人家伸手。也许是看我破衣烂衫,可怜得要命,没人跟我打语录仗,多少都会施舍点吃的。
流浪了三四天,我又觉得没意思,就想再跑远一点。就去汀泗桥车站,准备扒上汽车,往北到武昌,或往西到蒲圻。哪里露水不养人呢,当叫花子好像也不难。
没想到一进车站,我就被公安逮住。这个公安也是李沛人,蹲点几天了,正一肚子气,他不知怎么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当天就把我投进咸宁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已经是坐牢了。
我的所有侥幸和妄想全部破灭。
我蹲进去的号子已有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高个老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瘦子。他们问我,因为什么问题进去的,我说跟红卫兵打架。我反问,你们怎么进来的?他们苦笑。也是打架,不过是打嘴架,或说打笔仗。
高个老人是个中医,还是院长,被造反派抓小辫子,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中年瘦子是臭老九,说他贴大字报,“书写反动标语”,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刽子手”。
我被关了三个月,他们说已查明事实,说我没有开路条,竟敢四处流窜,不仅破坏革命生产,而且污蔑伟大领袖的著作。
我被判处反革命罪,可我没看到判决书,但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像我这样的小角色,还不够格开公判大会。我的两个狱友应该够格,但我和他们分开了,没能亲见。
定罪之后,我被送到沙洋监狱劳改。
在牢里,主要是劳教劳改。牢饭有得吃,当然要干活,还抓政治学习,就是不挣工分。
我被分在砖瓦厂,一起有几百人。在砖瓦厂四年,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劳改犯,因为除了不挣工分,各方面都不比生产队差。
每餐吃半斤米的饭,大土钵蒸的,每个组派人轮流去食堂挑,还有菜拌饭下咽。冬瓜、南瓜、黄瓜、丝瓜、萝卜、白菜、豇豆、茄子等时令菜没断过。他们做苦力的每天还有一瓢肉,我这不出力气的每个星期也有一瓢肉。逢年过节还打牙祭,筒子骨汤、猪肉炖粉条、辣椒炒肉,什么都有,一餐吃过瘾。
住就不多说了。毕竟是坐牢嘛,睡的大通铺,还有狱警拿枪看守,起夜解手,必须先打报告,否则后脑勺一梭子。
再说政治学习,抓得可真紧。每天雷打不动,学满两个小时。收工回来后,有时夜里,有时白天,专门坐下来,搞思想改造,比公社学习班还认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受到深刻教育,觉得不懂知识真可耻。那本红宝书,我差不多背下来了。
● ● ●
1976年10月,上面为我平反。沙洋监狱出了一纸文件,让我交到咸宁县委,国家补偿我五百块钱,外加五百斤粮票,之后让我回老家。
我回到李沛村,拿着县委开的证明,无论见到大人还是伢仔,我都拉着他的手说,“看,我是无罪的,我是冤枉的,上面判错了,完全搞错了!”
樊队长——还是他在当队长,驳斥道,“哪里搞错了?当初判你是对的,现在为你平反,也是对的,上面永远是对的!”
因为我坐过牢,所以讨不到老婆。这些年,没人肯为我说媒。看到适龄的女子,我也不敢有任何念想。时间越往后拖,就越没有合适的了。
我回家时,父母都去世了。老弟结了婚,老三间只够他一家人住,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没别的手艺,找不到正经事做。有时在横沟给人看山林,有时到贺胜茶场炒茶,都是打零工勉强糊口。好在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坐牢之前,在生产队当猪倌。算起来,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最擅长就是养猪。
进福利院之后,黄院长逢人就夸,谁养猪都没我靠得住。我喜欢养猪,看猪崽哼哼抢食,跟一群伢崽一样。养猪不给我另外发工资。还有人自愿种菜园,天不亮就去浇粪水。院民都是做惯了的,几十年勤扒苦做,一下子也怕闲出病来。
我在几岁就打猪草,那个年代的小孩都会。十六岁开始挣全工分,算是正式搞养殖。
那时六畜吃的都是草,家里烧火做饭也要用草,所以柴草不像现在草盛为患,藏得住豺狼虎豹,田埂上、地头旁、旷野里都收拾得很干净,每天想打到一篮猪草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哪有正经读书,放学就挎上竹篮,拿着铲刀满山满岭野,一对眼子就像打猎似的。
我高小没毕业,便接了老猪倌的班。
每年为生产队养十几头猪,大概养了十来年吧。那年头任务重,我养的猪基本交给公社了,队上只留一头年猪,年关每户分两三斤肉,欢天喜地过大年。因为有荤腥呀,一个男劳力每天六七工分,遇上年景好,工分单价也就值四分钱,而一斤肉要七角二分钱,挣的工分换口粮都不够,不是过年哪有肉吃?几个管事的落点猪下水,我能多喝一碗心肺汤,那个滋润呀。
相对来说,喂猪不算重活儿,比犁田耙地轻松得多,我还算是捡了便宜。每天晚上铡猪草,大铡刀明晃晃的,特别在月亮地,看着分外瘆人,跟电影里差不多,敌人用它铡刘胡兰的头,你要一不留神,会被铡断手指。
猪不光圈养,还要放牧。春夏两季,野草疯长,日头又大,照着舒服,我就把肉猪赶到草甸子去。
从大集体给公家养猪,到分田到户自家养猪,我养的猪都是吃猪草长大。不像现在吃的是饲料、泔水,我先前养的猪长得慢,从猪崽断奶到生猪出栏,将近一年时间,从来不用什么添加剂,更没听说过瘦肉精。
● ● ●
到了千禧年,我在黑沟养猪场谋到差事。这里养猪规模很大,生猪五个月养肥出栏。
那些年生意也红火。一般年成,生猪存栏有一千多头,行情好时达到两千多头,根本就不愁销路,都是军车来直接拖走。因为养猪供给部队,老板娘对外号称特供,逢年过节宰杀几头,一扇扇猪肉拿来送人情。
那个猪肉呀,城里人不识味,反正我不爱吃——尽管是亲手喂养的。
那些猪怎么养大的,情况我最清楚。跟我在生产队养猪铡草煮猪食不能比,跟我在福利院养猪喂酒糟和剩菜剩饭也不能比。
养猪场有几个工种,总共二十多人,分成三班倒,有产房保育的,有催肥防疫的,我负责配料和清粪。清粪脏了点,臭气又重,人要吃得亏。配料比较轻松,也没技术含量,无非卖点力气。一班有三个人配合,把玉米、麦麸、米糠或秕谷等袋装饲料,按照50%、30%、20%的比例,放进机器搅拌均匀,然后一袋袋装好,每天定量一百袋,有时赶工装两百袋。事情干完,就可以坐着玩。
老板娘人不错,没亏待我们,工资从不拖欠,先是每个月六百元,后来涨到八百元。一直干到六十岁,我进了横沟福利院,当时有两万块存款,至今在这里,我都是最富有的,不过零打碎敲,也花得差不多了。
● ● ●
进福利院要讲条件的,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我一辈子没成家,也没个后人,才有资格吃五保。我坐牢回来之后,从来没去上访,不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打申请比较顺利,村长帮我申报的,横沟桥镇民政办直接收了。
在福利院,我过得不错。黄院长说,你养猪靠得住,再奖励你养个人,每年补你六百块。
于是,我认了瓦片头当干儿子。有个傻孩子陪着过日子,屋里就多个人气,每天为他把屎把尿,算是有点正经事做。有的人笑我,有的人夸我,其实他们都不明白,我养瓦片头是赚了。至少我有个伴,这个伴不是一条狗,也不是一只猫,他是一个孩子,只把我认作亲人。有了瓦片头,我不再像个孤老头子,事实上也有了依靠。我不用对着墙壁说话,还有个人可以偎脚,我们是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说起来也蛮有意思,我们的父子情分是天注定的。
瓦片头是智障儿,身世很可怜。在他三岁时,亲生父母赶夜路,一齐出车祸死了。原来没那么多监控,肇事司机跑掉了,亲戚只好把他交给国家养。
我进福利院第二年,就正式认领瓦片头。
那时他才十多岁,到现在跟了我八年,吃饭仍然不会用筷子,睡觉不会自己盖被子,有时还管不住大小便,屎尿拉在裤裆里。福利院为了防止他走失,从小到大在他脑门上故意蓄一撮毛发,就像半片瓦盖在头顶,走到哪里都好认,怎么跑都丢不了。
倘若只是有点傻,那还比较好办,可他还有间歇性神经病,不发病时没什么异样,独自闷头玩,连眼神都很温顺,发起病来乱打人,两三条大汉摁不住。一般人不敢靠近,只有我才能安抚,瓦片头只认我,这不是投缘是啥。
瓦片头有学名,不过从来没人叫,只是用在花名册中。大伙都随我叫他阿福,我希望他傻人有傻福。我现在跟他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了。
阿福听力没问题,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就是不会说话,只会模模糊糊喊声“爸”。这个字儿是我教会的,这么多年也只教会这一句,阿福尿床了,他会叫“爸”,让我给他换洗。阿福做噩梦受到惊吓了,他会坐起来叫“爸”,要我陪他一头睡。阿福在外面看到新鲜事了,他会奔回来叫“爸”,拉我一起去看新鲜,原来是喜鹊在梧桐树上做窝了,或是黄院长的黑子撵到野兔了。
我就是喜欢听阿福喊声“爸”。黄土快埋到我的脖子了,洗白自己是不可能啦。只等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好歹有个人给我端灵牌。
再过几天,阿福满二十岁,就是个大人了。我打算给他剃掉瓦片头,留一个平顶板寸,这样好看些,跟正常人一样,像个说得上媳妇的小伙子。
我已经七十岁了,这辈子连女人手都没摸过。老都老了,白捡一个儿子,我也该知足了。
寡居者第一篇:《一辈子只放过一次坏炮的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