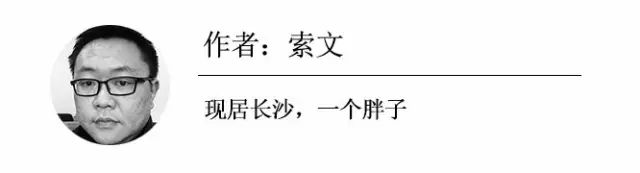图 | CFP
露天浴场沿山而建,火烧到露天浴场的最顶端时,被扑熄了,救火的人们兴奋又疲惫地散去,满天飘着黑色的烟屑,像刚刚结束了一场庞大的祭祀。
晚八点,开车出门,载着太太和孩子去灰汤(温泉小镇,位于宁乡县)。
太太原本不同意今天去,看我有些气闷,也就由我了。孩子五岁,对每一次出行都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一路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每年年初去泡一次温泉,是我的执念。
开年到现在,心心念念了许久,终未成行。眼看着夹克换下棉袄,天气渐渐变热,心思无奈淡了许多。这夜吃过晚饭,听户外狂风大作,打开窗,冷风扑面,吹得人一个激凌,忙不迭地关了,一个念头倏地涌上心头,我欣喜地返身,对家人宣布:“我们泡温泉去。”
汽车开上高速,眼前豁然开朗,最近的车尾灯在目力所及的远处,眼前只有车灯照出的空旷路面,其余都隐在黑暗里。太太和孩子在后座小声地说话,孩子说:“妈妈我又饿了。”小孩子不知道饱足,晚餐才扒过一大碗饭,又惦记上太太带的零食了。
路仿佛没有尽头,汽车在隆隆的寂静中行驶,车内只有导航呆板的指示声,太太静坐着休息,孩子在吃着雪饼,蟋蟋嗦嗦像只小老鼠,“一下子变冷,会不会下雪啊?”太太轻轻地问。
我一愣,“谁知道呢?”
去年的这个时候,不记得更早一些还是更迟一些,我去过一次温泉疗养。
彼时,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老友刘医生给我开了些药调理,并嘱我休息,“抽得出时间的话,去泡个温泉吧。你太累了。”说罢,他又挤着眉揶喻,“像那些日本作家一样,搞不好有艳遇噢。”
“哪里可能,正是温泉生意好的时候,听说下饺子样,晚点去,漂一池子的汗垢。”我露出恶心的表情。
刘医生哈哈大笑。
但我还是去了,一个人,去了江西,在温汤镇(温泉小镇,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旁的一家新酒店小住了几日,带着我的笔记本。在想象中,我真把自己当作了独自出行的作者,忘却了现实中的困窘与卑微。
刘医生嘱我戒一段时间酒,这对本就睡眠极差的我更是雪上加霜,整日极晚睡去,极早醒来,在房间的泡池里放一池水,坐在里面,等待日出。
阳台敞着,有风吹来,略寒,扑在脸上、肩上,人不由得往水里缩。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糟极了,每天都游神一般昏昏沉沉,电脑打开,半个字都写不出来,带去的书,也是看得无味。偶尔去酒店大堂吧坐坐,看着酒柜上琳琅满目,忍得越发辛苦。
有一天,近中午时,我叫了辆车去镇上,单程20元,路程不远,熟了路才发现其实也可以走着去。司机大哥把我放在温泉古井边,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驾车扬长而去。
我在镇子里闲逛,看了一眼温泉古井,便往镇上走,满镇都是洗脚店,家家门前摆着水桶,这是最简单的泡汤,花上10元,便可不限时温泉泡脚,老板不时提着水桶去泉边打水来续。
我在镇街上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远处的山是深绿色,眼前人来人往,匆匆皆过客。
逛得饿了,转身踅进了另一条仿古街,街上各种小店,卖旅游用品的竟然不多,我在一家五金店边的米粉铺子门口驻足,看了看,走了进去。老板娘在简陋的灶前忙碌着,我看了看桌案前仅有的几盘码子,点了肉丝排骨双码加卤蛋的米粉。
老板娘高兴地应了声好,嘱我先坐。
店里零散有几个客,占据了仅有的几张桌子,我找了个只有一人的桌子搭桌,坐了下来,对面的汉子正低头对付一碗炒粉,右手边放着一支开了瓶的小酒,扒几口,咪一口,咂着嘴,轻轻地陶醉地摇头,又低头吃起来。
那是个中年汉子,浓密的络腮胡,短发,鬓角修得整齐,着一件墨绿色的开衫毛衣,内里穿着亚麻的衬衫。炒粉是豆芽菜鸡蛋的配料,汉子口味极重,洒了不少辣椒粉,吃到一半,又舀一勺洒上,一盘炒粉红通通的,他吃得津津有味。
我的米粉也上来了,味道有些淡,份量也偏少,三两下扒完了,倒上醋,喝了两口汤,放了碗。对面汉子也刚吃完,一头的汗。酒没喝完,他望着瓶子略一凝神,扭头呼喝老板娘上几片卤豆腐下酒,说的是普通话,嗡声嗡气的,像闷罐头。
卤豆腐用小碗盛着端上来,略呈酱油色,汉子同样舀一勺辣椒粉洒上,筷子夹成小块,就酒。
酒香味勾得我肚里的酒虫蠢蠢欲动,我点上根烟,盯着他手中的白瓷酒瓶,酒瓶很精致,上有水墨山水,汉子嘬一口,将酒瓶敦在桌上,瓶上山水旁赫然四个小字——“雁塔文峰”。
“这是什么酒?”我轻声问。
汉子低着的头抬了起来,乜了我一眼,将酒瓶往我跟前推一推,“本地牌子。”
“来一口?”他指了指酒。
“不了,我在戒。”我摆摆手。
我开了根烟给他,他放了筷子,双手接过。许是吃多了,饭气翻上来,他一手捂嘴,侧身轻咳。
“外地人,来泡温泉?”汉子点上烟,问。
“看得出啊,你不也是吗?”我笑笑说。
汉子连连点头,“这里名气大,我慕名而来。住了一阵子了。”
“你该再早点来,正是天冷的时候,泡着才舒服,”汉子端起壶,又让一让我,我双手合什作揖拒绝,他没有坚持,自顾喝了一口,“这酒还行,本地酒里算好的。但是泡汤起来,要喝药酒,当归、五加皮泡的,也有泡蜈蚣的,祛湿毒。”
“这里有茶馆吗?”我问他。
他定神看了看我,低着头想了想,“没留意,”又嘿嘿一笑,“戒酒又喝茶,你不怕失眠?”
“已经失眠了,总不会更糟。”我笑着说。
他哈哈笑起来,笑声像闷罐子里放了石头,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我又开了根烟给他,他愣了愣,笑着接过了。
“你我都是客,有句话怎么说,先入为主,我有茶叶,我招待你。”汉子说。
10分钟以后,我们坐在他旅馆的门前,他回房拿出自带的黑茶,敲下小块,请前台用玻璃杯泡上一杯,二人门神一般,在旅馆门前各倨一个靠椅,初时有人来赶,见是他,又走开了,汉子倒觉不好意思,呼喊着,“我们泡脚啊。”
“老客啊,优惠价。”他又补上一句,回头冲我挤挤眼,“生客10块,老客5块。”
已是下午时分,蓝天白云,日头半掩在云里,阳光照在身上并不显热,街上的人客不见减少,四周青山如黛,远处的高山看不分明。脚边的桶里已经注入了温泉水,和冷水混合,脱了鞋袜,把脚伸入,仍烫得咧嘴,赶紧抬起,搭在桶沿,一会儿,再试探,再抬起,如此反复,终于受得住了。
默默地将身体放松,瘫在椅上,伸手端起茶,嘬了一口,热茶入肚,从里到外都有热的,人惬意了许多。
汉子仍拿着他的酒壶,时不时地嘬上一口,150毫升的量,仿佛怎么也喝不完似的。
在去旅馆的路上,我们已经互问了台甫和来处,汉子姓陈,来自川中某个小城,原本做老师,后来下海经商。做什么生意,他不说,我也没问。
“当老师时,我就告诉学生,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大好河山,不在字里,在眼里,在感触里。不到近前,不能领略。”汉子说,“可真正要做,我花了好久时间。”
我皱了皱眉,以为他要给我说他的成功史。但是他并没有。也是,萍水相逢,真的没必要交浅言深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仰着头,望着天上的流云,一句话也不说。酒壶照例攒在手里。我小口地喝着茶,默默地想着心事。街对面有个鱼疗馆,群群小鱼在玻璃鱼箱里焦躁地游着,一只脚落入水中,鱼儿一拥而上。近处,有店老板用本地话大声地呼喝着帮工,工人毫不示弱地回应,二人吵闹着,将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当成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小街的尽头,一队新到的游客从拐角处转出,导游无精打采地说着,客人们饶有兴致地听着。
● ● ●
“老弟,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失眠。”许久,汉子忽然低头问道。
我一惊,望着他的眼睛,那里面幽深空邃,如止水一般。
“我不知道。”我低声答着。
“会不会是焦虑呢?”他说,“我也有过,很难受的,为了一件事情,不分昼夜地操心。没得停。身静了,心也不静。”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他自说自话,“我们都说这里是个好地方,可要是我流浪到这里,我会这么认为吗?我会觉得没得一口饭吃的地方,肯定不是好地方咯。景色好不好,有没得温泉泡,关我啥子事呢?”说着说着,他带出了乡音。
“你现在就是这样子噢,有吃有住有温泉泡,倒还像个流浪汉,还是不开心嗦。”他笑着说。
我直起身子,想要辩解。
汉子笑眯眯地看着我,不说话了,像在等我说。
我默默笑了,开了根烟给他,自己也点上一根。
他将烟夹在耳上,瘫回椅子,控着腔喊,“老板,加水!”
“VIP呢,半价无限续。”他笑说。
我点上烟,吸了一口,指了指他,半开玩笑地问,“劝我惜福吗?”
“是节制啊!”他嘿嘿地笑。
渐渐的日头西倾,我们的脚都已经泡发了,茶水也续过几轮,我抽出脚来,擦拭干净,该走了。
汉子惬意地伸着懒腰,夸张地打着哈欠,“我想吃炒八扎了。”
“我不陪你,我回去了。”我说道。
“好!”汉子说,拿起那瓶小酒,起开瓶盖,又嘬了一小口,“其实你不必戒酒,不多喝就好,驴饮我见得多了,那是只求一醉的喝法,第二天早上脑壳痛。像我,这一瓶喝一天也可以,小口小口地喝,爱酒,就体味它的味道,进口辛,到喉辣,入胃暖,反复地品味,会觉得感受多好多,一层一层的。”
他咂着嘴,看着我,又像是望向我的身后,目光又复深邃,“不要求醉,就像我们,莫太追求结果,那句话怎么说的,陌上花开缓缓归。”
我起身告别,汉子摆了摆手,没有起身,坐在椅上伸着懒腰,“明年带家人来,好地方,一个人,还是闷了点。”
那一天,回到酒店,我在房间的泡池放了一池水,坐进去。窗户开着,对面是不知名的山,我在池子里愣坐,水冷了加水,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楼下有人惊呼,对面山上涌起一股黑烟,起了山火。天干物燥,火越烧越旺,很快连成一片了,不一会儿,两台消防车开来,我起了身,穿好衣服,走出门去,大堂里,许多人往后山赶,经过前台,有人在理论,烧过来怎么办,要退房。我跟着人们往后山跑去……
露天浴场沿山而建,火烧到露天浴场的最顶端时,被扑熄了,救火的人们兴奋又疲惫地散去,满天飘着黑色的烟屑,像刚刚结束了一场庞大的祭祀。
此时,车子仍行走在黑暗中,要下高速了,孩子和太太在后座嘻闹着,似远似近、或明或暗的乡间灯火在右前方路肩下缓缓移动。
到了灰汤的岔口,车子右拐而下,眼前瞬间亮堂了许多,经过收费站,驶上寂静的小街,两旁的大树葳蕤,密叶如盖,遮出迎客的温柔。隐约望见高处酒店的灯光,孩子开始欢呼,妻子小声地呵斥着。
我也开心起来,终点在望,那一池池烟气蒸腾、消乏解困的温泉水,就在路的尽头。
编辑:侯思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