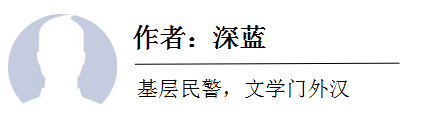图 | 东方IC
公安机关既无权免去他的医药费,也没法帮忙与医院讨价还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徐征只能继续待在社区里,做一颗“定时炸弹”。“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老徐说得到,却做不到。
前言
精神病人管控不易。在社区警务交流会上,我和同事打趣:“只要张革命躺在马路牙子上晒太阳,小豪走街串巷捡饮料瓶,阿强在汽车站唱歌,常娥坐在家门口玩纸盒,今天就平安无事。”
“不然呢?”
“不然”我笑了笑,“你忘了那年冬天,咱俩在武汉满世界找精神病人的事了吗?”
聊着天,我就突然想起徐征。
2011年4月的一个晚上,五七夜市杨家烤鱼店的老板报警:“派出所吗?快来人啊,徐疯子又来搞事了!”
“徐疯子”本名叫徐征,39岁,人高马大,一表人才。如果他是正常人,凭借长相应该就能迷倒很多女人,可他从小就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直到现在也无法正常工作,没有结婚。
我和同事抓起防暴钢叉就往夜市赶,到了烤鱼店,杨老板和他的妻子站在店门口。杨老板脸上带伤,身上的衬衣被扯得不像样子,一众食客在店门口围观。
“人呢?老杨。”
“在屋里呢,你们快把他弄走,幸亏刚才老子跑得快啊,妈了个X的!”
我和同事赶紧进屋,只见徐征握着一把菜刀正在砍电冰箱,周围桌椅横倒,吃食撒了一地。看我们进来了,徐征二话不说,提着菜刀就迎了上来,我心里一惊,伸手要摸枪,同事大喊一声:“小李,用钢叉!”然后猛地冲了上去。
同事的伸缩警棍甩开,徐征稍一犹豫,警棍正砸在他右手腕,菜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赶紧用钢叉把徐征叉住,同事扑上去,按住他的双手,掏出约束带,把他牢牢地绑在了暖气管上。
徐征瞪着眼睛,面目狰狞,张开嘴“啊啊”地叫。他挣扎了没一会儿,就放弃了抵抗,同事爬起来,蹲在一边喘粗气。
一直站在门口的杨老板看徐征被控制了,才走了过来,顺手拾起了一个酒杯,要砸徐征。
“老杨,别动手!” 同事赶紧制止他。
“你看看,他把我和我店里搞的!”杨老板怒气冲天。
“别给自己找麻烦,他是精神病人,砸伤了他,你还得赔他钱。”同事赶紧站起来。杨老板气得直跺脚,“他是么斯(什么)精神病人,我看,他就是蓄意报复,这次必须赔钱!”
杨老板的烤鱼店前,原有一台“抓烟机”(类似于娃娃机)。3天前,徐征连投五个硬币都没有抓出一包烟,当场就犯了病。他捡起石头把抓烟机砸个稀烂,烤鱼店的伙计推了他一把,被闷了一砖头。事过三天,1000块钱的财产损失和医药费还没给,徐征又把烤鱼店砸了。
二十分钟后,徐征的父亲,老徐,赶到了烤鱼店。
彼时,徐征仰在地上,正歪着头舔自己吐在地上的口水,看到父亲来了,他双脚乱蹬,又兴奋地“啊啊”叫起来。
老徐瞟了儿子一眼,扭头问:“杨老板,这次又是多少钱?”他语气漠然又无奈。
“两次加在一起三千块。少一分也不行!”杨老板怒气冲冲地朝老徐吼。
“先别说这个,老徐,你儿子现在怎么办?”同事打断了他们。
“还能怎么办,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
多年来,徐征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常客,几乎每位民警都处理过与他有关的案情。
有时是他砸破了烟酒店的玻璃;有时是他划了小区里的私家车;有时是他追打路人,最严重的一次,他把桥头卖水果的摊主打成了轻伤。打人事件发生后,徐征被送到沙市精神病院强制医疗了三个月。虽然打人时他正处于发病期,不用负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还得出。
三万元的赔款几乎压垮了老徐,那段时间,曾有人看到老徐在武汉光谷地铁站乞讨。
长期以来,老徐的生活就是在“去派出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骂儿子、送精神病医院”的圈子里兜兜转转。
后来,他骂不动儿子了,只是去派出所给受害人道歉赔钱,再把儿子送进精神病医院。
再后来,老徐没钱了,就只能频繁地来派出所领人,低声下气的给受害人道歉。
遇到脾气好的、损失小的,看老徐可怜就算了,有时遇到不好说话或损失太大的,老徐还是免不了到处筹钱。
“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老徐说得到,却做不到。
经过两个小时的调解,杨老板走了,手里拿1000元的赔偿金,这是当时老徐能筹到的全部钱。
处理完赔偿,我们才再次注意到徐征。他还在派出所后院绑着,疯劲已经过去了,老徐跟我商量:“他现在好点了,能不能让我带回家?”
我劝老徐赶紧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老徐无奈地摇头,“等等吧,明天他姐姐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这会儿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我把他们送到派出所门口,告别的时候,老徐问我:“李警官,现在还有精神病人强制送医的政策吗?”
“有是有,但那是出大事儿以后,你可别盼着啊!”
“哎,算了。”老徐嘴里嘟囔,带着儿子走了。他们的背影在暗夜的灯光下,拉得老长。
老徐快70岁了,每月只有不到2000块的退休工资。他妻子的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吃药,好在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本市上班,每月能拿些钱回来贴补家用。
徐征不发病时,像正常人一样,见了人会打招呼,有时也帮母亲做家务。有段时间,他连着半年没有发病,老徐便托人在市机械厂给他谋了一个看仓库的差事。
可后来,徐征发病打了厂里的职工,被送去精神病院治疗,虽然事后老徐一再保证“已经治好了”,但厂长死活也不肯再雇他了。每个月几百元的收入也没有了。
精神病人管控是社区民警的一项职责,需要每月按时调查情况,做好记录。我刚接管社区工作时,就去了徐征家。他家住在一座旧家属楼上,两室一厅,陈设还是90年代的风格。
老徐说:“儿子刚吃了药,正在卧室睡觉。”说着,他便把卧室的门关了,拿张椅子坐在我对面。
家访的内容无非是“目前病人情况怎样”、“是否按时吃药”、“有什么需要民警帮助的”之类的话。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准备告辞,送我出门时老徐还不住地说:“徐征没有工作单位,每次去精神病医院都是自费,本地医院不接收他这种有暴力倾向的,沙市精神卫生中心一个疗程(两个月)要一万多,武汉的更贵,确实是送不起了。警官你看,派出所有什么办法没?”
我感到很为难。
市场经济时代,公安机关既无权免去他的医药费,也没法帮忙与医院讨价还价。后来,我曾试图帮徐征办理社会医保,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能成功。
徐征只能继续待在社区里,做一颗“定时炸弹”。
2011年5月,市里召开重要会议,上级要求做好社会面管控,务必不能发生重大治安问题。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当天有群众报警称,辖区内有人打架。
我和同事赶到现场,看到徐征正把一名收废品的外地人按在地上殴打,周围有不少群众围观,却没人敢上去拉。
我们赶紧上前,想把徐征拽开,不料这时老徐突然冒了出来,他手里拎着一根钢管,举起来就要往徐征头上招呼。同事见势不妙,上去阻拦,钢管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身上。这一下的力道不轻,同事当场就疼得说不出话来。老徐吓坏了,顾不得儿子,不住地道歉。
一众人等被带回了派出所,在办公室里,我怒斥老徐,问他想干嘛,老徐低着头半天囔出一句话,“刚才,我真想一棍子打死徐征。”
“杀人偿命呢。”我冷冷地说。
“我70了,偿命就偿命吧,都解脱了。”
最后,老徐出了500元的赔偿金,收废品的外地人骂咧咧地离开了。这次,我再也不听老徐的了,坚持要将徐征送往精神病院,老徐原本还想把他带回家,但可能是觉得自己误伤了民警,有愧,最终默许了。
去精神病院治疗,费用问题依旧逃不过去,老徐给女儿打了电话,那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老徐的脸色很不好看。我问怎么了,老徐没说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点了一根烟。
半小时后,徐征的姐姐、姐夫来到派出所,虽然他们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答应把徐征送往精神病院。
他姐夫说:“我要开车,一旦他反抗,我怕老婆和岳父在路上控制不住他,希望你能陪我们一起去。”
在去往沙市的路上,我用约束带把徐征绑结实,老徐给他吃了一些药物,徐征昏沉沉地睡着了。
车内寂静无声,只是徐征的姐姐不时从倒车镜里看一眼弟弟。眼神复杂。
回到家中,老徐问我:“李警官,徐征这种情况除了送精神病医院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出院后只要按时吃药,一般可以控制住病情。”
老徐摇摇头,“警官你不知道,那些药物并不能根治徐征的病,而且副作用很大。”
精神类药物中的镇定剂成分让人整日嗜睡、无精打采。一些成分也会伤害人的肝脏和肾脏,很多精神病人晚年会面临着严重的肝病和肾病。老徐担心儿子的身体,就经常自作主张减少药量,结果导致徐征频繁发病。
“1978年,我有个朋友也得了疯病,家里被折腾的没办法,就把他送到新疆种树去了,一家人也就安生了,现在还有类似的路子吗?”老徐问。
“把亲生儿子送到新疆去种树,你真舍得啊。”我笑。
“年轻的时候真舍不得,徐征小时候,我有个亲戚在西藏,劝我把儿子交给他,自己再生一个。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总想着‘生养生养’,既然生了他就得养,得了病,就得给他治,但现在看来,唉……”
我以为老徐是为了钱发愁,便劝他,“现在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报销比例在提高,经济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小的。”
老徐摇摇头,“不只是钱的问题,我今年70了,身体也不好,万一哪天不在了,他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安慰他,“好在徐征还有个姐姐,可以帮忙照应。”
谁知老徐听到这话,眼泪就掉了下来:“这些年,我已经太对不住女儿了。她从小就因为有个精神病弟弟被人欺负,结了婚还要负担弟弟的医药费,我女婿虽然不明说,但我也能看出他的不满。之前,我曾打算把女儿变更为监护人,想着我百年之后,徐征还有个依靠,但女婿说如果那样做,他就马上离婚。我真的不想因为儿子,毁了女儿的一生。”
两个月后,徐征出院了,尽管我一再嘱咐老徐一定要按时按量给徐征吃药,但一切还是沿着“发病、打人砸物、报警、赔偿送医”的老路行进着。
后来,我要调任刑警支队,最后一次进行精神病人家访时,我问老徐:“有什么需要民警帮忙的?”
老徐说:“我打算下个月带徐征去湖南一趟,给你报个备。”
“干啥去?”
“有人说那边有个神医专治这种病,我带儿子去瞧瞧。”
谈话间,老徐的眼神有些闪烁,我不禁有些担心,“你可问清楚了,千万别被骗了,徐征这种情况出门很危险,我建议最好别去,但如果你坚持要去,那也一定要把药带足。”
老徐点点头。
● ● ●
2012年1月,徐家父子出发。
2月,原派出所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让我赶回派出所,说要了解徐征的情况。我有些诧异,赶回派出所后,发现所里有两名湖南警察。
湖南警察告诉我,徐征父子死了。我吃了一惊,连忙问是怎么死的,他们说是车祸,随即又补充道:“确切的说,是老徐制造了这起车祸。”
他们递来的材料里,详细地记述了那场车祸的过程。
2月7月下午,老徐骑着一辆踏板摩托车载着儿子在长沙某水库旁徘徊,三点多,老徐突然加速,与儿子一起,连人带车冲进了水库。水库旁的监控,记录了整个过程。
湖南同行说,原本是要按交通肇事立案的,但老徐的行为有故意杀人的嫌疑,虽然他已经死了,但还是需要来居住地了解情况,看是否是受人唆使。
我终于明白了老徐跟我报备时,那个眼神的含义——治得好就治,治不好就带着儿子一同赴死。
我赶紧带湖南同行前往徐家查看,他们的亲人们早在屋里哭作一团。看我们到了,徐征的姐姐拿出一封信,是2012年2月6日由长沙寄出的。信中的内容,如今我还依稀记得:
宝珍、小夏:(徐征的母亲和姐姐)
我带小征走了。原谅我这样做,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次来长沙本想最后试一次,结果那个神医也没有办法。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毕竟这么多年了,我也知道小征的病没办法好……
宝珍,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了。孩子是我们生的,孽是我们做下的,就让我来还吧。我们老了,照顾不了儿子了,我不能让他再毁了小夏的人生……以前听人说,家里有个精神病人,这个家就完了,我不相信,但现在我信了。我带小征走,我们一家都解脱了,有我陪着,到了那边他也有人照顾着。
小夏,原谅爸爸,好好过日子,孝顺你妈妈。爸爸没有能力给你留下什么积蓄……
● ● ●
我把信交给了湖南同行,他们默默看完,拍照取证,我就离开了徐家。单位同事问我:“之前,你真的没发现过什么苗头?”
我说没有,同事说:“那是你的工作责任没有尽到。”
“你有何妙法呢?”我问。
“没有。”
编辑:罗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