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不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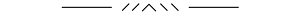
宗教与科学的相爱相杀
文 | 聂建松
作为还算比较有闲的人,我平时经常去网络社区打发时间,看看网络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怎么看待科学或者宗教。我的直观感受是,大多数人经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溺水者只会抓住眼前的一根稻草,却不见身旁的救生圈。
作为对科学史比较感兴趣并且有些许了解的人,我觉得大概自己肩负了一点儿科普这些基本概念的责任。譬如,一旦谈到了科学如何定义,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句话:
“科学是证伪的!”——如此简短,别无其它。可是,事情就仅仅如此么?
▍一、“证伪主义”与“黑”山羊
曾几何时,科学这个概念是笼罩在“归纳主义”(Inclusivism)框架之下的。
那么何谓归纳主义呢?简单地说,就是将“相似且反复发生”的现象集合在一起,并且从中得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随后再将这规律再推而广之,应用于世界。
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遇见的每只山羊都是白色的,因此所有的山羊都是白色的。这就是归纳主义的方法逻辑。
此刻,即便不用提醒,相信很多读者也会发现这个逻辑的缺陷了——我们不能保证见到的下一只山羊是白色的,而下一只山羊很可能就是“黑色”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逻辑不能等同于“归纳主义”。由此,一些学者就开始思索科学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基础上,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提出了“证伪主义”的思想。

▲ 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
那么,证伪主义与归纳主义的差异在哪呢?
归纳主义的逻辑是“我见到的山羊都是白色的,故而所有山羊都是白色的”;证伪主义的逻辑则是“在我没有见到黑色的山羊之前,我姑且假设所有山羊都是白色的”。
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真理性的论断(“所有的山羊都是白色的”)在此变成了一种假设(Hypotesis)——在证伪主义的逻辑下,科学发展不是某个真理展示自身的过程,而是一个人类不断试错的过程——一旦我发现了一只黑山羊,那么我就会抛弃掉“所有山羊都是白的”的论断,而不会以某种不合理的方式调整这个论断。
这里必须提及一句,“某种不合理方式的调整”一般是“特例式”(ad hoc),即抛弃明显更清晰明白的普遍看法,而是针对某个观察到的“特例”,为之“单独发明”一个额外的解释。
譬如,当我观察到了这只黑山羊的时候,但是我会假定这只黑山羊本身仍然是一只白山羊,只不过它掉进了染缸或者煤堆之中,甚至可能只是我一时眼花了。
▍二、证伪主义、神与“精神病”
证伪主义反对的“特例式”解释,当然不只是某种逻辑上的反驳,而是在历史中具体有所指——卡尔·波普本人就不喜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
那么,证伪主义是从什么角度上对这二者表示反对的呢?或者说,在证伪主义者看来,为何这二者不能算作“科学”呢?
这是因为在证伪主义者看来,科学是需要恰当且具体的定义。
那么,什么又是恰当且具体的表达呢?譬如,当我们说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在讲述一个“不科学”的论断。
不过,证伪主义者反对这个论断的原因,并非一定是出于某种“无神论”的观念,而主要是因为“神”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在科学上不甚清晰的定义。
我们可以在生物学上定义各种生物,在化学上定义各种元素,在天文学上定义各种星体——但至于神?神经常是被表达为“超越世界”的存在,但是科学研究的是“世界”。因此,神是世界的创造者,这句话不是“科学”的;反之,神不是世界的创造者,这话也不是“科学”的。
那么,我们把“神”这个词换成别的词语,是否就构成了证伪主义上的科学论断呢?
世界是由某种力量所创造的?世界是由某个起点开始的?世界是朝着某个目的运动的?世界是在一个框架下运动的?这些看法在证伪主义上看来,都可以算是“非科学”的论断,因为这些论断都过于“宏大”了……太不具体了————如此类型的论断总是试图解释一切,但在证伪主义者看来,它们却没有解释任何具体的东西。
换句话说,证伪主义者实际上反对的是这样的看法,即科学是那种“真理展示自身”或者“必然通向真理”的表达——在他们看来,这些看法都更像是神学,而非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是透过“不断地试错”,而逐步“澄清和细分”认识对象的一个过程。
譬如,简单地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将人类意识和行为都归结为“力比多”(libido,性的力量)。在如今的认识水平下,这个论断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如果具体分析下抑郁症以及生活中遇到的工作学习压力,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科学”的做法,便是认识它们并非是不同程度的“一类”东西,而是“不同类”的东西。
▍三、证伪主义与“高塔”
我们在前面大致谈论了证伪主义的逻辑,而且在肯定意义上,谈论了证伪主义对于科学的贡献。
这是否说明了,证伪主义本身就是关于科学前进范式的完美表达么?也不尽然。
首先在逻辑上,证伪主义并非是无懈可击的。
其认知论上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针对观察到的材料,我们提出假说。而当我们观察到不符合假说的时候,我们就要抛弃我们的理论假说,或者对之进行一番有效的修正。
不过,问题就在于,在实际当中我们真的能够确定到底是我们的观察出了问题?还是我们提出的理论假说出了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前文提及的“黑山羊-白山羊”的故事,假如那只“黑山羊”真的不过是一只白山羊呢?假如我们真的不过是看到了一只掉进了煤堆或者染缸的白山羊呢?或者说,干脆就是我那一刻真的就是“眼前一黑”呢?这也就是说,在没有大量观察到“特例”的时候,我们难道就一定要抛弃自己的理论假说么?
其实,很多在实验室中做过实验的人肯定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得出与理论相悖的成果的时候,绝大部分工作者都是在反思自己的实验过程中是否出了问题(是否含有杂质?测量是否精确?计算是否有失误?),都是在怀疑自己的观察是否出了问题,而没有直截了当地怀疑理论是否有问题。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证伪主义仍然可能是一种“上帝视角”下的反思,在描述科学发展这个过程的时候,可能仍旧有些偏颇——读者如果有读过我关于之前的事实观念讨论的文章,就会明白事实其实很难脱离于理论而存在——甚至说,我们的观察必然会受到理论的影响。

▲ 波兰华沙哥白尼像
让我们看下具体的历史事例。在天文学的发展历史当中,哥白尼的日心说代替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系统下的地心说,而在这一理论换代的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人们关于“地球是否转动”是有过几番争议。
反对地球转动的学说,难道只是某些人出自私心,而反对真理么?
并非如此。因为如果从当时的人们所掌握的知识来看,之所以很难接受“地球转动”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于引力和惯性的这样的概念基本为零——而这些对于今人来说,就是普遍接受的常识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对于“地动论”的接受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十分难以回答:
假设地球是转动的,同时假设有一尊非常高的塔,如果从塔顶扔下一块石头,那么这块石头为什么仍旧落到塔基附近的地面,而没有落到离塔很远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石头落到塔基的地面确实是我们毫无疑问观察到的事实,而如果没有引力和惯性的存在,那么这块不就应当落到远处,甚至飞向天空么?——这个问题甚至到了牛顿时期,仍旧在困扰着人们!
那么,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古人担忧下,按照证伪主义的思路,当时的人们是应当抛弃自己的观察结果?还是应当抛弃“地动论”呢?
地动说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并非是因为古人突然之间发明了太空飞船“观察”到了地球是转动的,而更多地是因为,与基于“地不动说”的“地心说”相比,基于“地动说”的“日心说”在数学计算上有着更大的便利——说白了,在实际应用中,日心说更方便。
或者,戏谑一点儿地说,日心说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并非是因为人们能够按照“证伪主义”的逻辑,抛弃了不合理的理论假说,而恐怕是得感谢科学家们都是爱偷懒的人。
【作者简介】
聂建松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宗教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