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窜行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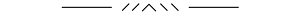
带你游遍全世界的博物馆
文 | 顺手牵猴
纽约现代美术馆的五层展厅,有一件不大艺术的艺术品——一个安在前叉上的自行车轮,倒装在一个四脚木凳上。按照书上的说法,原本是马塞尔·杜尚临时起意,随手捣鼓出来的一件摆设;本意是当作壁炉里的火苗观赏。在他当时住的地方,当然也是没有壁炉的。
那是1913年,他在巴黎享受一战之前,最后的和平时光。至于说这位杜尚,您猜对了,就是拿小胡子给“蒙娜丽莎”易容的,那个艺术界不法分子。那些都是后话。此时的他,由于画家哥哥的关系,混在一群立体派画家中间,技法上也深受其影响,同时搭他们的便车,参加过秋季沙龙、独立沙龙的展出。从他的早期画作,已不难看出追求动态的趋向,所以他弄出那个倒立的轮子,倒也不足为怪。

这是一个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那种改变范式的人。战争开始后,他成功地逃避了兵役,可巴黎到处洋溢的爱国气氛,让他没法再呆下去,于是跑到了纽约。那个安在木凳上的自行车轮,自然没有随行李带到大洋对岸,结果被留守的亲戚们,当成废品处理掉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丢进垃圾站的那件东西,可是动态雕塑的鼻祖,早于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更不要说亚历山大·卡德尔。可惜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是后来重做的复制品。
瓦尔特·本雅明,就是写过《单向街》的那位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先知,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但在现实领域,这只是个乌托邦式的想法,因为艺术品的复制涉及极为复杂的法律纠葛,从许可到限量,等等等等。杜尚这个车轮也不是你想复制就能复制得了。就算造出来,也别想弄进博物馆。就算拿到淘宝上卖,要是让内行人给盯上,搞不好又给阿里巴巴找麻烦。
MoMA这件杜尚,一般人不会留意。原因倒也简单,就是“不美”。可究竟什么是美,还真不容易掰扯清楚。维多利亚式美人儿,热带海岛风光,都挺美,但在艺术领域,这些只供反讽。在北京遇到一饭局,做东是当地一位大亨。席间她问一位指挥,是不是古尔德弹琴,比理查德·克莱德曼还美。在场各位一听,全都换成“那种”表情,原本说好的合作事宜,也就无疾而终。所以美是一个非常势利的话题。
审美,或曰趣味,是钱砸出来的。这话没错,土豪也于是有救。可修理土豪下手最狠的,就是刚洗白的土豪。比起原始土豪,他们擅长调动更少的资源,让行业发展的矢量方向,朝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偏转。优秀的扑满,有风口要飞,没有风口创造风口也要飞。特别是在创意领域。新规则就此产生,包括所谓“逆向装逼”。复杂游戏中翻云覆雨的人物,很可能追韩剧,吃小龙虾,拿土豪金爱疯刷屏,而不是跟你探讨《金刚经》、莫扎特。
很多东西都是“逆向”出来的。别人还在一面先锋,一面依依不舍地跟拉斐尔学造型,跟伦勃朗拼笔法,跟鲁本斯比色彩,而杜尚已经告别了“视网膜”时代。他向后人示范,视觉效果必须让位于观念的阐释,成为作品的次要成分。艺术就此沦为作者参与操盘交易的概念股。流风所及,当代艺术中最酷的人物就此摆脱了画家、雕塑家的身份,成为超然于物质形态的“艺术家”。前面忘了说,杜尚这辈子最上心的,是台球和象棋,凡事预先多看几步,也属题中之义。
西方现代艺术,经过莫奈、梵高、毕加索这几代巨匠,风格上的可能性,开始趋于饱和。对于杜尚这一代后来者,继续在表现技法上增加投入,将面临边际效用递减。而创造的核心部分,也将由制造转变为发现,还有选择。他选择了收益最大化的路径——放下画笔,转向工业制成品,将其定义出一套新的能指系统。至于所指,那只是填空题的答案。话不能全都让你一人说完了,总得留点儿给理论家吧?
杜尚的最大遗产,是降低创作的技术门槛。各种硬性指标一旦消失,艺术就成了抖机灵。他最为成功的精神嫡裔,都是另具别才的人物,比如设计广告出身的安迪·沃霍。作家戈尔·维达尔曾经这样臧否这位后现代明星:“他是我平生仅见的,智商60的天才。”他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坊,称之为“工厂”。这是一个民主的姿态,就像他那句将来每人都能出名15分钟的名言。
直到沃霍,艺术的话语总要设计人对未来的价值设定。如今,那个应许的未来已然落锤,证明预言落空,我们谁都没有15分钟的出名机会,只能眼巴巴看着全世界不到15个人,占据全部话语空间。比起以往的前辈,新一代明星只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中产阶级大众司空见惯各类噱头之后,他们追求的效果也从震撼转变为愉悦。那些超级昂贵的玩具,被超级富豪捧得日益抢手,也只有他们才能供奉得起。他们的艺术“工厂”,总有产品出现在曼哈顿的公共场地,从市政公园到陆军广场。
纽约本身正在变成美术馆。据说它与伦敦之和,已经占据全球艺术市场交易的六成份额。而这首先是资本的游戏。走出现代美术馆正门,街对面就是洛克菲勒中心那一片办公楼。其中之一正是佳士得拍卖行的纽约分号。这两年,那里拍出过毕加索《阿尔及尔女人》、莫迪里阿尼的《侧卧裸女》,都因为中国买家参与,刷新过售价记录。
购进历史名人的遗作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早已经被别人纳入收藏(也是部分价值所在),所以要等原主出手。老一代藏家多做长线,和藏品,甚至艺术家的情感联系也更紧密,后来者往往要等他们离婚,欠债或者过世——据说有人称之为3D(divorce、debts、death)——否则难有机会。在世艺术家的作品,于是成为更好的选择。首先,他们的作品至少是在增量通道,新派藏家转手也相对更快;其次,你只需要知道谁是当前的绩优股,用不着再去补艺术史课。这年头谁不是忙得尾巴冒烟?
还是同一家拍卖行。这里近年有一件创纪录的当代拍品,就是杰夫·昆茨的《气球狗》(橙红版)。这组小狗造型的金属雕塑共五件,算是限量出品,包括大红、洋红、宝蓝、橙红和铬黄。其中,洋红版在凡尔赛宫展出期间,还引发过不少争议。

也难怪。他最近一次高调出镜,是在《名利场》杂志。配发专题文章的是他的一幅近照,在健身房引体向上的全裸照。当然是背对镜头。快六张的人敢这样秀,总要有点儿本钱。对于这位当今最赚眼球的艺术家,自我暴露也不是头一回。大约1990年前后,他做过一件大幅作品,模特是匈牙利出生的A片明星奇巧丽娜。那是一系列油画、照片和雕塑,表现俩人的性爱(昆茨当年形貌略似年轻时的马龙·白兰多),叫《天堂制造》。
肤浅和犬儒,是昆茨摆脱不掉的恶谥。还有廉价,虽说他的作品在通俗意义上并不廉价。比如那件气球狗,那次就拍出近六千万刀,创出在世艺术家的记录。这种艺术甜俗夸张,厚颜无耻地歌舞升平,缺少内在性。可起码不给你添堵。也许对于满脸旧社会的评论人,拒绝冒犯本身就是冒犯。在和气生财的同胞面前,他们总爱祭出抗议界专业人员的标准。
这位衣着永远光鲜笔挺的前华尔街人士,对于市场营销,以及我们时代虚荣本质的体察,绝非一般凡夫俗子能比。问题不仅在于一个艺术家,是否可以兼任波提切利和洛伦佐·美迪奇;更重要的是,艺术是否必须批判,一定苦大仇深?西方十九世纪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把快乐贬逐到文化记忆的底层;人类情感中的小调、半音,一概被视为犯规。直到这个渐趋暗淡的繁荣年代。
这个时代总的精神,就是“给我们吃蛋糕!”。艺术尽管昂贵,但也有与民同乐的一面。对于不想买票去美术馆的广大吃瓜群众(其实MoMA每周五晚间免费入场,纽约其它博物馆的门票,也多为建议价),也有其它机会接受艺术服务,比如跑到洛克菲勒中心的通用电气大楼下,在当红艺术家的公共作品跟前自拍,从露易丝·布尔儒瓦的巨型蜘蛛,到村上隆的卡通人形,也包括这位杰夫·昆茨。
他的作品最近一次出现在这里,是一件巨型作品,叫做《中分木马》(Split-Rocker)。这个装置借用了儿童木马造型,兽头部分从中劈分为二,一半是木马,一半是玩具恐龙。这是一座立体花园,巨型钢架上插植两万余株矮牵牛花,内置复杂的喷灌系统维持生机,而那些速生速朽的植株,正是我们这个无常时代的表征。这件穿越雕塑、建筑和园艺界限的制作,宠物般讨好所有人,即先锋又商业,扮演着消费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近十几年来,这类“大而萌”的艺术品频繁出现在主要城市空间,接受公众的巡礼检阅,还有他们的仰望和惊叹。他们往往体量超群,否则很难在车水马龙,广告铺天盖地的都市环境中脱颖而出。这是由信噪比的要求决定的,就像昆腔在庙会、街市上生存不了一样。它们与生俱来的工业制成品特征,泄露出来自杜尚的基因源头。
百年前的先锋艺术,由于其原创性,带有修道院的朴拙气质,以及车库作坊样机的生愣。今天我们看到各种开发成熟的“产品”,材料、工艺和体量不断变化,具有高度的品牌辨识度,对于用户也更友善。也就是说,它们从不羞于袒露其商品属性。是商品就得交易,做工、用料就得考究,不能整天靠玩儿情怀忽悠甲方。粗陋的卖相并不反衬卖方的诚恳,两者之间从来不是正相关。那些做对冲基金,开科技公司的,哪个不猴儿精猴儿精的?新艺术背的后,是以宗教态度看待世俗事务的文化,奇观性是它唯一的超越部分。
上世纪反叛文化的老革命,面对新的形势,早已经进退失据。一段泡沫盈溢的历史幽灵,在福山想象中的历史终结处的最后瞬间,通过光艳的人造偶像附体作祟。而整个故事的起点,却是在纽约的另外一角。
【注】本文题图为《天堂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