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西闪
个人以为,《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沃尔夫冈·J.蒙森著)是2016年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且不说本身的学术价值,或者译者阎克文的翻译水平,单是钱永祥先生的导读就够我一读再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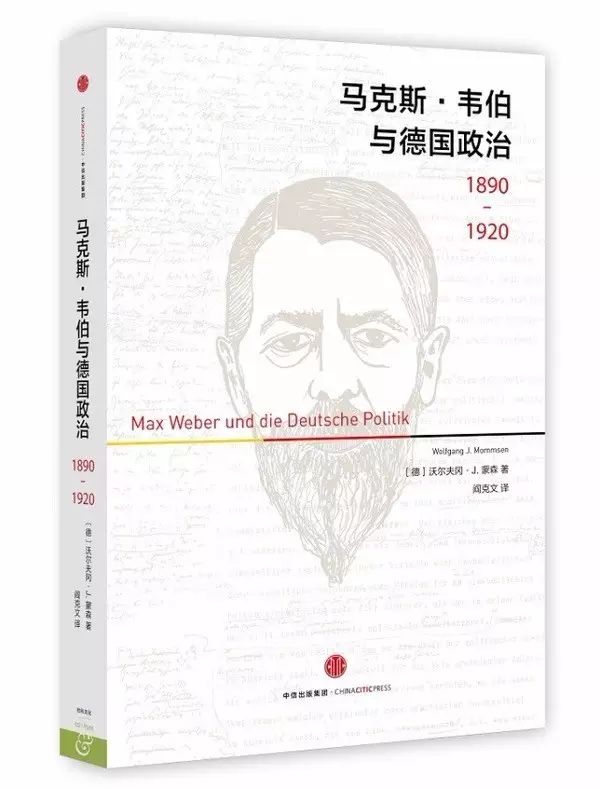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何许人也?有学者将他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我觉得相当准确。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视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决定力量,韦伯却看好资产阶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在组织上与效率上都优于其他制度,因而资产阶级不会被无产者“埋葬”,依然大有前途。大体上韦伯的学术与思想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展开。比如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他试图重新唤起资产阶级奋斗精神的一种努力。
之所以说“重新唤起”,那是因为韦伯认为,资产阶级的现状让人很不满意,尤其是德国的资产阶级。照理说资产阶级应该具有一种勇于冒险的创业家精神——这种精神的确存在于资产阶级的新兴时期,然而随着财富的积累与地位的稳固,他们开始变得保守,不思进取。由于德国统一很晚,政治进程也晚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因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出现也较晚,且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既缺少现实的判断力,又缺乏行动的勇气。他们虽然取代了贵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却很难抵挡阶级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接管国家权力的决心。
关于这一点,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说里说得很明白。他说,创建德意志国家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在这个国家创立之时,“没有从资产阶级那里采伐木料来制作民族的航舵。”可是很显然,他对资产阶级仍然抱有希望。正如他在另一个场合的演讲中所说,凡是不相信资产阶级还有未来的人,必定会对德国的未来疑虑重重。
把一个阶级的未来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未必没有抵梧。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强调个人自主与理性至上的自由主义,如何与那种动辄诉诸“集体情感”、“共同历史”的国家-民族优先的原则对接起来?韦伯好像没有仔细考虑。因为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韦伯生活在一种被称为“民族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下。
看看韦伯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他说,命运使德国背上了历史的重负,置身于一个兵器林立的世界,不得不像一座兵营那样保护自己的文化。他羡慕美国人,因为他们不必“和我们一样披挂上锁子铠甲,书桌抽屉里也不会像我们一样动辄就塞满了战时进军令。”但他坦然接受这一“命运”,认为德国的威权统治、殖民扩张乃至国际战争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且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胜利才能与德意志的民族成就并驾齐驱。他毫不含糊地宣称:“我们不可能带领我们的子孙后代走向和平与人类幸福,而只能进入无止境的斗争以保护我们的文化与人口。”因为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指英美)塑造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不利于体力和智力占优势的民族(指德国),必须施以冷酷无情的厮杀与斗争。
韦伯的这一政治立场,一直维持到1918年德国战败。而对于韦伯的这一立场,即使一再告诫自己不可以今日之是论昨日之是,我还是觉得很惊讶。要知道,韦伯历来被人视为自由主义的先驱者与捍卫者,而经沃尔夫冈·J.蒙森的解读,他在德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应该担负的政治责任,都大大改变了过去人们普遍的认知。难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会认为,一旦韦伯的政治立场遭此解读,将使“新生的德国民主失去一位创始人,一位显赫的鼻祖和一位天才的发言人。”
可是蒙森认为,韦伯在自由主义谱系中神话般的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塑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从德国自身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寻找可以跟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划清界限,又能支持战后德国民主的精神资源。很自然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在魏玛制宪过程中影响巨大的韦伯。事实上也是如此,在魏玛宪法草案的13名审议者中,韦伯是惟一不具官方身份的人。在魏玛共和国究竟应该实施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制的关键问题上,韦伯更是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就像他在写给妻子的信所透露的那样,宪法大体上完成之时,“非常接近我的提案。”可是,我们能就此认为,一战后的韦伯已经彻底转变了他对政治、权力以及国家的看法吗?恐怕不能。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与韦伯的理念脱得了干系吗?恐怕未必。
韦伯在德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深刻地关涉到一个问题: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果说韦伯的政治理想的失败反映了这两种主义的冲突和矛盾,那么韦伯的成功又作何解释呢?难道它们之间没有相互吸纳的可能?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似乎还少了些篇幅。
有意思的是,包括钱永祥先生在内,不少中国学者看到了当代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存在着某些类似的历史境遇,继而又注意到韦伯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某些困境上的相似性。这一点,在本书的导论部分钱先生有相当精彩的论述。不过我认为,这种相似性不可过于当真。时移世易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由则在于,那些试图在权力政治中扮演角色的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责任”二字于韦伯的意义。而我觉得,正是责任将韦伯看似分裂的学术和人生有机地结合了在一起。
阎克文先生在本书译序里提到,德国一战失败后韦伯给当时的德军主将鲁登道夫写了一封信,要求鲁登道夫等领导战争的人负起责任,把自己的人头自愿交给协约国,为德国的名誉献祭。之后,他和鲁登道夫还面对面的为责任问题争论了好几个小时。当鲁登道夫质问何为民主,韦伯的回答是:“人民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如果领袖犯下罪错,就把他送到绞刑架上去!”
本文原标题《用责任把思想与人生结合在一起》
【作者简介】
西闪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