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读冷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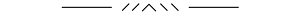
阅读新坐标
文 | 西闪
柏林墙倒塌后,正在柏林访问的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接受了一次手术。刚从麻醉中苏醒,他就跟人开起了玩笑。他问医生:“香蕉为什么是弯的?”医生耸耸肩,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没人去丛林里干涉它,把它掰直。”
笑话太冷,没几个人能懂。至于香蕉的意蕴,估计赫希曼本人也未曾细想。那个“香蕉共和国”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自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他就再没去过哥伦比亚,尽管那里是他为发展经济学奠定基础的地方。
正是因为哥伦比亚,香蕉才成为赫希曼喜欢的一个隐喻。1952年,时任哥伦比亚政府经济顾问的赫希曼被一个漫画家朋友画到了香蕉树上。画面上赫希曼坐在蕉叶上,只穿了一条短裤,光着上身,翘着二郎腿,严肃地盯着手上拿着的生产计划。计划中画着一只大香蕉,细还有细密的数字表格。在树下,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正在收摘果实,背景是地球的半个圆弧。赫希曼把这幅漫画做成了圣诞贺卡,寄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贺卡的下方有手写的标题:“香蕉是很好的食物。今天我们吃它,明天我们来计划。”
这当然是一种精妙的反讽,只有那些熟悉赫希曼风格的朋友才能领略得到。如果说香蕉意味着复杂对简化的嘲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赫希曼的人生也是如此。毕其一生,他都在揭示“计划”的荒诞与失真。同时他呼吁人们正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从中提炼行动者所需的希望,以此来质疑和对抗妨碍进步的那些僵化的观念——无论它们是保守主义、理性主义、目的论还是别的什么宏大观念。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可能主义”(possibilism)来形容自己倡导的这种积极的态度,一如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所言,“快乐可能会令人失望,但是可能性永远不会”。
赫希曼之所以新创“可能主义”一词,也是要跟天真浪漫的进步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一个可能主义者(possibilst)或许在行动上会具有堂吉诃德的某些气质,但他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讲,可能主义者是对赫希曼自身的刻画,也是对某一类行动者的定义。这样的人,应该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高度敏感,有着强烈的务实精神,却从不把确定性当作思考和行动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准确地抓住了可能主义者的精神内核,他将赫希曼的传记题为《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说明了这一点。
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实在太丰富,太传奇。他1915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青年时期投身战场,成为首批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战士。二战期间,他先是法国军队的士兵,后来从事地下活动,营救过夏加尔、杜尚、阿伦特、本雅明、亨利希·曼、布勒东、林飞龙等一大批名人。为躲避追捕他逃亡美国,之后又再度从军,打回欧洲。
战争期间赫希曼还继续学习经济学,发明了著名的基尼系数,写出了首部著作《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退役后他进入联邦储备委员会,为马歇尔计划出谋划策,是复兴欧洲的幕后高参。之后他出任哥伦比亚政府的经济顾问,并在那里工作数年。1956年他成为大学教授,凭借《经济发展战略》一举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
1963年,他出版了另一部轰动之作《迈向进步之旅》。在这本书中,他“高举实证的火把,近距离地、尽可能细致地考察了拉丁美洲政策问题的历史”。在他的影响下,拉丁美洲迈入了一段颇有希望的改革历程,其中一位改革者还当上了哥伦比亚的总统,他因此被人揶揄为“改革贩子”。事实上,赫希曼的思想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进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70年代,发展经济学渐渐淡出赫希曼的视野,他把眼光投向更深刻的现代性问题,尤其针对现代学术的弊病。在他看来,当现代社会的危机越来越深重,学者的眼光却被日趋专门化的学科分类分割成了碎片,根本无法应对现实。因此社会科学诸领域不仅要加强合作,还有必要促进彼此间的交叉与融合。有可能的话,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还有其他社会学科,应该成为统一的科学,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他引用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的格言提醒同行们:“一切过于简单的都不真实;一切过于复杂的皆归无用。”
赫希曼的名著《退出、呼吁与忠诚》完美地展示了何谓统一的社会科学。全书仅有97页,比一篇论文长不了多少,却字字珠玑意蕴隽永,堪称传世杰作。经济学界将这本书誉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宣言。政治学家指出,赫希曼对呼吁的分析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政治哲学家的反响也非常热烈,他们还组织了专题讨论会,把赫希曼比作社会科学家中的摇滚巨星。
不少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为赫希曼没有获奖而抱怨,并把他与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尔赫斯相提并论。年轻的学者们觉得赫希曼是最接近“思想之神”的知识分子。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他的评价更加热烈。他说:“除了阿尔伯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术上的朋友如此理解我,让我如此崇拜。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古希腊人会把我们这种关系称为爱。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这样说了。”
在一次颁奖仪式上,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了赫希曼早年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强调了赫希曼在马赛拯救众多艺术家和学者的经历,并把他称为“当代英雄”,而我更愿意把他称为“神秘博士”,因为谦逊的他很喜欢让自己隐没在神秘的时光之中。就像他在一篇笔记里写的那样,有些人的一生有一个毕生一致的崇高使命,这个使命就足以概括他们的一生。“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一条让讣告作家写起讣告来非常容易的人生之路呢?”
《入世哲学家》只是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第一部传记。可想而知,关于这位当代英雄或神秘博士,探索之路刚刚起步。
![《入世哲学家》/[美]杰里米·阿德尔曼 著/贾拥民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http://mmbiz.qpic.cn/mmbiz_jpg/E6ME5dOJ0orib68OicvBRg8UnpdN9nrePxt0RtIa2IiaQq81CpNSATclKtlk0KfXPAm0gQyOiccuFb88eb9LpKIqSA/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
▲ 《入世哲学家》/[美]杰里米·阿德尔曼 著/贾拥民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
题图:为二次大战战犯德国步兵上将安东·多斯特勒担任翻译的赫希曼(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