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叶克飞
爱尔兰与捷克类似,它们都是地理上的小国,却又是文学大国。伟大而迷人的王尔德出生在都柏林,尽管当时的爱尔兰还在英国控制之下。同样耀眼的名字还有均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叶芝和希尼,写下《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创作荒诞戏剧《等待戈多》的贝克特。即使你不想那么文艺,只爱革命时代的激情,那么也有伏尼契的《牛虻》。直到当下,约翰·班维尔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常客。但是,特雷弗与他们都不一样,尽管他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受益匪浅。

以88岁之龄去世的威廉·特雷弗,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也被《纽约客》誉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他于1928年生于爱尔兰,曾就读于爱尔兰最著名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1952年移居英国,居住于德文郡,这也是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乡。1964年,特雷弗凭借小说《老男孩》获得霍桑顿文学奖,从此全身心投入写作。
这部处女作委实出手不凡,它讲述一群老校友委员会成员在推选下任会长时的勾心斗角,其间穿插回忆,原来,他们当年在学校时同样如此。矛盾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失,甚至更让人无法释怀,偏偏身体和精力已经很难承担这样的争斗。咄咄逼人的表象之下,尽是孤独与悲凉。
他的大学时代正值二战后期,若是身在法德,难免跌宕于大时代;若是身在匈牙利波兰捷克这样的国家,更会在有生之年见到两种极权的兴盛与衰亡,极有可能在光怪陆离中成为一个抗争者。可是,他生于爱尔兰,即使战火最为激烈时,也有一块相对宁静的天地。当昆德拉从捷克流亡到法国,当马洛伊从匈牙利流亡到美国时,他也选择了自我流放,可那是从爱尔兰到英国,从一个世外桃源前往现代文明发源之地,从一种从容走向另一种从容。他的漫长人生几乎没有变化,那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幸运,而且并不影响他以敏锐的观察探究人类心灵。
所以,特雷弗只会以简洁的短篇形式写那些小城或山区小镇的故事,将生活剥茧抽丝,袒露所有的困顿、悲苦、欺骗、背叛和悲悯。即使涉及政治,如英国统治爱尔兰时期的旧事,他也并未将一切过错推给英国人。他始终暗示自己的读者,人类完全可以超越回忆,超越不幸。在特雷弗的小说里,你只能见到小人物,他们卑微不幸,他们迷惘忧伤,他们放纵荒唐,不过,他们都来自爱尔兰。客居英国的他曾说:“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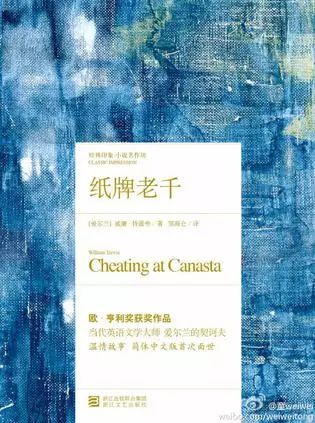
我所读的第一本特雷弗,是2012年1月出版的《纸牌老千》。它作为最早的中译本,其英文原版反倒相对“新鲜”,诞生于2007年。八十岁高龄的特雷弗写作此书,大有看透时间的冷酷。开篇的《裁缝的孩子》,讲述一个年轻人驾车意外撞死一个孩子,孩子母亲是一个穷困落魄的女裁缝,她目睹车祸却未告发,而是转移孩子尸体,造成非车祸致死假象。她随后执着地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里,希望“得到”后者以改变自己的不堪境地。受到良心谴责的年轻人则始终挣扎,他知道自己终将走向这个放弃为孩子的报仇的艰难女子。
同样在2012年读到的《雨后》,其实是1996年便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曾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书中有十二个故事,最让我喜欢的是《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那种平淡悠长的韵味,几乎能让我想起小津安二郎。钢琴调音师有两任妻子,前任维奥莱特已经故去,他与继任贝尔结婚时,已然垂垂老矣。友人们说:“不管怎么说,她算是得到了残余的他。”但这样的得到并不能让贝尔满意,因为尽管维奥莱特已经故去,可贝尔每做一件事,都会以维奥莱特为假想敌。在人为制造的种种疑惑中,生活仍在继续,只是,“贝尔赢得了结局,因为生者总是赢家。而这似乎也是公平的,因为维奥莱特赢了开局,并且度过了更为美好的岁月”。

书中有不少一针见血的金句,比如“所谓美满,到头来总有一天,在离婚法庭上,被叫作乏味”,又如“用恋爱去修复自己对爱情的信念,过于肤浅和随意了”。可是这些金句,最后都化作小人物的无助,就如《孩子的游戏》里所写的那样:“他们轻而易举地成了伙伴,喝着鸡尾酒,在盛大宏丽旅馆登记签名,可这种伙伴关系只不过是凑巧给了他们,是从别人的生活里丢出来的一件礼物。无助,才是他们自然的状态。”这对孩子,其实来自双方父母离异后所再组建的家庭,没有血缘关系却成了兄妹,“在和平协议里被抛来抛去的这对无助的当事人成了伙伴”,并在阁楼上扮演自己父母来还原昔日吵架的场景。
相比《雨后》,《爱情与夏天》更让我喜欢。每次重读此书,都会想到黄耀明那首《忽而今夏》,绵密鼓点构成的间奏,真的宛若风吹稻浪,孤独少年迷惘之中,“听见一颗心叫我一手敲碎”。可《爱情与夏天》分明不似《忽而今夏》,没有青春激昂,亦无荷尔蒙冲动,只有平平淡淡,连婚外情都带着几分恬静。之所以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想来是因为同样的迷惘吧。
于特雷弗而言,《爱情与夏天》堪称其早年爱尔兰乡村生活的一次最好总结。爱情中的离愁别绪,与大时代的去国相融合,所告别的,唯有随时光而渐渐逝去的旧日乡村。他笔下的乡村,在时代前行的脚步中渐渐落伍,以至于被淘汰。它已无法给予作家足够的养分,却成为作家永恒的追忆。
《爱情与夏天》里婚外情如此恬淡,另一部小说集——2015年出版的中译本《出轨》就更是“徒有虚名”,你休想在书中找到“重口味”元素。

《出轨》的首篇《坐对死人》,讲述艾米莉丈夫去世,正在等待收殓,艾米莉向两位修女倾诉心声。她讲述过往的爱情,也讲述丈夫的暗面,如贪财好赌,讲述自己的纠结内心。“她说起过的对丈夫的爱,已经被忧惧消耗殆尽,只剩下一层空壳,但她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怜残余的存在,就像她在两位访客面前也没否认一样。只是,她无法悲伤,也无法哀恸:剩下的何其少,毁掉的又是何其多。”如果这也是一种出轨,何其悲凉?因为,它连自己都要背叛。
《格来利斯的遗产》讲述一个男人意外获得一位女士赠予的大额遗产,而他们的交集仅仅是在图书馆里探讨哲学和文学。如果这也是出轨,那么也是一种纯粹的、摆脱了物质桎梏的精神交流。这说起来很美,可是在世俗眼光中,这种交流注定会遭到猜疑,并被视为危险。最终,男人选择以绯闻与谣言来保全这份情愫,“冬日的花朵已然飘落零散,隐没在一道秘密的暗影中,而欺骗的幻象成全了一份静默无语的爱情,为它赋予尊严与荣光”。这又是何等美妙的选择?即使无言。
《在外一晚》讲述一对并无感觉的相亲中年男女互相利用,却在分开时感受到莫名情愫。“当地铁载着他们在灯光摇曳闪现的黑暗中快速穿行,这种感觉依旧盘恒不去,甚至变得亲近私密——仿佛他们曾经暗通款曲,共赴巫山。”
同题短篇《出轨》同样克制,这是办公室同事之间的婚外情,女方跳槽另找工作,男方留守公司,而在婚姻上,他们的选择如出一辙,这使得这个平淡故事有了几分寓言的味道。结局同样平淡,“就因为一个轻微的小问题,两人共同经历的朝云暮雨,一起携手度过的花晨月夕,却要宣告终结。她无法想象那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午夜梦回,怔忡惝恍,一时间不知是什么让自己惊魂起坐,然后在蓦然闪现的意识中爬梳搜罗、寻寻觅觅,却只发现那荒寂空无的真相,怅惘茫然之际,沦陷于无能为力的绝望”。但是,最终,特雷弗还是给了些许希望:“未来其实也并不会像现在看上去的那样凄凉惨淡,未来仍然会有由他们之间的寡言默契所带来的美好、满足和感激,未来仍然会有他们自己——是这一段曾经沧海的爱恋,把他和她变成了各自的样子。”

今年,我读到了特雷弗的《费丽西娅的旅行》。于中文版而言,这是一本2016年的新书,但英文原版则创作于1994年。而且,我早已在DVD中与它相识,它的电影版曾入围戛纳电影节,有人评价“自《沉默的羔羊》之后,没有看过比这更好的温柔的惊悚片”。
这是一个未婚先孕的爱尔兰少女的寻人之旅,充满着绝望。她来到英格兰中部地区,寻找失联男友,却落入重重陷阱之中。
如果故事仅及于此,那么不过是一个公路故事。但特雷弗的爱尔兰情结融入其中后,一切便变得不同。女孩出身于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曾祖父在1916年的爱尔兰反英起义中牺牲,曾祖母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家庭,父亲为家族传统而骄傲,并因此仇视英国,女孩却反感这种壁垒分明的价值观。她的男友也许是个英国军人,这让父亲大为恼火,将之视为敌人,她却毅然离家出走,远赴英国寻人。看到这里,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代际冲突的故事,一切终将证明老人的过时,可特雷弗却不这样想。当女孩遇到危险时,所能倚仗的恰恰是源自曾祖母的血统,那种爱尔兰女子的坚忍与睿智。
没错,他深爱着爱尔兰,并为此不惜离开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