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许倬云
今日世界的现代文明,承袭了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总是将人的起源,联系于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故事。而且紧接着,就是人犯了违背上帝的原罪,人若是要赎罪,只有坚定地信仰上帝一途。其实,世界上各处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系统,也因此有不同的人类起源的传说。
这篇文章里,我将从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的起源说起,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人的认识,与上述西方上帝造人的取径完全不同。
中国疆域广阔,各处造人的传说也并不完全一致。不过,至少在战国时代,盘古开天与女娲造人,已经是大家都接受的一个说法。这一个盘古、女娲传说,应当是起源于华中长江流域,蛮苗系统的古代民族。可是,在战国时代,屈原的《天问》就以这个传说,作为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的说法。
在没有开天地以前,宇宙是一团混沌。混沌的形状,就如一个巨大的圆卵。圆卵忽然裂开,其中坐了一个盘古,他举手将清轻的空气往上推,成为天空;将重浊的资料往下压,就成了地面。盘古的骨骼成为山岭,血脉成为河流,毛发成为草木,这就是世界的出现。

▲ 盘古开天辟地
因此,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老庄所说的“无为有之母”,以及“混沌”是最原始的形态,颇与这个说法相符合。如此解释宇宙的起源,似乎比先有一个无处着落的上帝,更具有哲学意味。否则,大家还是会问:上帝又从哪里来?今天太空物理学,讨论到宇宙的起源,基本的假设是:宇宙从一个点开始,然后爆炸为宇宙。我们一样会问:那个点在何处?在数学意义上,点不占空间,因此等于零。然而,这零又怎么可以爆炸?
盘古之后,女娲出现了,女娲也就是女性的意思。在道教的神道系统中,女娲就相当于斗姆,在今日的民间宗教中“先天老母”应当就是女性的原始。这一观点,也和老子所说“元妣”的观念相当。女娲用黄泥和水,捏成人形,给予其生命,就成为人类。
女娲这个角色,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整顿者。在水神共工发怒,撞倒了天柱不周山后,女娲烧炼地上的五彩石,补上天的缺口。大水泛滥时,女娲又用炼灰,堵上了泛滥各处的洪水。从这个方面看,女娲的力量是地的一面,和天对立而相辅相成的。虽然有如此的神力,然而,女娲并不是统治宇宙的神祇。她不是上帝,她只是代表一个力量——母性和地。与她相对的,应当是天和男性。
战国和汉代的刻石图像中,常见伏羲与女娲。两者都是人面蛇形,二尾交缠象征着交配。他们二人手中,一个手持圆规,一个手持矩尺,可能就是天圆地方的象征。综合上面所说,女娲造人和补天,只是象征着母性的原创力。这一个传说的意味,毋宁指出“人”本身,是自然出现的,并不是屈服于上帝的子民,更不需要背负上帝与人的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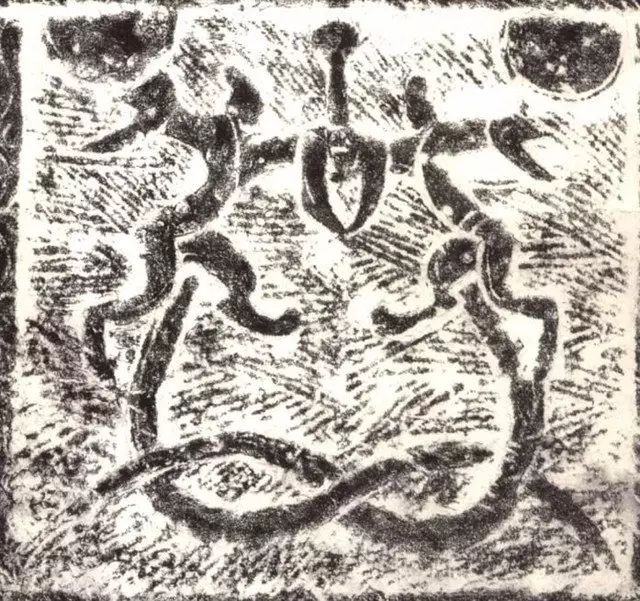
▲ 伏羲与女娲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沿着太平洋岸,从辽宁的红山文化,一直到浙江的良渚文化,都有高天的信仰,而且是以太阳作为象征。太阳高高在上,成为中国“昊天”的起源。红山文化的高山上有女神庙,还有酋长或是祭司的坟墓和祭坛。祭坛、坟墓四周,都有中空、无底的陶罐,围绕着基地排列。这一安置,毋宁是象征天地之间的沟通,而以神圣的祭坛,作为相通的管道。墓主是一个尊贵的人物,还有法器陪葬,他也许就是大祭司或者酋长,负责天地之间的交通。
在良渚,琮形的玉器——就是一个外方内圆的玉管,有人说其上是一个圆盖,其下是一个方底,这也是象征着天和地之间的沟通管道。有一件琮上,刻着一个飞行的神像,也许他就是天神?亦或是神的使者?还是人间负责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我们不知道。在另外一些琮器的边上,往往刻着一只飞鸟。在许多地方的传说中,飞鸟常常是天神的使者。这些良渚的鸟形,是不是也是天和地之间沟通的使者?在渤海湾四周的太昊和少昊文化的传统,他们在古代的首领们,太昊系统是以云为号,少昊是以鸟为官:这种安排,也正是象征着天和地之间,经过人,会有一定的沟通机制。

▲ 良渚玉琮
有一件汉代的楚地绢画,虽然时代很晚了,却可能继承了古代的传说。这件马王堆的绢画,分成三个层次:最上一层是天,最下一层是地下的水,中间则又分成人间和死亡的境界。有一棵大树,植根在底下层,枝叶却是在最上一层;枝叶上面有十只鸟,可能就是当年的太阳鸟。
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一件青铜树,树干上栖息着许多鸟——这一枝神树,可能就是和马王堆绢画上的树一样的天地之树。这是联系天和地之间的管道,人却正在管道的中间,上通天,下达地。宗教史家Mercia Eliad 指出:世界许多地方,都有这种通天树的观念,树到后来,可能演化成高塔,例如《圣经》中的巴别塔。似乎中国古代的这一观念,也并不独特。只是,在人神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认为,“人”却是沟通天地的中介。
人的身体,在中文里的解释是:圆颅方足,象征着天圆地方——人本身俨然是一个宇宙。战国时代,阴阳家与五行家两个自然哲学学派,各自陈述他们对宇宙的理解。阴阳家认为,宇宙之间有阴和阳两股力量,交缠互动,成为宇宙运行的动力。宇宙之间所有的事物,都有阴的面和阳的面。两者并不只是对立,也能互补。
五行家则将宇宙的构成,归纳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因素,或是五个成分,五者相配构成万物。每一件事物,都有特定的五行成分,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阴阳五行家结合在一起,成为秦汉以后,中国自然哲学形而上理论的基础。
阴阳思想的产生,当然是首先认识到两性交合能够创造新的生命,才将生命力归纳成为阴和阳两个因素。这两因素不能独立运作,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因此,女娲和伏羲必须同时存在。阴阳之间,应当调和而不是对抗——在两个因素之中,永远是寻找平衡,任何一面的过强或过弱,都会造成整体的不平衡,而导致灾难。
五行则是古人从日常生活中,引申出来素朴的理论。任何一项因素或者功能,都不能不受到另一方向的反制。这五个因素之间,必须要调和,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活体系。同样地,每个元素之中,都有强和弱的区隔,过强或是过弱,都会造成灾害。因此,五行观念正同阴阳观念一样,指出人类生活之中各种因素,必须在平衡之中相互调和。失去了平衡,维生的资源不仅不能有助于生存,反而可能妨害了生存的环境。
这样的永远趋衡的动态宇宙,当然会牵扯到时间的观念。时间轴线,在现代科学观念中,是线性前进的。在基督教神学观念中,自从上帝创造天地,时间就永远延续下去,到最后审判的日子,人类的时间终结,但宇宙的时间还会进行。中国式的观念则是循回的,也是在许多条件之中,不断地寻求一个“完足”,而这些条件参差不齐,因此“完足”的境界很难达到。中国人的宇宙中,时间的观念,可以以汉代最后经过形上学思考,发展的年历学作为指标。
经过若干演变,从汉代开始,以至于现代科学进入中国为止,中国人的历法是按照太阳历和太阴月配合:太阳年一年的“岁实”,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太阴月的“朔策”,是二十八又九分之五日,一年必须要有十二次月圆,每个月圆之时必在月中。单单凑齐这个条件,就需要相当大的公倍数。每一个太阳年,在中国历法上,划分成十二个节、十二个气,每一个关键点,都代表着中国靠近北方的大陆气候转变的关口。因此,这些节气的名称,都是农耕程序必须要注意的天气转换的节点。
再加上中国人的天象观念,宇宙是个大圆球,日月加上金木水火土五星,每一个星体离我们的距离代表一层天,这七层天相当于同心圆的层次,围绕着地球。历法家理想上的宇宙起源日,是在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在这一天恰好是立春,而立春的时间恰好掉在正月初一日的子夜。将所有这些因素调和起来,取得的最小公倍数,

▲ 古代中国人的天象观
从汉代元始年间,乃是两千七百多年前,历法学的术语称为“上元”。但是,即使到了我们这一个大周期的终结,时间也不会停止;日月和五星的轨道,在中国历法上,也有不断变动的规律。于是,一个大周期之后,只是另外开始一个新周期,时间永远进展。“人”却是观察这些变化的主角,于是,宇宙的永恒进行,就系于“人”之存在。
论其根本,阴阳家的起源应当更早。五行家的出现,必定是需要到铜器和铁器成为日常事物时,才有“金”相的功能。阴阳互动的形而上学,当然是和上述伏羲、女娲之间的相生相克,有历史上的渊源。
到了汉代,董仲舒综合儒家的人间伦理学,和阴阳五行的理论,组织为天人感应的学说。在他的庞大宇宙系统中,大小宇宙层层套迭,人体也是一个自我完足的小宇宙。从天地的大宇宙,到人间秩序的宇宙,以至于到人体之内的小宇宙,彼此间互相感应。不仅是大宇宙会影响小宇宙,小宇宙的变化,一样会回馈于大宇宙,引发相应的变动。在这些宇宙中,任何因素都不能过强,否则会压倒其他的因素;也不能过弱,不然也无法保持各种因素之间的动态均衡。
宇宙内部和宇宙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反映在人和天地的关系上。从汉代以后,人们就认识到“人”在大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样重要的地位——天、地、人三才,是大宇宙的三个层面。因此,汉代以后出现的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在其原始的“三官”,就是天、地、人;到东汉以后,“人官”的部分才被“水官”代替。“人”不是屈服于自然秩序的一类生物,反而是各个层次宇宙的命名者和解释者,是和天地并列的宇宙的一部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不仅是说天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人的变化依然能影响到天。人的变化——尤其是集体的行为,例如国家的政策或政治体制运转的状况,都会影响到宇宙的均衡。从汉代开始,国家的正史往往会包括一章,称为“灾异”“祥瑞“或者“五行”,记载了气候灾变等现象。并且,著史者常常将其与政府的作为相联系,认为是人间的若干措施有所偏差,才导致了气候和其他的自然变化。举例言之,假如皇帝过分依赖皇亲国戚,或者女主专政,这就是阴气太盛,会导致严重的水灾。又譬如,用刑过度或政府的苛政,会造成肃杀之气,以致秋天有严重的早霜,伤害了农作物的收成。
凡此形上学的玄虚之说,当然都是附会。不过,这些想法也确实影响历史上中国人的行为。谏官往往以灾变的出现为理由,理直气壮地纠举政府的行为失当。当天人感应理论刚刚出现,汉代的知识分子,确实常常借着某些灾变的时机,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甚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建议皇帝退位。以上只是说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密切相连的。“人”在宇宙之间,不是居于从属地位,而是在天、地、人三才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直到今天,中医的理论,很大部分是从天人感应之说,以及阴阳五行的形而上学入手,建构了一套人体内部各部分的平衡理论,也建构了人体系统与外在大宇宙系统之间的呼应关系。
冯友兰的“新原人”之说认为,人生所处的境界,可以有原始、功利、知识和天地四个层次。我们生在原始状态,应当是生物性最为突出。然而,我们不当自甘于生物,因此,才有“厚用利生”的需求和行为,这是功利的境界。在功利之上,我们还需要将其提升到理性的知识层面。最高的境界,则是从功利升华为与大宇宙呼吸相通的天地境界。他认为这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依赖于我们的“觉解”。“觉解”二字,也许正相当于儒家心学中所说的“悟”。当然,这两个字与佛道的觉悟和解脱,也有明显的关系。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讨论,回到中国民间对“人”的理念。上述中医的人体观念,其实就是代表了民间已经由“人”学入手,形成了一套医疗认知体系。在民俗信仰之中,也从精、气、神的理论往下延伸:南北朝时代,道教的炼丹先是从炼制药品开始,从医疗保健推演到长生之术。
服用丹药可以将生命延长,甚至于永远不老。这个愿望本身,就代表了生命是可贵的,值得延续到无穷尽。从炼丹的观念,又发展出内丹学说——据说,人可以从自己身体之内,通过一套方法,开发出自己的真火和真水,将其重新修炼以改造肉身。

▲ 古人炼丹
最高的境界,可以将精、气、神中“神”的部分,在自身内部“结内胎”,“内胎”可以进一步炼化为纯熟的“元神”。按照道家的神秘学说,“元神”才是真正的自己,可以摆脱肉体永远存在,成为神仙。即使没有进化到神仙的地步,“元神”一样可以短期地离开身体四处活动。所谓“元神”的观念,几乎就是陈述人体本身可能达到的永恒状态。人自己的努力,可以修炼到如此地步,“人”的可贵,显而可知。
中国的民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妖精古怪,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内,蛇妖狐仙处处都有。按照中国人一般的观念而言,古老的物体或动物,都可以成“精”;“精”的最高层次,则是进化出来人形,以人的形象,超脱了原来的动物或是对象。人可以成仙,物可以成人,所以说这些妖精,理论上还可以进一步进化成为仙,与天地同寿。由此可知,“人”这道关口,是高于一切事物和一切其他生命的。“人”的地位之可贵,就不是承受神惠的受格而已了。
冯友兰的“觉解”,在民间宗教之中称为“修炼”。中古时期,中亚一带的救赎教派传入中国。最初,这一教派还保留原来的面貌,例如祆教和景教。后来者,除了在中国的伊斯兰教能够保持原貌外,其他救赎宗派都大量吸收了中国道教的一些教义,混合成今天常见的一些民间教派,例如一贯道和过去大家熟悉的各种民间信仰。他们所寻求救赎的途径,不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救主,而是靠内修达到的境界。一贯道的“无生老母”,就是道教从无到有的转换。走到这一步的悟解,一样是从清理人体本身和人心本身的污浊部分入手,渐渐提升直至解脱。“人”本身可以达到的境界和地位,不需要仰望神恩就可以做到。
另外一些不是救赎派的宗教,例如妈祖信仰、王爷信仰等等,这些神祇的法力,可以解除人间的困苦和灾难,也可以在人死后将其引导进入极乐世界。不过,这些神祇也不仅仅是使用外在法力加以救赎,而是还要看看这个人自身的境界,至少是行为品德的修为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神仙才会伸出援手。虽然,庙宇门前有无数的信徒烧香礼拜,也有神坛前的捐献和贡纳。然而,认真的信徒一定会告诉我们,单单靠这些奉献不能获得功德,只有通过内在的修行提高自己的品德,神仙才能将信徒引进极乐世界。
很多不了解的人以为,中国人是靠念佛和施舍购买神恩。有一些愚信之徒,以为做些功德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知,即使民间宗教,都看重人本身是否具备至善的条件——从至善,才可以提升到解脱,提升到超凡入圣。
总而言之,从中国的造人神话,一直到今天的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一部分。儒家的人文伦理,将在下一篇文章里讨论。但本文所说而言,“人”不假外求,足以依托自我的不断完善和提升,最终超越生物的境界,也超越物质的限制。这当然是唯心论的论述,只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一信念其影响极为深远,也极为普遍。与犹太基督教义中“人”的地位相比,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二字,具有更重的分量。
(本文原标题:《天地人神的世界》)
【作者简介】
许倬云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