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姜鸣
▍1881年出现的彗星
光绪七年五月,军机大臣左宗棠奉旨察阅北京周边地区水利状况。他出京去涿州,二十三日抵达天津,会见多年未见的老对头、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把盏言欢,似乎从前种种龃龉,都付笑谈挥去。二十五日分手,左宗棠乘舟沿大清河西去,二十七日抵赵北口。二十八日(1881年6月24日)清晨,在换轿返回涿州的路上,忽然看到一颗明亮的彗星自北指南,划破宁静的天际。
我们今天知道,彗星是星际间物质,是进入太阳系内亮度和形状会随日距变化而变化的绕日运动的天体。当彗星离太阳较远的时间偶,只有一个暗而冷的彗核,当它接近太阳的时候,才在太阳引力作用下,由头部喷出物质,形成彗尾。英文Comet,是由希腊文演变而来的,意思是“尾巴”或“毛发”,也有“长发星”的含义。而中文的“彗”字,则是“扫帚”的意思。
由于古人对彗星缺乏科学理解,作为一种异常天象,彗星往往被暗示着兵灾、饥荒,或者重要人物死亡、国家动乱,也预示上天对人间帝王施政行为的警示。正是这种神秘力量,每当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彗星出现后,必然引起统治阶层的高度关注和敬畏。左宗棠后来把这个观察写信告诉李鸿章,并说:“占者言人人殊。特诏修省,以儆天戒,想荧惑退舍,亦不远矣。”
住在北京的人们,观察到这颗彗星是在次日。张之洞说:“二十九日夜间,彗星见于参、井之分。”(参、井为二十八宿中的星名)六月初一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破晓醇邸书来,云彗星见于西,其光可骇,盖家人辈亦于是夕亥初见之矣。”显然,醇亲王奕譞也将彗星出现视作大事,漏夜写信与翁师傅沟通情况。初二日,翁同龢继续记录:“亥初彗星见于西北,其光白,长丈余,乍明乍晦,因有云气也。北斗直北,约在井宿分,恨窥天不识耳,闷甚愁甚。”
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每天都在天穹出现,引起国家上层广泛的不安和焦虑。初四日,翁同龢发现,慈禧太后“因星变兢惕,串凉热,痰中血沫,筋骨软,健忘更甚”。初七日,翁同龢在李鸿藻家,听到来自天津的访客刘文锦讲,彗星已入紫微,光指北极,不由“中怀如捣”。他还记载贝勒奕劻说,街上路人聚观天象,流传着各种谣言,“闻之心悸”。
六月初九日,清廷发布上谕:
数日以来,彗星见于北方,仰维上天示警,祇惧实深。方今时事多艰,民生未遂,我君臣惟有交相儆惕,修德省愆,以冀感召祥和,乂安黎庶。尔在廷诸臣,其各勉勤职守,力除因循积习,竭诚匡弼,共济艰难。各省封疆大吏,务当实事求是,认真整顿,访察闾阎疾苦,尽心抚绥,庶几日臻上理,用副朝廷恐惧修省应天以实,不以文至意。
▍彗星引发的官场斗争
初十日,刚刚越级提升内阁学士的张之洞上奏《请修政弥灾折》,指出自古以来遇到灾变警示,不外乎修德修政。他认为今日修政之要,包括用人、言路、武备、禁卫数端。关于用人,建议“内而部院卿寺各堂官,外而督抚将军诸大臣,其有蠹国害民、旷官费事、昏庸鄙劣、物论不孚者,择尤请旨,立予罢黜数人,以儆其余”。小人革去,长官换贤,才“可以讲求自强之略,储材之道,察吏之方,理财治军之策”。关于言路,他说四月初二日曾有上谕,命诸臣对用人行政各方面剀切指陈,不可稍有避忌。然数月来言者寥寥,台谏失责,各种信息无法上达,应当申谕有言责诸臣,对于臣僚贤否、时政遗阙、直言无隐。“言而当者奖之,不当着容之,则谠言日至矣。”

▲ 外国人观察到1881年大彗星的情形
全国正处在热丧之中。此前不久,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突然薨逝,灵柩停在景山观德殿,各种丧礼都还在如仪进行,彗星成了敏感话题。故聪明的张之洞,在奏折后面夹进一个附件《星变修省勿过虑片》,他安慰慈禧:“星辰变异,正由上天仁爱人君,因事垂象,俾得早为之备。”又说这次彗星,较之前数次所见大有不如。光淡气薄,亦无芒歧,所出所经部位,亦非要地。且逐日递减,未犯垣中。
他引用《春秋传》中典故,齐国出现了彗星,晏子说:君无违德,何患于彗?又说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澄汰不职的。涤荡积弊,就是除秽;登进贤良、奋发振作,就是布新,不加儆惕预防则为祸,增修政事、益臻治安,则转可为福,实非不解之灾。太后闻星变之后,过于忧焦,寝食不怡,必须保重身体,早臻康复。近年中俄因收回伊犁交涉棘手,沙皇却自薨了(其实是俄国民意党人3月1日将其暗杀),“中华安如磐石,是天之眷顾中国,福祚我朝,信而又征”。
六月十一日,右庶子陈宝琛奏《星变陈言折》,指出今月以来,彗星夜见,经旬不减,致烦圣虑。彗星之警,断断不在君上,而在臣下。建议选择职任最重而衰庸不职者斥退一二,以答上天谴告之心,振作臣下奋勇之气。
陈宝琛选了三人供朝廷选择:一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称其近来年齿渐衰,暮气太甚,诸事不理,在危疑扰攘关头屡次请假,望朝廷念其前劳,许其休息,以礼赐告,曲全老臣。二是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程祖诰,性既昏庸,人亦猥琐。称其见一尚书、侍郎,卑躬屈体,有同属吏。志节风骨,均不足以表率谏台同僚。请即行退休致仕。三是吏部尚书万青藜,曾三次被参劾,依旧腼然居六部之首,最为舆论不平。兼管京尹(北京市长)二十年,北京吏治日益败坏,皆凿凿人口,请朝廷若许其休息,曲全老臣,则为天下之幸。
这道奏折为朝廷提供了“扫除污秽”的具体方案。最高层踌躇两日,十三日颁布上谕:“陈宝琛奏星变陈言请斥退大员一折,所奏甚为剀切,然亦不无过当之处。大学士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宣力有年,襄办诸事尚无过失之处。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该大学士受恩深重,精力尚健,自当恪矢公忠,勉图报称,不得稍涉懈怠。吏部尚书万青藜,办理部务有年,尚无贻误,惟屡经被人指摘,众望未不孚,着开去翰林院掌院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祖诰,才具平庸,以原品休致。”这个决定,保全了宝鋆,免去了万青藜的一个兼职,而程祖诰则躺枪,成为彗星出现后的第一个牺牲品。
用人问题,不外乎除旧布新。光绪初年主持大清日常政务的军机大臣,除恭亲王奕訢之外,另有满人文祥、宝鋆和汉人沈桂芬、李鸿藻,沈、李分别以籍贯而被视作南北两大官僚派系的领袖。
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增补景廉入枢,而宝鋆与沈桂芬走得较近。
光绪三年,李鸿藻丁忧,沈桂芬援引同是南人的王文韶进入军机处,南派势力大盛。
光绪五年,李鸿藻服阕后重新入枢,运用新近崛起的“清流”力量与南派抗衡。
光绪六年除夕(1881年2月17日)沈桂芬因病逝世后,军机处里李鸿藻的话语权大增。在当年,他被认为是理学家,但敢于引用“清流”打击政敌,也敢于拔擢“清流”做自己的班底,开一时风气。因为“清流”是以清正敢言、批评贪腐庸碌、主张对外强硬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彗星带来的“天意示儆”就成为一个好理由。七月十一日,陈宝琛补授翰林院侍讲。八月十七日,吴大澂补授太仆寺卿。八月二十八日,张佩纶补授翰林院侍讲。到了年底,还任命张之洞为山西巡抚,这些都是李鸿藻启用新人的安排。
张之洞26岁考中探花,其后宦途并不顺畅。当了十八年中下职位京官。但他受到李鸿藻信任,本年二月,授翰林院侍讲(从四品),六月一日,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不到半年竟外放疆圻,使得官场人士大跌眼镜。
李鸿章私下对前福建巡抚丁日昌说:“近日建言升官,大半李鸿藻汲引,亦可明其去取大端矣。”两江总督刘坤一对陕甘总督谭钟麟抱怨:“当今所谓清流,均系读书明理、知古今治乱者,何复如此标榜,如此排挤,以蹈前代覆辙?”而张佩纶也向吴大澂坦承:“李鸿藻秉政,颇采清议以为治,张之洞超迁内阁学士,阁下拜奉军,北极库仑,南至台湾,将吏亦颇得人。”
▍1882年彗星与李鸿章“夺情”复出
转眼一年过去,光绪八年八月十三日(1882年9月24日),彗星再次出现在北京上空。那天五更时分,僧格林沁的儿子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祜亲眼看到,有长星现于东南。次日拂晓,彗星再次划过东偏南的空域,“芒长一二丈,熊熊可畏”。二十日早上,翁同龢注意到彗星在东南,“行甚速,其光如长刀,头微弯”。二十一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说“妖星又见”。李鸿章复函也提到“妖星光芒甚炽,未知何祥,深为焦虑”。九月十五日,张佩纶又对李鸿章说:“十日来,妖星行次渐进,十一日并有流火彗孛飞流,层见叠出,恐非平静气象。”
八月二十四日,清廷再次为彗星出现颁布上谕:
上年彗星见于西北,降旨令内外臣工,各勤职守。本月中旬,彗星复见于东南,此必用人行政,时多阙失;闾阎疾苦,未尽上闻,以致昊苍屡次示警。深宫循省,兢惕难安。……尔在廷诸臣,各宜共效公忠,力戒因循积习。各直省督抚,均有察吏安民之责,务当实事求是、力图振作,属员中有不职者随时参办,毋得稍事姑容。并就各地方情形,悉心访察,认真筹度,以期利无不兴,弊无不除。朝廷考察督抚,惟视该省吏治民生以为殿最。其各力挽颓风,毋稍玩忽。庶几官方整肃,百姓乂安,迓天和而消沴厉,用副遇灾修省至意。

▲ 1882年10月17日大彗星掠过巴黎上空的情形
这个时期,清政府主要关注两大问题:对外是朝鲜“壬午兵变”和由此带来的对日外交,对内是云南报销案和由此引起的将王文韶革出军机处的角逐。
这年三月初二日,李鸿章母亲故世,李鸿章丁忧回籍奔丧。六月初九(7月23日),朝鲜汉城的士兵因为一年多未领到军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的反感,聚众哗变,大量市民也加入起义队伍。他们攻入王宫,杀死亲日大臣和日本人,推戴国王本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隐操朝政的闵妃在暴动时化装宫女逃走。起事者还焚毁日本公使馆,日使搭英舰逃离,回国率军舰返韩问罪,形势骤然紧张,史称“壬午兵变”。
“清流”中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张佩纶便借机为李策划“夺情”复出,以图拉拢掌握兵权的洋务大佬对付日本。他给李鸿藻写信说:“合肥(李鸿章)如此可出矣。”清廷命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兵迅赴朝鲜,并着李鸿章立即驰返。张树声派将领吴长庆、丁汝昌率水陆两军平定事变,出发前他们与朝鲜派在天津的使节金允植商量情况,金判断兵变可能是大院君李昰应策动,故吴、丁到朝后就设法将李昰应扣留,解送中国,安置于保定,以消除“麻烦制造者”。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回到天津,重归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清流”谋划对日作战
当时朝鲜刚刚对外打开锁闭的国门。国王李熙,有点类似光绪帝载湉,由旁支入承王位,先是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李昰应其实是亲华守旧而不谙世界格局变化的,被称作“事大党”。李熙亲政后,闵妃鼓励他采取开化政策并引入日本势力。闵妃及其外戚闵氏家族对朝政有很大操控权,与大院君形成对立。这个闵妃,后来在韩剧中称作“明成皇后”,但其生前从未被称过皇后。因为在清朝,藩属国君主的正妻只能称“妃”,没有“皇后”的称谓。
在处理“壬午兵变”时,朝鲜大臣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许赔款五十万日元,并派使谢罪。张佩纶对此不满,他要求李鸿章与日本交涉,修改条约,否则发起军事行动。
同时,另一位“清流”健将邓承修上《朝鲜乱党已平请乘机完结琉球案折》,建议派大臣驻扎烟台,厚集战舰,责日本光绪五年(1889)擅灭琉球之罪。张佩纶自己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治精兵,蓄斗舰,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又上《条陈朝鲜善后六事折》,称“星象主兵,请修德讲武,以应天文而靖藩服”。他说:
近者彗星柄在张度,芒指西南,九月甲午,流星陨于东北,……臣以理测之,彗端甚其锐,兵象也。流星如火,亦破军象也。随彗星所指而击之者胜,视流星所向而攻之者亦胜。吾之西南,则今越南也。吾之东北,则今日本也,东之西即西之东,吾之东北,日本之西南,则今朝鲜也。越南既有亡征,朝鲜亦萌乱象,二国之存亡治乱,系中外之强弱安危,是以上天重之,垂象以儆我。
李鸿章高度重视并花费很大心机,来经营同张佩纶—李鸿藻这条秘密政治渠道。不过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不理会张佩纶的招呼,上奏称中国海军实力难以作战。张佩纶随即去信,说你是以金革(打仗)为名复出的,现在若无金革之事,难道要把这个说法翻掉吗?
张佩纶还告诉李鸿章,其丁忧期间,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还保留着。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没有依缺递补,是李鸿藻“让贤逊位”,也是朝廷“笃旧褒功”,这是一份人情。李鸿藻大让无名,诸事从中调护,亦欲结平勃之欢以利国耳。你若以大故之后,凡事颓唐,西洋主和,东洋亦不主战,则人人能之。“一二知己于公善则扬之,过则隐之,恐天下之人爱公,远不尽如吾辈二三人。”
张佩纶前后连写五封密信,强调“朝鲜孱王耎国,恐有乱萌。来教以为过计,然天文家言,均以星指西南,日本实得高句丽之柄。鄙人不免杞忧,辄陈六事聊谢缄默之咎”。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上奏称“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张佩纶对此竟也无可奈何,军事行动无法推进。
▍彗星与“云南报销案”
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悄悄准备。
先是在七月二十三日,“清流”干将、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弹劾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财政支出,指控该省派出粮道崔尊彝、永昌知府潘英章到京活动,并汇兑银票、贿赂关说。朝廷派尚书麟书、潘祖荫查案。
八月二十四日,江西道御史洪良品又奏,称云南派人到京报销,户部官员索贿十三万两银子,因新任尚书阎敬铭马上就要到任,旋将贿额减至八万两,户部尚书景廉、侍郎王文韶均受贿巨万,余皆按股朋分。这样就将矛头指向中枢。王文韶是沈桂芬在浙江主持乡试时录取的门生,在湖南巡抚任上被沈调入北京,担任军机大臣,他的本职是户部左侍郎。
年初,户部汉尚书董恂被“清流”弹劾去职,由他署理,因此要对户部报销案承担责任。洪良品指出:景廉久历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种情弊。天变之兴,皆由人事之应。未有政事不阙于下而灾眚屡见于上者也。现在彗星复出东方,形如匹练,尾长数丈,直扫西南。日将出时,其光莹莹,几与争曜。臣虽不谙占验之术,然博观载籍,皆云政失于此,而后变见于彼。还说景、王皆枢垣重臣,以此二人管利权而舞弊如此,遂使天象警示不止,不是他们又是谁的过错呢?朝廷以此事关乎重臣名节,加派惇亲王奕誴和翁同龢确查。并专门颁布上谕,要求在廷诸臣和地方大员,以彗星再出为警惕。但户部报销案所涉关键人物潘英章、崔尊彝未曾到案,调查进展缓慢。
九月初一日,给事中邓承修上奏,谓景廉素称谨饬,王文韶赋性贪邪。现在王文韶枢柄未解,麟书、潘祖荫难以办案。请将其先行罢斥。奏上,无结果。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张佩纶连上三折一片,请求罢斥王文韶。张佩纶与王文韶是姻亲(张和王文韶儿子王庆祯是连襟,他们分别娶了前大理寺卿朱学勤的两个女儿),私下交往也很熟悉,但他认为:“报销案起,洪、邓两作,一戆一空,弹劾贵近岂能如此容易?调停了事,已费无限斡旋。……鄙人寂无一言,后世必有遗议,自处亦甚难也。”他还对李鸿藻说:“从来为小人者未有无才者,此公岂真有为国之心、为公之意哉?”经张佩纶强烈弹劾和王文韶本人多次陈情辞职,虽未查证到受贿证据(次年结案,亦排除景、王受贿的指控),太后仍批准王文韶开缺,回籍陪伴老母颐养天年。
从现有史料看,弹劾王文韶并非李鸿藻直接指使,但通过这场斗争,李鸿藻在军机处的对手被消除了。其后,在云南报销案引发的人事处分中,巡抚杜瑞联被免职,而张佩纶大力推荐,刚从四川建昌道擢升为云南布政使仅仅一年的唐炯,被任命为云南巡抚。这个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哥。“清流”在引荐自己人的时候从不手软,只是后来,唐在越南对法作战中大败而被革职,张佩纶也被追究了“滥保匪人”的责任。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回忆录中提道,某天王文韶前来拜访,请求解释他上朝时偶见一颗彗星陨落的凶兆,他因大祸临头而忧虑不安。丁韪良百般宽慰,也不能使他开怀,果然三天之后,他因涉嫌谋财欺诈而被告发,这更使他确信彗星预示了他的倒台。
▍“彗星已入紫微,光指北极”
在西方天文学传入之前,中国人很早就对彗星进行观测和记录。《春秋》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传》进一步解释:“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前者是世界公认的关于哈雷彗星的首次记录,后者则带有强烈的天人感应的天命观。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翁同龢在李鸿藻家听人说道:“彗星已入紫微,光指北极”,这同古人所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天象是一样的,恐怕这正是引起恐惧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为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若干颗恒星组合起来,一组称作一个星官。众星官之上,再划分中宫和二十八宿。中宫是北极附近的星空,又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其中紫微垣居于北天中央位置,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类似地上皇帝居住的紫禁城。除了天帝之外,皇后、太子、宫女也都在此居住。
从星图上可见,紫微星垣由紫微左垣和紫微右垣的十五颗星拱卫着,星垣里面,包括北极、勾陈、四辅、六甲、大理等星官。以北极五星最为尊贵。北极一星为太子、二星为天皇大帝、三星为庶子、四星为后宫、五星为天枢。勾陈为后宫,即大帝正妃,又主天子六军。四辅,是环抱北极的四星,是天帝之四邻。六甲,可分阴阳而配节候,故在天帝旁布政教、授农时。大理,在宫门内,主刑狱。这些名字,都是人间皇室和官府在天上的投射,按照古代星相学的观点,彗星出现在这样的核心区域,或预示将有重大动乱变故出现。

▲ 中国传统天象中的紫微星垣
所以翁同龢日记中提及彗星时,往往还伴随对其他天象的记录。比如他在光绪七年六月十三日写道:“钦天监连衔封奏。……闻司天言星出六甲(紫微垣内)。主水主刀兵,前奏谓主女主出政令。”十四日记,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来谈,“云同治年间两次彗入紫垣,不过大臣伏法(何桂清、胜保)。又云留则不可,穿则可。”十七日记:“彗星初二在八谷东,尾指上丞、少卫二星间,行黄道实沉、鸦首、二宫间。初三,其尾指勾陈大星。十二日,子正坐六甲,光过四辅,尾指勾陈二三星之间,光芒比前较减。十日三,仍坐六甲,尾正指勾陈第三星,长阔较初旬减三分之一。”等等。
更有趣的是,翁同龢在日记中亲手绘制了两幅插图。今年11月7日,上海图书馆举办《琼林济美——上海图书馆翁氏藏书与文物精品展》,我得以见到翁氏后人捐赠的《翁同龢日记》手稿,发现翁还用朱笔画出穿越四辅的彗星位置,并认真地记录了彗星的移动轨迹:
同文馆测彗星:二十一日亥初三刻,测得彗星斜出四辅二星之下,相去不足半度,其白气隐约至北极星旁,与勾陈明星若合成勾股形,彗星北极距为勾约三度半强,北极勾陈距为股约五度,勾陈彗星距为弦约六度馀,其尾正对勾陈三、四两星斜弧线之中。
是夜看仍长二三尺,似已入四辅,掩住左一星矣。闻同文馆云廿四日正掩北极第一天枢星。
《翁同龢日记》近年由翁同龢旅居美国的后人翁万戈先生捐赠上海图书馆。手稿中的星图,亲手抚之更可感受当年气息。注意此时正处慈安太后丧期,故日记本底框从通常的红色改成蓝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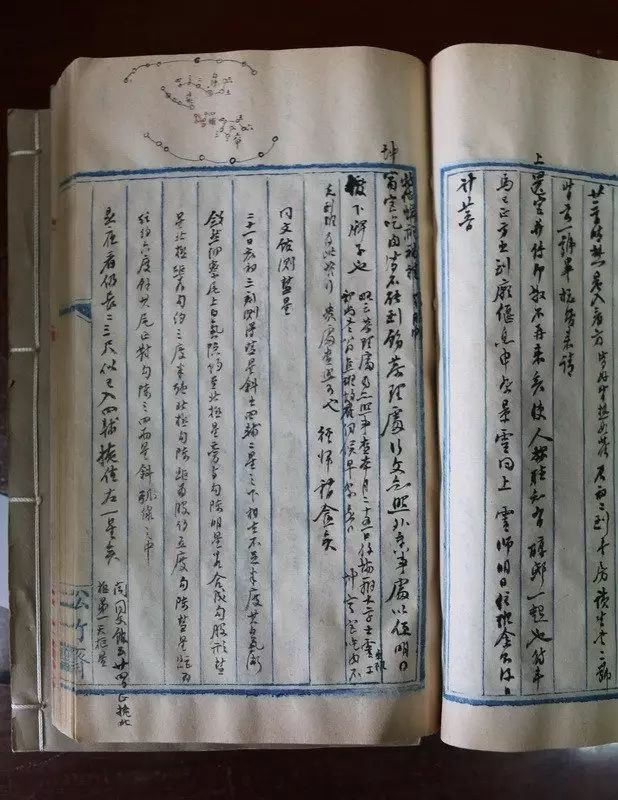
▲ 《翁同龢日记》

▲ 翁同龢手绘彗星进入紫微星垣中四辅星宫的情形,图中蓝字和绿字为笔者所加

▲ 翁同龢手绘彗星离开北极星宫的情形,红圈、蓝字和绿字为笔者所加
这段佶屈聱牙的文字是说,同文馆观测到红箭头所示意的彗星已闯过四辅二、三星之间,即将掩向四辅一星,并于六月二十四日掩住天枢星。我不懂星相学,但从星图来看,这是一个惊险的局面,似乎天上有闯宫者,已经突破层层保卫,在天帝居住的核心区域晃悠,无怪乎地上的人们要忧心忡忡。
七月初六日,翁同龢又记录:“测彗星距北极十度二十七分三十八杪,距大理八度五十六分。近因彗星距北极日远一日,故昨夜以远镜窥,其光尾甚为暗淡,其长约二度有奇,又测得现在彗星距地一万三千二百万里,距日二万二千二百万里,距日愈远则光尾愈暗,故后二三日彗星当不见也。”从第二幅插图看,彗星似受到顽强阻击,已经离开北极星宫,且渐行渐远。
▍西方天文学的彗星观察
古代西方的宇宙观,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其基本观点是“水晶球”体系,即以地球为中心的诸天体(包括月球、太阳、五大行星和众恒星)附着在各自所属的球层上,被携带着运转;这些球层由不生不灭、完全透明、坚不可入的物质构成;整个宇宙是有限而封闭的。月球轨道以上部分,是万古不变的神圣世界,只有“月下世界”,才是会腐朽的尘世。按这种理论,彗星、流星、新星爆发等天象,都只能是大气层中的现象。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彗星的元素是火。是大气中的燃烧现象。全体火元素,和大多数在它下面的气元素,都被旋转的天体带动着。同时,西方人也把各种灾害和不祥的事件与彗星相联系。古罗马人记载,恺撒遭暗杀当天,彗星活动频繁。在英国,黑死病的爆发与哈雷彗星到来有关。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通过研究1577年大彗星发现,它比月球遥远得多。彗星在行星际空间运行,毫不费力地穿越那些先前被认为“完全透明、坚不可入”的天球。这样使第谷明白,原来“水晶球”并不存在。
之后,天文学家和业余天文爱好者们不断地探索彗星的种种特性,笼罩在彗星身上的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609年指出彗星是一个天体,否定了以前关于彗星是空气散发的观点。人们陆陆续续观测发现了1600余颗大大小小的彗星,而这仅仅是庞大的彗星家族中的沧海一粟。随着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后来发现彗星循椭圆形轨道运行,牛顿的好友哈雷通过计算,成功预测了1758 年哈雷彗星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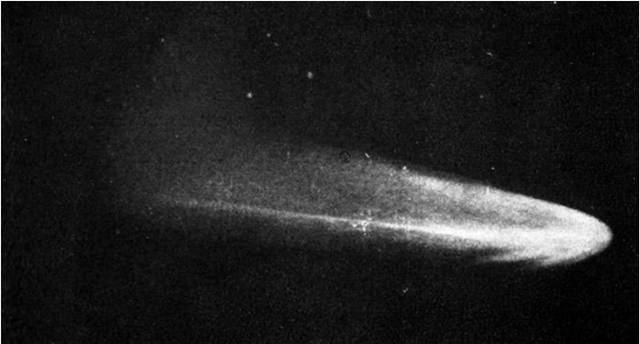
▲ 1881年,朱尔斯·詹森拍摄下了世界上第一张彗星的照片,使用干板底片,曝光30分钟
在西方天文学看来,光绪七年和八年出现的彗星其实是两颗。
前者称作“1881年大彗星”(编号C/1881 K1),1881年6月1日,天文学家特巴特(Tebbutt)首次观测到它的彗尾。11日,在南半球首见彗星。22日,在北半球观测到彗星。朱尔斯·詹森(Jules Janssen)使用干版底片,第一次拍下彗星的照片。后者称作“1882年大彗星”(编号C/1882 R1),1882年9月1日清晨,南半球的好望角与几内亚湾有多人独立观测到它。第一位发现1882年大彗星的天文学家是开普敦皇家天文台的芬利(William Henry Finlay),他在9月7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 时观测到,并测得彗星的视星等为3等,有1度长的彗尾。这些观测,都比中国人看到得更早些。
1882年大彗星9月17日通过近日点, 距离太阳表面仅30万公里。德国天文学家克鲁兹(Heinrich Kreutz)研究后提出,这颗彗星是一颗更大彗星的一部分,它在先前通过近日点时分裂了。目前天文学界认可1882年大彗星是1106年大彗星(即在宋徽宗崇宁五年出现过)的碎片,它和其他一些彗星都是克鲁兹族彗星的一部分。公转周期是772 ± 3年。
由于彗星本身的光芒较弱,只有运行到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才有可能被观测到。而恒星距离太阳系都十分遥远,远到以光年计算。进入近日点的彗星在这些恒星间的穿越其实只是视觉上的重合,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各种星宫,本来就是人类对遥远天体编造出来的童话,并且中国和西方对于星宫星座的组合与命名还各不相同,彗星会带来地球上的灾难和人事变迁,其实都是无稽之谈。
近代彗星知识 19世纪中后期较为广泛地传入中国,如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A. P. Happer)所著《天文问答》(1849)、英国传教士合信(B.Hobson)所著《天文略论》(1849)、美国教习赫士(W. M. Hayes)编译《天文揭要》(1849)、英国人伟烈亚力(A. Wylie)与李善兰合译《谈天》(1859)等。这些著作,有的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有助于开拓普通民众眼界;有的则是专业性相对较强的天文学家著作,最有代表性是《谈天》,该书供有一定天文或数理基础的人阅读,激发感兴趣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天文知识。
此外,光绪七年彗星出现后,六月初六(1881年7月1日)的《申报》头版发表《彗星论》,指出“彗星绕日旋行,迟速不一。有三年一次者,有五年一次者,有七十五六年一次者,有数百年一次者,亦有仅见一次,而不复再见者。因其轨道有长短,故其来去有迟速也”。对于灾异和天人感应,作者认为“中国历代相沿卒不以为非者,正以天象以为修省之道”。“彗星本不足异,而人君不可不以此为恐惧修省之道。”巧妙地将传播科学知识和中国统治者加强自我修省结合起来。光绪八年彗星出现后,《万国公报》发表了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Parker)的连载文章《彗星》,进行科学扫盲。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于彗星的了解,已经进入了两种话语体系。

▲ 1881年7月1日上海《申报》发表的《彗星论》
▍天象与政治斗争
最后我自己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是清廷钦天监和总理衙门办的京师同文馆已经掌握一定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工具(天文望远镜),其对彗星的表述与传统星相学说是怎样的关系?从现有史料看来,显然还是中学为体,天文仪器的观察是为古老迷信服务的。但同文馆诸多洋教习内部的看法是什么?
二是中国官员,尤其“清流”干将,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否真的相信天人感应这套理论?这点我缺乏完整的资料,但是我读到过张之洞写给张佩纶的一封信:
适间露坐,偶一仰观,彗星已掩四辅,犯北极,指勾陈第一第二星之间,光气尚长尺余。鄙人素不信占候,安得天下人尽如鄙人坚持天远人迩之说,力扫术士陋谈乎?台官如晓事,不以此摇惑人心则善矣。
从函中看出,此时星相正是翁同龢画下的场景,而张之洞本人,其实并不相信彗星引起灾变的说法。只是“清流”们仍以此为理由,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令人感慨不已。

▲ 作者在查阅《翁同龢日记》手稿时,与翁氏后人翁以钧先生(左二)的合影
【作者简介】
姜明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