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龍昇
读腾讯·大家上俞天任先生的《支那通,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怪物》(原题《“支那通”以及“支那通”思维》)文,见其文述说的“支那通”是“昭和历史书经常出现的名词”,指的“是当时陆军中的一个群体”。
不说读后感,却说读后脑中浮出了另一类“支那通”:一批日本大正时代和昭和初期活跃于中国的文化单位和文化人。对比那一个陆军群体,他们是一个体制外的文化和文化人群体,比如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日本堂书店、报刊《上海日日新闻》等,比如曾居上海、南京、苏州多年的文化人井上红梅,引出上海别称、写下小说《魔都》的松村梢风,曾数十次旅行中国、写下《支那风俗之话》等大量中国风物志的语言学者后藤朝太郎等。
想说说的井上红梅,有很多头衔,其一就是“支那通”。 俞天任先生原题中的支那通是加了引号的,非常理解。说井上红梅也免不了出现“支那通”或”“支那”之词,我干脆在文题中用“中国通”吧。
▍一
他悄悄而来,不善经商,由文青变成了中国通。
井上红梅的生卒之年,公式说法是1881年—1949年,但没有具体的生卒月日。只知他的生父是贸易商,未知姓名。只知他幼年丧父,先由祖母领养,后在七岁时过继给了设在东京银座尾张町开设“井上商店”的店主井上安兵卫当养子,取名井上进。此后的他才有了较清晰的人生轨迹。就是说,幼年少年的井上红梅形象很模糊,给人悄悄而来之感。
井上红梅的较清晰的人生轨迹的出现,除去极少的自己记载,更多地可从宫田芳三、寺田寅彦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和记载中找到。宫田芳三,也是1881年生,十三岁时进“井上商店”当店员,后来边工作边读早稻田大学的讲义,经校外考试,取得了毕业资格。
“井上商店”经营纺织品、绷带材料、医疗器械和杂货,面对的主要客户是军方,宫田芳三发明了一种“伸缩绷带”的制作方法,成品被军方大量采用为医用绷带和绑腿,他的发明为商店带来利益,得到店主井上安兵卫的器用。作为养子,井上红梅被井上安兵卫送进商业学校读书,这红梅却因病中途退学了,原来他志不在商而愿当文青。

▲ 井上红梅画像
因以上原因,义父废了他的名分,改认宫田芳三为义子。却说宫田芳三比井上红梅更文青,他早井上一年就在青年文艺杂志上投稿发文,且比用了笔名的井上红梅著文多、文采高,因此了解青年时代的井上红梅可从宫田芳三的人生轨迹中打捞一些。
寺田寅彦,是很有名气的物理学家、随笔家、俳人,他读东京帝国大学时曾寄宿在“井上商店”,成名后也常来店作访。那时的井上红梅正由少年转入青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交集,因此井上之名和事情会在寺田的日记和记事中出现。
1911年,“井上商店”店主去世,井上红梅将商店的经营权和债权让渡给了宫田芳三。1912年,改姓为井上的宫田芳三正式袭名井上安兵卫第二代。其间,井上红梅曾开过中华料理店,也因不是经商的料而破产。1913年,三十二岁的井上红梅囊中羞涩地到中国放浪去了,一去多年,他由文青变成了“支那通”,完成了自着、合著的近三十部的等身着作中的大多半。
▍二
他多年在上海、南京、苏州居住,以亲临、亲见、亲感而成了中国通。
境况窘困的井上红梅先在上海、香港、台湾漂泊了一年多后,于1915年,在日文版的《上海日日新闻》谋到一个记者之职,才选上海定居下来,先住福州路后居淡水路。住了一段时间,除去一般报道文章,他更深入到对中国风俗的观察研究,他在淡水路的住房里创办了只有一人的“支那风俗研究会”和只有他一个人著文的日本语杂志《支那风俗》。
1918年起,上海日本堂书店,将他积三年观察研究出的报道文章结集,出版了上中下三部头的《支那风俗》,内容大部分涉及到中国的“吃喝嫖赌戏”——吃(菜肴)、喝(酒)、嫖(女人)、赌(赌博)、戏(戏剧)。笔者曾从福冈县立图书馆借阅到《支那风俗》的复写版,看到书中除去作者自序里提到的那“五大道乐”外,还有对中国南方服装服饰、方言、茶道、迷信、街头叫卖声等记录描述。

▲ 上海日本堂发行的《支那风俗》
1921年,在发表了《支那女研究香艳录》之后,井上红梅移步南京,抱着“想进中国家庭过中国人样的生活看看”的想法,经人介绍,与一个苏州籍的带着拖油瓶的小寡妇毕碧梅过了三年结婚生活,那段生活终因供不起碧梅的吸食鸦片的费用(也包括自己的沉湎于酒)而结束,他又移居到了苏州。
不过在那三年内,井上红梅又完成了研究土匪内幕的《土匪》、记录中国农村红白喜事节假庆典的《支那各地风俗丛谈》、翻译了三部头的《金瓶梅》(《金瓶梅与支那的社会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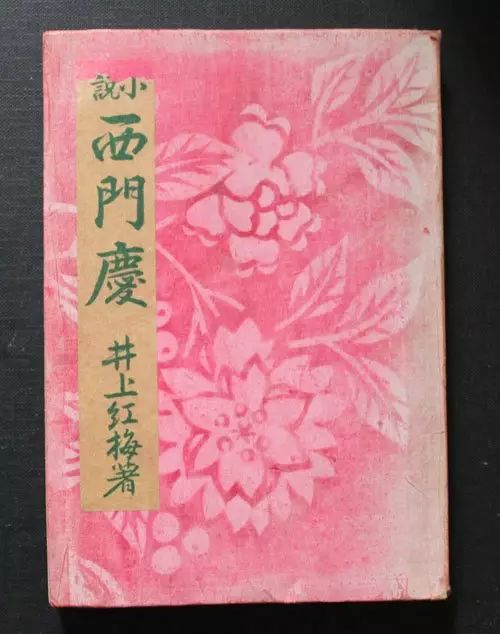
▲ 1941年弘文社版《西门庆》
1924年10月5日,上海日本堂书店发行了井上红梅的《支那ニ浸ル人》(《沉浸于中国的人》),书的自序写于“苏州寓居”。
笔者曾在福冈市立图书馆借阅到只供馆内阅读的《支那ニ浸ル人》原版书,見书中收录了井上红梅移居苏州之前三年写的关于南京的六个小集子:秦汇画舫录、四象桥日记、荤素杂志、俚谣管见、金陵的鸟、家和塔和桥。
前三集写的夫子庙和秦淮风月、旅店琐事,以及其与苏州籍小寡妇毕碧梅的被介绍及至成亲的故事。后三集则增写了丝竹之音、江南小曲(从胡琴、锣鼓到南京歌、泗洲调、到《孟姜女》、《打牙牌》、《十八摸》)……南京的鸟——莺、鹊、鸦、鸽、八哥、百灵、布谷鸟……江南民居庙宇建筑特色、水乡的桥与塔……
此后的他,写了不少关于中国风俗的文章,还于1930年出版了成部头的《酒、阿片、麻雀》(《酒、鸦片、麻将》)。
▍三
他确实是中国通,可通得很另类。
井上红梅是头冠“中国民俗研究家”的“支那通”。他在《支那風俗》中有不少关于牌九、骨牌、马吊、麻将的记载,他还写了单行本《家庭游戯 麻雀の取り方》,介绍了麻将的打法、术语、规矩,因而被评为日本的“麻将普及之祖”。 他在《支那风俗》中描述的戏(戏剧),包括了京剧,对京剧的对外介绍和传播有着一定的文化意义。他还研究了说书和评弹、详尽地用日文记录下《珍珠塔》。井上红梅不仅耳熏目染、甚至娶中国女人为妻过中国人日子地了解、记录中国民俗,以至能熟练地使用南方女人的嗔骂“吃侬记耳光”。
和井上红梅同时代居于中国的日本文化人和访问游历过中国的日本文豪们,也写过鸦片、麻将和女人,但他们更多地写过其它的中国风俗民俗山川景致。井上红梅虽也写过丝竹音乐戏剧小曲,但他更沉湎于书写酒、鸦片、麻将,以至写得精致细腻、绘声绘色、淋漓尽至。这使得他在同一类文化人“支那通”中显得更另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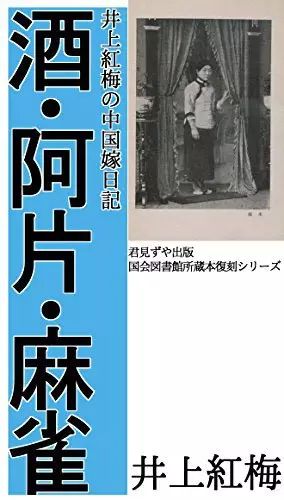
▲ 再版的《酒、阿片、麻雀》
井上红梅“苏州寓居”一年后回到了上海,是因受聘于为《日刊支那事情》的文艺栏记者,在那栏目中介绍《今古奇观》《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中国白话小说古典文学。也因此,他将情趣从“支那风俗”转向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得到中国文学翻译家的头衔。
同时的井上红梅,也转向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翻译,着眼点是鲁迅,后果很严重。
▍四
他是最早翻译鲁迅作品的日本人,但鲁迅对其人及其译著均不满意。
最早将鲁迅作品翻译成日文的人是鲁迅自己和其弟周作人,而最早将鲁迅作品翻译成日文的日本人可以追朔到井上红梅。早在1926年,井上红梅便翻译了小说《狂人日记》,却在投刊杂志过程中石沉大海。1928年,他译的《阿Q正传》终于在《上海日日新闻》上刊载,同年还刊载了他译的《社戏》。1932年,东京改造社出版了他译的《鲁迅全集》,内收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的全作品。
同期着眼并参与翻译鲁迅作品的日本文人作家研究者有好几位,比如倾心于中国文学的佐藤春夫、因亲来上海聆听《中国小说史略》讲义而成了鲁迅爱弟子的增田涉。但是,无论对鲁迅单篇小说的翻译还是合集作品的翻译,井上红梅都比他们早了一步。
鲁迅与井上红梅有过交集,也对他最初的翻译作品做过指导。但看到井上改造社版《鲁迅全集》后,他表示了不快感:“井上红梅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近来看到他的大作《酒、鸦片、麻将》更令人慨叹。”(见1932、11、7鲁迅致增田涉书简)、“下午收井上红梅所译《鲁迅全集》一册,略一翻阅,误译甚多。”(1932、12、14鲁迅日记)、“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他似未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我觉得那种做法,实在太荒唐了。”(见1932、12、19鲁迅致增田涉书简)

▲ 井上红梅参与的《大鲁迅全集》
看得出“他和我并不同道”的意思,对中国旧习俗和风俗嫉恶如仇的鲁迅,当然与写了《酒、鸦片、麻将》的井上是两条道上的人;看得出“我也感到意外”,是“概叹”译出改造社版的《鲁迅全集》和写了《酒、鸦片、麻将》的竟是同一个人;看得出“更令人概叹”的是慨叹手把手地指导翻译本人作品的爱弟子增田涉,怎么被井上抢了头功。
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看出早于增田涉和佐藤春夫许久翻译鲁迅作品的井上红梅,怎么会“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总之,也许是投机、但并无恶意地翻译了鲁迅作品的井上红梅,被鲁迅的“实在太荒唐了”一剑封喉了。
鲁迅于1936年逝世,次年,日本东京创作社便出版了七卷精装的《大鲁迅全集》,参加各卷的译者有井上红梅、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山上正义、鹿地亘、山田岳夫等人,编辑顾问是茅盾、许景宋(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佐藤春夫。它比中国最早的《鲁迅全集》的问世早了一年。
▍五
他回日本后没华丽转身成功,最后悄悄地走了。
井上红梅好像在1929年与1930年交接时回到日本,先住了一段日子,改造社版的《鲁迅全集》便是出版于那时。之后,又以报道记者身份去过中国,而在1933年与1934年交接时回日本,此后,再未去中国。有记载说他住在东京本乡一栋简陋的排房里,好像去中国时囊中羞涩,从中国回来时亦囊中羞涩。
归国后的他仍坚持对中国书籍的翻译,除去1937年参与了《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同年他还与武田泰淳合作,将1936年陈赓雅写的《西北视察记》,翻译成了《支那边疆视察记》。1938年出版了与《支那风俗》内容相似的《中华万华镜》。1941年,弘文社出版了他以《金瓶梅》改版的《西门庆》,1942年,清水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古今奇观》,1947年他译的《西门庆》被柳泽书店再版。其中值得一赞的是他译的《今古奇观》,从二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东京,花费了近二十年心血。

▲ 1947年柳泽书店版《西门庆》
纵观井上红梅的写作史,除去步入青年时发表的十几篇幼稚之作、做记者时的报道的《上海骚扰记》《上海蓝衣社的恐怖事件》《萧(伯纳)与孙文未亡人》《关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等记事、和临终前在日本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俳句,他倾半生之力记录描述了中国风俗、翻译了中国的古典白话小说和近代的鲁迅作品。尽管他如此努力,但由于日本战后对“支那通”冷眼相视等原因,他未能华丽转身为一流作家。
尽管他对中国风俗的选项挺另类,但他的《支那风俗》曾被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大家欣赏并当作了对中国旅行的指南,他对麻将的介绍普及了日本的娱乐文化。尽管他对鲁迅作品的翻译“误译甚多”,但今日研究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总绕不开他。
井上红梅1949年的卒年是推断出来的,那年躺在医院病床的他给报刊投稿了一首俳句。此后,音信皆无,没有讣告不见葬礼,如同他的悄悄而来,他又悄而去。
【作者简介】
龍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出版过长篇小说《血色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