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招待所仅存在了大半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几位写诗的年轻人为了减少生存成本,租住在同一个地方,在生活上有所照顾。它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氛围,激发着住在那里的人——从语言到认识,他们每天所关注的就是诗。

火星招待所(上)
文 | 李纯
一
2002年,在老家过完春节的一个月后,张羞买了一张L开头的火车票,这是春运期间额外加上的临时客车,速度比普通的列车慢。从杭州到北京,开了一天一夜,总共停靠50多站。他第一次去北京,没有什么好奇,仅仅觉得那里是个文艺青年爱扎进去的地方。当列车在天津下客,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犹豫要不要回去。
下午五点钟,列车停靠北京站。那是三月份,北方的落叶植物还没有长开,空气里夹杂着粉尘,灰蒙蒙的。这个来自南方的男孩,有点不适应北方的气候,他穿一件衬衫,衬衫外面是卫衣,卫衣外面套了一件薄棉袄。他拿着一本兰波的诗集,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等吴又过来,带他去火星招待所。
张羞出生在浙江嵊县一个雨水充沛的农村里。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长他十五岁,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10岁那年,他的家庭遭遇了一次变故,他的姐姐被山洪冲走了。
那天,他的哥哥和嫂子带张羞的姐姐去镇上走亲戚。他们喝了酒,开拖拉机的司机师傅也喝得醉醺醺。晚上10点钟,他们走山路回家,经过一座桥。河水涨潮,已经漫过桥身一米高,司机继续往桥上开,开了不足10米,车身翻滚,掉进河里。
哥哥和嫂子被岸边小卖部的老板看到,救了上来。拖拉机司机被压在拖拉机下面,死了。姐姐年纪太小,被洪水冲走,隔了两天才被捞上岸,尸体已经腐烂变绿。
对于这件事,张羞记得的画面很少。他尚年幼,意识不到死亡是什么。他只记得,他的妈妈哭得很伤心,记得出殡前,存放尸体的棺材摆在村子口等待合适的下葬日期,然后是守灵,他拿着姐姐的画像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有种新奇的感觉。他说:“你觉得这很好玩,它没有悲伤,因为你不知道悲伤,悲伤这个词都没听过。一个人有自我伤感是很晚的。”
或许是这个原因,张羞的哥哥在此后一直对他极尽可能地照顾。而当他长到一个懂得悲伤的年纪,他反复地想起这件事,想起这个人,越到后来,记忆越强烈。他说,这件事构成了他对人生的一个基本态度,他对生命的理解,他不喜欢生命的形式——从出生到死亡。以至于当他用这种态度去理解生活中的日常,他发现所有的事情变得非常无聊。“一个到世上散步的人。”他在一篇小说里这样写自己。
这个过早对生命产生厌倦的男孩,等他进入大学,他多少与周围的人有点不一样。1997年,他考进浙江工业大学。他本来打算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他的哥哥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哥哥希望张羞和他走同样的路。但张羞的高考成绩差了4分,没有考上。
大学期间,张羞的专业是通信工程,他本应该是个写代码的程序员,他对此没有一点兴趣。他的哥哥从日本带给他一只索尼的Walkman。他买了两盒磁带,一盒是陈百强,另一盒是崔健。他先听崔健,觉得《一无所有》还行,其他的歌很聒噪,不喜欢,陈百强的旋律顺,倒是喜欢听。但很快,他接触到Grunge,听涅槃乐队。1994年,27岁的科特·柯本在西雅图的家里饮弹自尽,他的死是摇滚文化的一个象征,人们喜欢把他的死看做一个纯粹的灵魂被工业侵犯之后的自我毁灭,而他的行为在他死后被不断模仿。张羞像找到组织一样地模仿柯本,比如,永远穿牛仔裤,匡威鞋,学习抽烟,看兰波的诗。大三时,他试过把头发全部剃光。他一下子觉得崔健特别好听,“瞬间就转过来了,你就把自己和其他人划分开来,不是生活上,而是追求和认识上。我是这一类人,你们是普通人。”
西方60年代的摇滚乐和诗歌占满了他的脑袋和生活。90年代末,网吧开始在城市出现。1998年,杭州还没有网吧,到1999年,有一两家。随后一年,网吧在城市、尤其是学校周边铺开,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网络论坛。1999年,高地音乐、暗地病孩子等几个亚文化的网络论坛出现,类似QQ的即时通信刚刚开始流行。张羞混迹于一些亚文化论坛,以及杭州的地下摇滚演出场所。那时候,他的偶像是诗人兼歌手杰姆·莫里森和法国诗人兰波,而在国内,他心里的类似人物是竖,一位上海的诗人。竖曾在暗地病孩子发过一首叫《长途车》的诗,描述了一个少年经历的孤单旅途。张羞读完以后感动地哭了,他开始写诗,想成为一名诗人。
2001年大学毕业,他在杭州找了一份工作,上班三个月之后,他上不下去,辞职打算往外地走。他打给在暗地病孩子上认识的吴又。吴又当时不叫吴又,叫子弹,有时前面加一个修饰语,变成“抛弃枪的子弹”,他写诗也写小说。张羞问他,子弹,离职之后该去哪儿混?成都怎么样?吴又说,你去成都干什么,到北京来,我已经和一群诗人住在火星招待所里了。

2003年,张羞在北京香山。
二
竖1972年出生在上海,年纪比吴又和张羞长7岁。三个人里边,竖写诗最早,熟悉他的诗人比较多。他身高一米八,四肢修长而瘦削,看上去郁郁寡欢,一旦喝起酒,行为变得桀骜,年轻的爱好诗歌的女孩们或多或少对他抱有爱慕。
竖第一次去北京是1994年。那一年,“魔岩三杰”刚刚发行新专辑,在全中国的摇滚青年里面产生很大的震撼,很多人被他们的态度和方式所影响。竖热爱音乐,他听了张楚《姐姐》想:“北京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容纳我这样的人,至少有人从那里出来。”他认识一个玩音乐的朋友在人民大学读书,他决定去北京找他。
那年初夏,离大学毕业还有一个月,竖决定辍学,去北京实现摇滚梦。他的叔叔是虹桥机场的处长,主动给竖在机场内部刊物安排了一份工作,一个月有六七千块钱。他知道竖喜欢文学。他像受了屈辱一般,拒绝了家人眼里的“金饭碗”,他对父亲说:“我要去北京。”父亲正在削铅笔,他没说话,把一支铅笔从十几厘米长削到大拇指那么短,竖说:“我没有钱,你们要给我路费。”他母亲觉得他的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早知道就不供你念大学了。”铅笔削完,父亲递给竖600元:“不管怎么样,别逞能,能回来就回来。”
在人大,竖认识了一个女孩,俩人陷入爱河。竖在配餐公司找了一份做盒饭切配的工作,同时等机会组乐队。他喜欢朋克,喜欢态度张扬的音乐,当时北京的校园最流行的是民谣,是老狼、沈庆和丁薇这样的人物,他找不到同类,乐队的事迟迟没有着落。他只好一边做盒饭,一边写一些不知道是歌词还是诗的东西发在网上。他到处投稿,写信给《十月》、《收获》,有一次投给一份叫《作品与争鸣》的文学刊物——他笃定自己的作品肯定会引起争鸣,他也写过信给张楚和陈升,这些信像投入汪洋的石子,杳无音讯。在北京待了一年,他的女朋友大学毕业,去海南工作,竖则回到上海,做起了卖打口带的生意。
在上海的四五年,竖像一只不安分的蚂蚁,从一个地方爬到另一个地方。他摆过CD摊,开过音像店,组过朋克乐队,去机场做过撕票员,在网络公司做设计,最后一份工作是运货,把铝制管道从上海运到其他城市。2001年,诗人杨黎从成都到了北京,他是竖的诗歌前辈,他打电话给竖:“我已经到北京了,过来吧,这里有很多朋友。”竖有点犹豫,杨黎说:“我帮你找工作。”到北京没多久,竖住进了火星招待所。

在通州杨庄,左起竖和另外两位诗人裴飞、蝈蝈。
搬进火星招待所之后,竖把另一个诗人吴又也叫了过来。吴又刚刚从武汉的大学毕业,在国贸上班。他成长在湖北荆州的一个县城,小时候他感冒患肺炎,病重到几乎断气,他的父亲求一位和尚给他做法,同时给他取名“吴法”,他活了下来。或许是名字的关系,从初中开始,吴又在学校就很调皮,南方的小镇充斥着古惑仔式的暴力,小镇里的少年喜欢混帮派,吴又是其中的一份子。他旷课,喜欢打架,台球和打牌。和周围人有点不一样的是,他很早开始写诗,对诗有天然的敏感。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按照家里的想法,去家乡的电力系统上班。他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武汉,除了吃烧烤,没什么留恋。他想去北京。他在求职网上发了几封简历,很快收到面试通知。第一家公司是后来的卓越网,正处于初创期,在一栋简易的居民楼里办公;第二家公司是赛特集团,在国贸一栋写字楼里,他觉得赛特的位置好,就选择了后者,做网络维护的工作,平常大厦的网络很稳定,工作没太多事。刚去北京那会,他叫一个北京的没见过的网友在奥森公园附近租了一间平房,房外有一条很凶的狗。有一天竖到吴又住的地方,把他的行李收拾一番,拎到了火星招待所。
在火星招待所,吴又展示出帮派青年所持有的仗义风范。那时赛特的待遇好,毕业生一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多的时候上万,他把钱算了算,对住在里面的其他诗人说:“你们别工作,我算了一下我们几个人开销,张羞还有一点从他哥哥那里拿来的钱,够了。”他说:“我养你们。”竖听完,觉得吴又特别牛逼。
三
火星招待所是一间屋子,也是一个团体和一种氛围。它在北京,是一间90平米的出租房,在通州杨庄一栋七八十年代建的六层楼房里。房子是单位公房,小区外有一道铁门,有门卫看守,晚上门卫会把铁门锁上。住在火星招待所的诗人要是在外边喝酒回来晚了,得翻进去,其中一位诗人有一次翻门不小心把新买的牛仔裤刮破了。
住进火星招待所的第一位诗人是张稀稀,黑龙江鹤岗人。2000年,张稀稀大学毕业,他和张艺,一个搞音乐的男孩,在杨庄租下这间房子。月租1500元。几个月之后,张稀稀的两位大学同学,蝈蝈和裴飞到北京谋生,也住在这里。不久,竖、吴又和张羞陆续抵达北京,他们也搬进了火星招待所。
起先是张稀稀盖的一床被子。这床来历不明的军绿色被子上面绣了五个字,“火星招待所”。后来它成了这间屋子的名字。火星招待所像一个沙龙,外地诗人到北京,首先会到这里做客。喝酒夜不归宿的情况是个常态。周末,住在市区的其他诗人也会过来待两天,久而久之,他们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招待所。

诗人们在通州杨庄。左起:张稀稀,池塘,裴飞,张艺,张艺女友,竖。
火星招待所装潢简单,空间开阔,最多曾容纳过十六七人。平常,小卧室睡一个人,大卧室有一个类似炕一样的大床,如果并排横着睡,可以睡四五个人。客厅的沙发到了晚上,也是一张舒服的床。
严格意义上,火星招待所仅存在了大半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除了吴又一直有稳定的工作,其他诗人差不多处于闲置状态。他们依靠家人、朋友和临时的工作机会维持生计。每个周末的夜晚,这里举办聚会。他们在论坛发表诗歌,线下聊天喝酒,接待新加入的诗人。
火星招待所代表了某种少见的生活方式,几位写诗的年轻人为了减少生存成本,租住在同一个地方,在生活上有所照顾,实际上没有它的名字听上去那么浪漫。但它确实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氛围,激发着住在那里的人——集体生活催化了他们的写作,从语言到认识,他们每天所关注的就是诗。
火星招待所的诗人都在一个叫橡皮的诗歌论坛上发表作品,这个论坛属于橡皮先锋文学网站,由“第三代”诗人杨黎、韩东、何小竹在成都创办。
后来,竖搞了一个论坛,类似橡皮的子论坛,他们称它“火星招待所”。打开论坛,网页是朱红色,配红褐底色,页眉有一个半开玩笑式的logo——一个胖乎乎的小人张开双手。这个小人要是细看,长得很像杨黎。2001年,杨黎还是个胖子,而现在他几乎瘦了一半。和火星招待所里的诗人一样,他刚从成都迁居到北京。他曾经是成都”非非“诗派的代表之一,后系统地提出“废话”写作。诗人间曾经流传,80年代的成都,一个招牌砸下来,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诗人。90年代“非非”集体下海,他跑过销售,开过广告公司,甚至开过夜总会。在北京,他喜欢把这些初涉诗坛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在他们之间,他树立了一种简单又抽象的诗歌风格。无论在诗还是在生活中,他同样具有感染力。

论坛“火星招待所”的logo。
四
张羞起初不怎么喜欢待在火星招待所,换句话说,他住进火星招待所是生活所迫。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去三元桥附近的人才市场找工作,无功而返。他没有什么经济能力,除了写诗,似乎没有更擅长的事情了。
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一天早上,房东突然开门进来,看见十几个诗人躺在地上,处在宿醉状态,而且有男有女。房东是个中年模样的北京女人,她生气地喊道:“你们在搞什么?赶紧给我搬走,我不租给你们了。”
他们在杨庄附近找了一间平房,时间仓促,他们匆匆看了一眼就付了租金。往外搬东西的时候,楼梯口坐了一男一女,姿势奇怪,女孩伏在男孩的膝盖上,样子似乎在哭,但没有哭的声音。他们问:“你们是住在这里的吗?”这对男女没有说话。他们又说:“那你们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坐一会。” 依旧没有说话。他们继续往外搬。
晚上,他们住进了新租的平房。打开电灯,他们才仔细打量这间房子。它很空,除了一张大通铺,几乎没有家具,有点像公路边的廉价旅店。他们怀疑这里原来是一家卖烤串的店,因为墙上有零星的血迹。南边是一扇大飘窗,从窗户望出去,是一片荒凉的空地,再远,是铁轨,偶尔有火车开过。他们并排躺在床上,提起白天那对男女,竖说:“你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是活人吗?” 一开始以为是开玩笑,顺着话题,他们聊起了生平遭遇过的灵异故事。聊着聊着,竖说:“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东西特别奇怪,你们看这个地方肯定杀死过很多动物,因为墙上都是血,那不可能是活人的血吧?” 他继续问:“大家相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是存在的,还是有魂魄的?”
聊到这儿,他们很害怕,但没有停止说话。房间里出现了一种细思极恐的气氛,夜已经深了,墙壁上的血迹在灯光底下越发地醒目。像鬼片里的老套手法,有一盏灯突然熄灭了。他们全都吓坏了,烟盒快空了,没有人敢出门买,甚至没有人敢上厕所。他们僵在床上,好像屋子里面全是鬼。
吴又22岁,年纪很小,却是几个人里边最镇定的一个。他说:“大家不要这样,” 他走到院子里,对着空气吼道,“有鬼吗?出来和我聊聊。”接着,他点燃一支烟,在院子里站了一会,似乎在等候回应。几分钟后,他回到房间,告诉屋里的人:“没鬼。”
黑暗中,张羞对着天花板哭了。他感到低落,不知道耗在这个地方,像僵尸一样躺在床上有什么意义。他写诗,但诗歌尚未给他的生活带来足够的慰藉,他身边的朋友也是。他刚来北京一个礼拜,已经有些待不住了。他去人才市场投简历,如泥牛入海,没有回应。他带了700块钱,以为能挨一个月,去了之后请哥们吃饭,一两天就花光了。他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生活。”
在杨庄的平房住了一两个月之后,一部分诗人觉得这样的集体生活难以为继。张稀稀,裴飞和蝈蝈各自找了地方住。剩下竖,吴又和张羞,他们搬到通州九棵树,合租一间两居室。火星招待所在杨庄的集体生活结束,九棵树的集体生活开始。
五
暗地病孩子的英文名是“ sick baby”,网站的创办人“sickee”,现在是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叫童玮亮。这个论坛很受一些个性怪异的年轻人欢迎,比起学院派,他们更亲近卡夫卡式的另类表达,在那里活动的包括后来的作家安妮宝贝和路内。在“橡皮”没出现之前,竖,张羞、吴又等一些诗人经常在上面发些东西。
2000年,网络已经普及。除了类似暗地病孩子、高地音乐这样的亚文化论坛,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诗歌而设的论坛,比如广州的“诗生活”和北京的“诗江湖”。二者都不太对他们的口味:诗生活属于学院派,上面的诗文本感浓厚,像欧美翻译过来的桂冠诗人;诗江湖的是”下半身”诗派的主要阵地,以沈浩波,尹丽川,南人等为代表,主打身体写作,态度激进。
那会,竖一边在上海的一家信息公司做网页设计,一边在网上发表诗歌。有一天,博库网内容总编黄集伟找到竖,给他一万元稿费,买他的诗。那是互联网的春天,很多热钱涌入,博库网想用这些钱鼓励活跃于网络的独立写作者,当时,拿到钱的还有作家狗子和诗人尹丽川。
竖把1994年到1999年写的诗,一股脑地发给黄集伟。他从没想过,这些发在论坛的不知道是诗还是歌词的东西,能给他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他高兴坏了,立马辞掉工作,打算去流浪。
他首先告诉乌青。乌青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诗歌青年,也是当时的年轻人中比较早有意识地与“第三代”接轨的诗人。他出生在浙江省一个叫玉环的小岛,是中国最临近钓鱼岛的地方。地理环境使这个地方具备了浪漫的海岛风情。乌青读的高中临海而建,下课后,可以走路到海边坐坐。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没有让他感受到快乐,相反,他急切地想摆脱小岛生活的封闭状态,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从童年时期开始,他有过四次离家出走的经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发生在高三。这次,他走得比较远,到了西安。他爬上大雁塔,站在七层高的塔楼,他念了一首《有关大雁塔》。
《有关大雁塔》写于1983年,作者是诗人韩东。80年代,以南京的“他们”,成都的“莽汉”,“非非”等为代表,第三代诗人发起了一场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的诗歌运动,针对已成诗歌主流的朦胧诗派。《有关大雁塔》因为对诗人杨炼《大雁塔》的直接反叛,成为那场运动的一个代表。
乌青视他们为偶像。他背诵他们的诗,把喜欢的诗摘抄下来,抄了两本厚本子。他在高地音乐论坛和竖认识,知道竖也写诗,就去上海找竖。他剃着光头,戴一顶草帽,然后把诗摘递给竖,竖问:“这个好吗?”乌青说:“这个好。”要是看不懂,竖问,“这个好在哪儿?”乌青就告诉他,好在哪。“我当时是一个后进者,他已经是个真理在握者。”竖说。
在此之前,他也找过张羞,以一种诗歌真理在握者的姿态和还在懵懂中写诗的张羞吃了一顿饭。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乌青在浙江工业大学的西门等张羞,隔有100米远,张羞就认出他了,“人是能看出同类的。”乌青瘦,空荡荡的,衣服比身子大了几个码。当他开口说话,语速飞快,好像有点紧张。那顿饭,乌青从鲁迅开始讲,讲到余华,讲到卡夫卡,讲了一大堆,“感觉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人。”接着,乌青对他说,“我前几天写了一首诗,叫《把中国最好的鸡蛋献给自己》”,他感叹,“写得太牛逼了。”张羞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很吸引我。”
竖打电话给乌青。乌青从大学辍学有一段时间了,他待在杭州的一家网吧,生活潦倒。乌青建议他们一起去成都,找另一位诗人,肉。他们从上海出发,坐了四十个小时的绿皮车,抵达成都。
当天,他们打电话给何小竹。何小竹是“非非”诗派的其中一位诗人,和杨黎是相濡以沫的好兄弟。他们约在瑞丰广场附近立交桥下面的一家茶馆见面。见面之后,何小竹对他们的印象很好,“用韩东的话说,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他给牌桌上的杨黎打了个电话,说:“我新认识了三个年轻人,觉得很不错,我们一起吃火锅。”晚上,他们见到了杨黎。
杨黎走进去,三个人全站了起来,他们的个子都在一米八,弄得小个头的杨黎有点紧张。三个人都羞涩,只是对着他笑,却不说话。何小竹给杨黎做介绍,接着,他们挨个给杨黎念自己的诗。杨黎回忆,“给我的印象,第一,我第一次认识了网络人物;第二,他们的诗歌很让我感动,经过了90年代的逆潮,整个90年代丧失了先锋精神的状况下,我一直觉得诗歌的某种精神和传承是不是断裂了,当我认识了乌青和竖之后,我认为这种传承还在。”
到了2000年的冬天,杨黎、韩东、何小竹决定办一个文学网站。想法是韩东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做论坛,在网上做一下文学和诗歌的东西。”杨黎在玉林路开了一家酒吧,橡皮,有点致敬法国新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意思。敲定之后,何小竹告诉乌青,希望他来成都帮忙。那顿火锅之后,乌青去了武汉,竖回了上海。乌青听完,又告诉竖和张羞,竖会网页设计,张羞会编程。没多久,他们都在橡皮酒吧碰面了。
那年没有大年三十,除夕是在二十九,也就是阳历的2001年1月23日,“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上线。橡皮一出现,就聚集了一支接近两百人的写作队伍。在对待诗歌的态度上,他们倾向于简单的出离的语言,和诗江湖的身体写作,打破禁忌不同,橡皮更追求诗歌的艺术性。
2000年,杨黎提出诗歌的“废话”理论,这个理论对后来的橡皮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在一篇《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文章里,杨黎写道,“诗歌写作的意义,就是建立在对语言的超越之上,超越了语言,就超越了大限。超越了语言的语言,就是废话。废话是语言的极致,盲区和永恒的不可能。”
“在写诗的理论层面上,橡皮一开始就给了你很高的高度。一般来说,写作从青春期的抒情,从写情书开始,表达欲望、荷尔蒙,慢慢进入对人生的理解,抽象和哲学化。橡皮说,要把诗歌从文学当中抽离出来,只说诗,这一个字。如果说诗江湖是青春化的写作,橡皮就是出世的老年人的写作。”张羞说,“这个理论很极端,当时折服了很多人,所以在橡皮写诗的人很多,估计得有五六百号人。后来,有很多人跳不出杨黎的东西,它有很强的逻辑性在里面,当思考的抽象度不够的时候,很难在另一个层面观察,所以就出不来。”
橡皮开办不久,杨黎在论坛认识了一个网名叫“橡皮的姑娘”的北京女孩,他和她见面,随即恋爱。2002年年初,杨黎把酒吧转让,随着爱情,去了北京。他已经在橡皮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诗人,他们都多少受到他的影响。火星招待所里的诗人,正是80年代的余绪。
六
2002年,春天快到末尾,竖,张羞和吴又搬到九棵树。吴又依旧在赛特大厦上班,竖在一家叫“紫图”的出版社做编辑,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班。张羞没有工作,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之后,对着房间里唯一的一台康柏486电脑,打一些分行的文字,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那台电脑很旧,没有word,没有联网,只有写字板,唯一能玩的游戏是空中接龙和扫雷。因为没有干扰,他很喜欢在那台电脑上写作。写完之后,他出门散步,在街边的小饭店吃一盘炒饼,接着去网吧,把刚写的诗发到橡皮论坛上。在网吧泡到下午三点钟,他回出租房,看点书,等另外两个人回来。六七点左右,竖和吴又都回来了。他们也在上班时间或者回程的路上写诗。他们交换诗作给对方看,然后相互评论对方的诗,语言非常直接。晚上,他们去外边的路边摊吃烤串。一般是叫几串羊肉串,几串馒头片,最重要的是有酒,有酒说话才有劲头。酒很便宜,一块五一瓶的普通燕京,烟也是,抽很冲的都宝,两块五一包。“人比较理想化,精神层面的生活会多一些,物质上比较匮乏,比较穷,但是大家都认为,无所谓,只要最低要求就行了,感觉都能扛过去。但是诗不行,诗一定要往好里面写,要不然出去没面子。”张羞说。
张羞交有一个女朋友是武汉人,正在武汉念大学。他们也在论坛认识,然后见面,恋爱。隔一两个月,张羞就去女朋友那住一段时间。当时,武汉有一家叫“诚诚”的书商,老板签了30个潜伏在地下的写作观念比较前卫的作者,打算每轮推10个代表作家。第一批有后来成名的作家盛可以和吴晨骏,张羞和吴又被签在第二批。2002年,张羞在武汉写了一部10万字的长篇《大象》,走的是美国60年代垮掉派“在路上”的路子。吴又一直在论坛发短篇小说,风格尖锐直接,在网络已经积累了一些人气,累计起来有20万字。第一批作者推出之后,反响寥寥,书没有卖出去。不多久,公司倒闭,第二批的计划不了了之。张羞说,“他以为文学的先锋时代还会出现,但是没有人买,像余华他们所经历的先锋的黄金时代没有出现。”
2002年,橡皮论坛的人数不断增加,成为圈内有影响力的文学阵地,文学期刊的编辑也会到这里寻找有潜力的写作力量。韩东当时是《芙蓉》的特聘编辑,他专门开了一个栏目“重塑70后”,发表了很多潜伏在网络的年轻诗人的作品。“前面已经推过一些和商业挂钩的70后的作家,‘重塑70后’和商业脱钩,让大家知道,除了卫慧、棉棉这种为大众所知的写作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写作的方式。”韩东说。
九棵树是橡皮的一个据点,诗人们像赴一场心照不宣的约会,隔几天就约在一起碰个面。他们很少讨论未来的出路,聊天的内容从“什么是诗”,“如何写诗”开始,细微到一首具体的作品,他们翻来覆去地探究,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完全处于写诗的状态,我们写,很多写诗的人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在专注地、投入地做这样的事情,有种浪潮的感觉。”吴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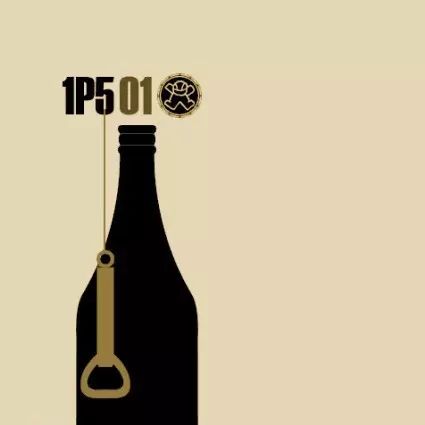
2002年,张羞、竖、吴又、小虚等诗人成立网站“一泡乌”。一泡乌是上海话,大概意思是垃圾、一坨屎,后来改成英文:“1P5"。设计师:竖。
吴又也在谈恋爱,对象是他初中同学,在石家庄的一所部队学校当兵。有一次,吴又的女朋友去九棵树看他。待了几天,她非常震惊,她不知道她的男朋友已经对诗歌投入到这样的地步——几个年轻人什么也不干,围着一张桌子可以坐上十几个小时,而永恒话题只是诗歌。她在石家庄,吴又写信给她,每次的信件末尾会写一首诗,像是附赠的一件小物品。她看一看,误以为那些诗是他摘抄下来给她的,觉得他是个有点心思的男孩。她问吴又,“这个年代怎么还有你们这样的人?”
8月,入夏了。竖有好一阵子没有再上班,他厨艺好,干过盒饭公司的切配,每天负责买菜做饭。有一天,九棵树来了一位导演朋友,雎安奇。1999年,他拍过一部《北京风很大》,入围柏林电影节,在电影圈有些名气。他正在为自己的第二部影片《诗人出差了》寻找男主角。在九棵树的出租房,他给竖试镜。几天之后,竖跟他去新疆拍片,那是一段波折而疯狂的旅途。期间,竖的手机关机,没有人能联系上他。他像蒸气一样消失了。
在竖消失的这段时间,吴又决定离开北京,去石家庄全职写诗。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桓有一些时日了,他越来越感到写诗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经历了没日没夜和诗人们一起聊天,讨论,他想安静一段时间,停下来,专注地写作。这个信号非常强烈,因为他觉得他和诗之间几乎触手可及,他想去石家庄彻底掌握它。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杨黎,杨黎觉得非常好。
两个月之后,竖的手机终于通了。吴又已经在石家庄安顿了下来。石家庄的生活负担很低,房租每个月200元。上午,他去市场买菜,做饭,之后看电影或者写作,然后是晚饭,继续写作。他保持一天三到四个小时的写作时间,以写诗为主,也写小说。日子过得规律又安稳。竖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石家庄。吴又见到他,他手提一串新疆提子,一副一看就是在新疆蹉跎过的模样。竖疲惫而沮丧,他告诉吴又,他和雎安奇闹翻,电影拍砸了。

2002年,北京地铁。左起:张羞、竖、小虚。摄影:贾冬阳。
七
对于住在九棵树的任何三个人而言,2002年都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年份。那年夏天,张羞后来在自己的诗集里写下了那个交好运的时刻,“2002年,夏天的出租房,一个清晨。我停下手,起身走去窗台,慢慢喝完还剩半瓶的隔夜酒。窗外没有云,天空全部是青色的,是一块绝对安静的天空。我琢磨着,我大概碰到了一生中最酷的时刻。因为就在几分钟前,在键盘上敲出的那十几行句子,让我感觉到,它们很可能就是诗。因为它和我以前写的所有诗都不同,因为它竟然是亮的。”他安慰自己,“你的运气不错。”
吴又离开北京后,九棵树没了经济支持,12月,房子到期。竖、张羞和后期搬来的朋克青年小虚,搬到太阳宫的光熙门北里的一间地下室,月租650元。三个人都没有工作,靠朋友的接济生活。那年除夕,张羞和竖没有回家,在小区的华热餐厅吃的年夜饭,他们是那儿的常客。吃到7点钟,张羞对竖说:“我要走了,我要去武汉。”竖摆出无所谓的姿态,“走吧,赶紧的。”他走出餐厅,在公交站等公交,天气寒冷,空气中飘着白色的雪花。他想这次离开,可能不一定再回来。
他买了一张去武汉的火车票,只有站票。他走进车厢,滞闷的空气令他不舒服,也许是喝了点酒又受寒的缘故,他瘫倒在座位间的过道上。有推车的列车员过去推他,他一动不动,仿佛失去了知觉。约莫十分钟,他爬起来,走到车厢交界的那片空地,那里刚好有一点缝隙,底下透进新鲜的空气。他靠在墙上,点燃一支烟,缓了过来。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他就到了武汉,新的一年来了。
新年过去没多久,全中国陷入对非典的恐慌,武汉的疫情也很严重,张羞盘算着回杭州找工作。他住在高中同学的家里,那个地方正对着医院,他觉得很不安全,他坐车回嵊县老家。一到老家,他就被村民关在家里,隔离起来,他的身体有发热的症状。他吓得要死,内心瞬间灰暗。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恢复了,非典的风头也慢慢过去了。
夏天,他的女朋友大学毕业。他们在杭州租了一间房,张羞找了一份网站美工的工作,女朋友找了一份行政工作。在杭州,他想念诗人的集体生活,因此倍感孤寂,像一只落单的鸟。
竖去杭州找过他一次,相当于再见的阔别。白天他们很俗气地游了西湖,张羞用他一贯的写诗的口吻对竖说:“竖,那个地方叫古荡,那个地方上面叫古荡的天空。”晚上,他们在饭馆叙旧,张羞提议喝黄酒,两人喝了七瓶古越龙山,他付钱给老板,老板说:“你已经付过了。”他说:”不可能。”他把存折掏出来,给老板看:“你看,怎么可能?”那天他刚好发工资。竖在旁边劝:“你别争了,没有老板要请你吃这顿饭,我见你付过了。”他知道张羞喝断片了。
过了大半年,张羞实在待不住,他不死心,打电话给吴又,和以前一样,吴又说:“那就来北京吧。”那是2004年的春天,吴又的女朋友快从军官学校毕业,她被分派到北京,他也决定回去。隐匿的将近三年的写作时光结束了,当他再次回到北京,他开始工作。那年秋天,他进入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张小波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书商,也写诗,曾是上海城市诗派的代表。1996年他因策划《中国可以说不》而崛起于中国出版界,策划了一系列畅销书。吴又很快适应出版业的游戏规则,在这个领域独当一面。一年后,他创立了自己的图书公司,却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

题图为火星招待所里的诗人在通州杨庄,左起:竖、张稀稀,池塘,裴飞,张艺。
所有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